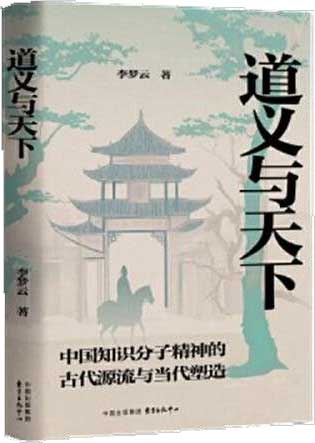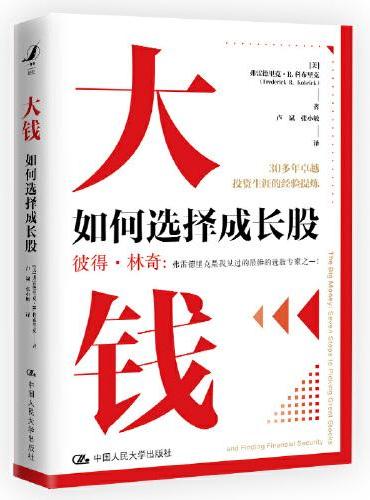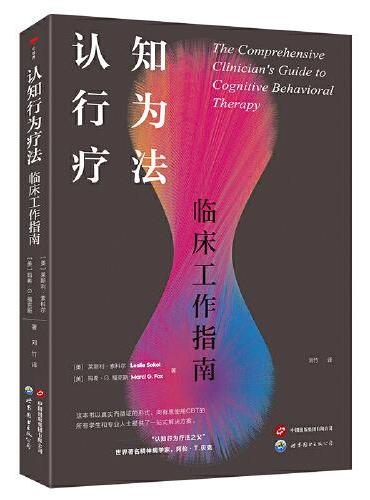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攀龙附凤:北宋潞州上党李氏外戚将门研究(增订本)宋代将门百年兴衰史
》
售價:HK$
97.9

《
金钱的力量:财富流动、债务、与经济繁荣
》
售價:HK$
97.9

《
超越想象的ChatGPT教育:人工智能将如何彻底改变教育 (土耳其)卡罗琳·费尔·库班 穆罕默德·萨欣
》
售價:HK$
75.9

《
应对百年变局Ⅲ
》
售價:HK$
85.8

《
前端工程化——体系架构与基础建设(微课视频版)
》
售價:HK$
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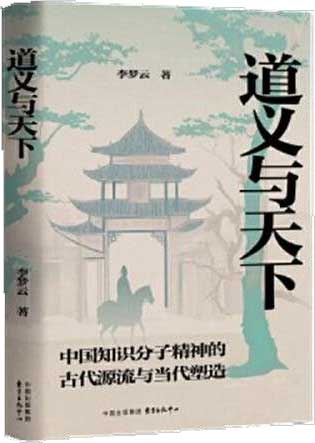
《
道义与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古代源流与当代塑造
》
售價:HK$
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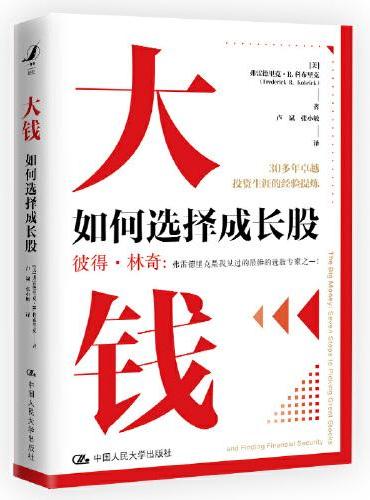
《
大钱:如何选择成长股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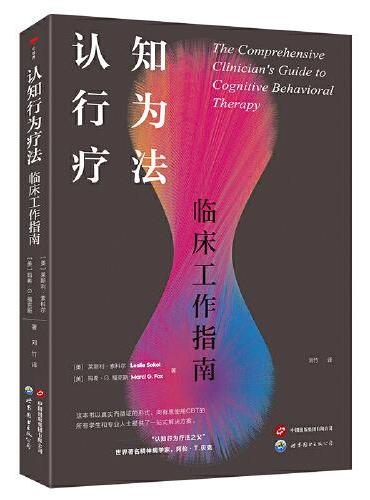
《
认知行为疗法:临床工作指南
》
售價:HK$
85.8
|
| 編輯推薦: |
这本书邀请读者参加一场对话。对话的主角是两位最具智慧的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2008年春天的许多个早晨和下午,他们坐在一起,探讨美国当前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是一场心灵与智力的旅程,两位全国最好的向导,带你走入下一任美国总统将要面对的多重选择的世界。
读者打开本书,可以想象自己坐在一张宽大的会议桌前,两位曾经在白宫以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份纵横捭阖的人,正坐在桌边侃侃而谈……
本书将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
|
| 內容簡介: |
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出现了问题。用传统的说法来讲,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最强大的国家,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多:恐怖主义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崛起、全世界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两位美国最具权威的外交政策专家,都曾担任过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戴维·伊格纳休斯的主持下,他们解析了美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挑战:美国应该从伊拉克撤军,还是继续留在那里?美国应该如何与伊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打交道?美国用什么样的强度来推进北约边界直至俄罗斯边境?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全球政治觉醒”有多重要?美国如何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美国必须捍卫自己在远东的地位吗,如何捍卫?……他们认为,美国今后几年内的外交决策将决定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还能维持多久,唯有改革才能将美国这艘大船带入最佳航道。
本书将帮助我们更加了解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
|
| 目錄:
|
前言
第一章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第二章 我们自己制造的危机
第三章 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第四章 开放的好处:中国和远东
第五章 没有天然疆界的国家
第六章 不可或缺的伙伴关系
第七章 文化尊严的政治
第八章 最初的一百天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我们怎么会在这里?
戴维·伊格纳休斯:让我引用乔治·马歇尔将军的话“别和问题纠缠”来开始我们的对话。我一直认为,他的意思是要“理解问题”,先向你自己描述清楚,然后再去解决它。千万别跟问题本身纠缠。所以,让我用描述问题的方式,来向你们每个人提问。问题在于,新总统上任之际,美国面临着什么样的形势,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有哪些困难,这些困难的实质是什么。兹比格,请告诉我你对今日世界面对的问题的看法,它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谈如何应对。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小布什总统曾在国情咨文中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是本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震惊。我就对自己说:“是不是有点傲慢?”现在是21世纪初,有人却在向我们灌输什么是本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假设我们回到1908年,如果被问及如何定义20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那么在大多数人的答案里,会谈到右翼和翼,谈到极权主义及类似的政权吗?或者回到1808年,如果被问及19世纪的挑战,会有多少人,在保守分子在维也纳会议取得胜利的前夜,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民族主义情绪将会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以及整个欧洲蔓延呢?
本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我认为这包含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
第一,我称之为“全球政治觉醒”。第一次,全人类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是说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年来的统治权。第三,则是全球共同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
伊格纳休斯:兹比格,请继续你的思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如何应对这些已经发生的变化?
布热津斯基:如果我必须将其归结为一点的话,那么我要说,这一点就是美国信心的沦丧。我一生中的主要时间,都生活在冷战的氛围中。这是一场巨大的全球斗争,但我们用自信来消耗它。可最近几年我却发现,美国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惧的文化,这种文化让我们故步自封。
当然,“9·11”事件引发了恐惧的弥漫。整个国家都在电视上看到了它,美国的自信开始摇晃。但是我认为,恐惧被人为宣传所放大,这一点让人十分难过,因为这样于事无补。如果整个国家被恐惧所驱使,美国将不可能合理地应对我们下面将要谈到的变化。
伊格纳休斯:布兰特,你如何评价我们这些问题的本质?我们的哪些反应能力遭到了破坏?
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兹比格基本一致。但让我先从历史背景谈起。我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历史在世界范围内的断层。
冷战将密集的注意力强制转移到某个单一问题上来。它将我们动员起来。它动员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反对某个单独的集团。它影响了我们的思维过程,影响了我们的机制,也影响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想,比起冷战时代,没有哪个时代更能让我们如此集中精力。
突然之间,只是一眨眼的历史瞬间,世界走到了尽头,被一个没有冷战般实体威胁的世界所代替。冷战之中,如果我们犯了一丁点儿错误,都可能会炸毁整个星球,突然之间,这种威胁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大堆棘手的问题。我们没法只通过一只望远镜去盯着莫斯科,我们现在站在望远镜的另一端,面对成千上万的小麻烦。然而,我们处理小麻烦的机制与思维过程,却只适用于应付莫斯科。
伊格纳休斯:你当年在白宫,当全球都在害怕核毁灭时,是怎样的状态?你们二位,都曾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坐在那个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在坏消息袭来、全球危在旦夕之时,你们身处其位,有什么感想?布兰特?
斯考克罗夫特:总有一种想法挥之不去。如果任何一方犯下严重的错误,那对全人类来说就可能是灾难。我们是不是每分每秒都在这样想呢?倒也不是。但总会想到这些,还有会不停地想,苏联人到底想要什么,他们的能力边缘在哪里,比如很担心,他们的技术发展,是否能够瞬间摧毁我们,是否能将核对峙状态变成核不对称状态?
对我而言,这些想法超乎一切。我们看待冲突,无论是朝鲜、越南,还是其他的小麻烦,我们都会想“怎么才能既证明苏联人背后有一手,又别去傻乎乎地冒险把自己搞得没有退路”。
伊格纳休斯:听起来,好像有一种恐惧,就是害怕任何小小的弱点被扩大成全球灾难。那正是我们至今念念不忘的冷战思维的一部分,甚至,还把它带入到新的环境中来。兹比格,你当年处在决策核心时的感受如何呢?
布热津斯基:哦,我的工作之一,是协调总统在核打击到来时的回应。我想,布兰特,那也是你的职责,是吗?我并没有泄密,不过,大概是这样一种过程:
我们会在苏联大规模发射核导弹后1分钟内发出核打击预警。大概在第2分钟之内,我们就能够得到该次核打击的基本规模以及可能目标的数据,并且精确度相当高。到第3分钟,我们多少已经知道何时预估后果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同样是在第3分钟,总统会收到信息提示。第3~7分钟之问,总统会决定如何作出反应。
这件事一开始就变得非常复杂。如果这是一次全面核打击,那么反应就会相对容易。你需要的只是全面报复。但假设这只是一次有选择的小规模打击,那么就会有许多种选择。总统需要权衡各种选择的利弊。他会如何反应呢?总会有一种不确定性。在任何情况下,这个过程必须在7分钟内完成。我想,这个时间,与你们共和党政府的估算应当差不多,是吗?
斯考克罗夫特:嗯,差不多。
布热津斯基:到第7分钟,执行的命令就必须下达,无论是什么样的决策,都必须执行。这并非完全的理论臆想,因为我们有过一次小小的恐慌。有一次,我被半夜叫醒,并被告知,战略指挥系统已经启动。当然,最后搞清楚这是一场演练,但不知怎么传着传着却被某些人误读成真的核打击了,不过,我们的反应很快。没有什么大事。
大约到第28分钟的时候,就会出现后果。也就是说,你和你的家人就已经死去。华盛顿被夷为平地。大量美国军事资源被摧毁。但可以想象,总统同时也会作出反应决策。我们已经回击。6小时之后,1亿5千万美国人和苏联人就会死去。
这就是我们当时与之共存的现实。我们尽可能地使之稳定可控。既不能首先进行核挑衅,又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坚定地执行敌对核政策,这样任何一方都不会心存侥幸。
现在就不一样了。我认为布兰特描述得很好,现在有一大堆棘手的问题。新的现实是一种分散的动荡。我认为,那就要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模式,要求我们对于全球变化的复杂性有着更加纯熟的理解。我们需要一个能够理解自身责任的明智社会,需要一个不会在恐惧中慌忙作出取悦大众的荒唐决策的社会,需要一个不会使我们与世界隔离,不会让我们变得非常脆弱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领导力。伊格纳休斯:布兰特,当冷战结束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曾经经历过冷战的人来讲,真可谓是突然之间,一切都结束了!可以理解,有一段时间,外交政策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人们好像真的不在乎了。这种观念让人迷糊了很长时间。
斯考克罗夫特:是的,“9·11”事件唤醒了人们。
伊格纳休斯:让我问你一个问题,记得世界改变的那一天,当你随之成长的世界、你和你的这一代人都十分熟悉的世界,变得完全不同的那一天。我想说的是,那就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苏联帝国正在崩溃,可能再也无法修复。布兰特,你当时正在白宫。请描述一下那一天,这场漫长而激烈的斗争开始终结的时刻。把你的想法描述出来。
斯考克罗夫特:不过,当时,我不会把柏林墙倒塌的日子当成“那一天”。对我而言,那一天是贝克(Jim Baker,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译者注)和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译者注)站在一起,宣布伊拉克人侵科威特的日子。对我而言,那才是真正的冷战结束的时候。苏联人在柏林墙倒塌时受到过沉重的打击吗?整个帝国当时摇摇欲坠吗?是的。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人们并不清楚结果会如何。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拼凑一个邦联,以代替老旧的苏联。他努力想修补架构,而不是要摧毁它。所以,一切都仍然处在模糊未定的状态。我们是不是感觉很好?当然是。但在那个时候,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总统的感受,却是“别得意忘形”,我也是同样的想法。即使这就是冷战的终结,我们也千万不能再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种“赢者通吃”的错误。恰恰相反,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是赢家。我们胜利了,苏联也胜利了!柏林墙第一次被破坏时,总统就把记者叫到他的办公室。当时,莱斯利·斯塔尔(lesley Stahl,美国CBS资深记者)就问:“总统先生,你看上去并没有那么高兴啊!我还以为你会很想在柏林墙的废墟上跳舞呢!”总统回答说:“哦,我不是那种人。”其实他真正想说的是,我并不想幸灾乐祸。因为莫斯科的反应很可能会摧毁我们的一切努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