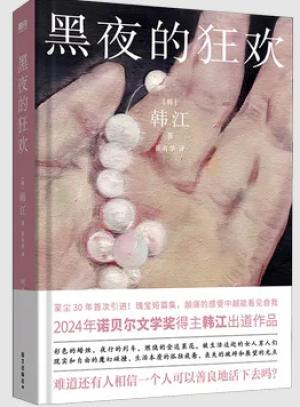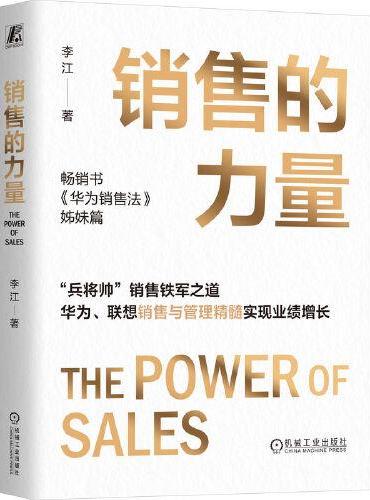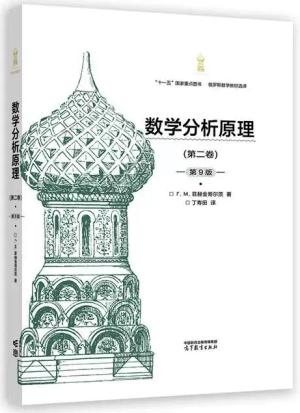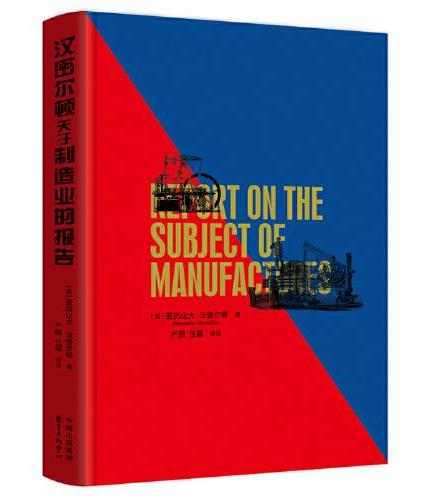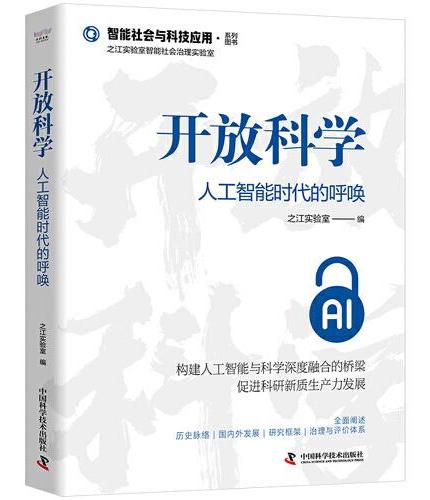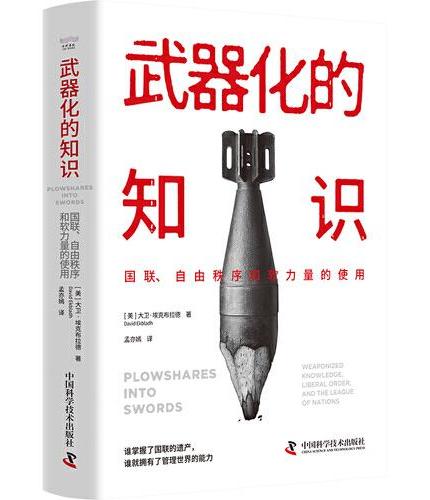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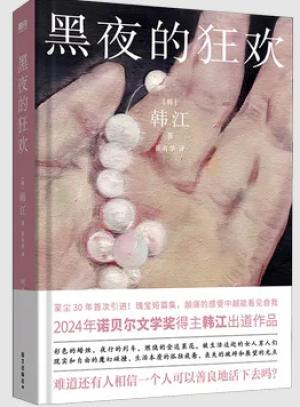
《
韩江黑夜的狂欢: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出道作品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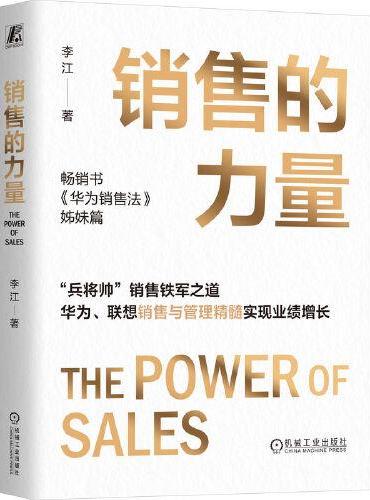
《
销售的力量
》
售價:HK$
97.9

《
我活下来了(直木奖作者西加奈子,纪实性长篇散文佳作 上市不到一年,日本畅销二十九万册)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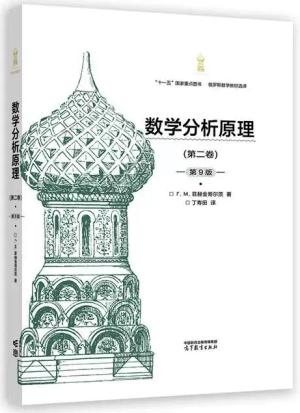
《
数学分析原理(第二卷)(第9版)
》
售價:HK$
86.9

《
陈寅恪四书
》
售價:HK$
3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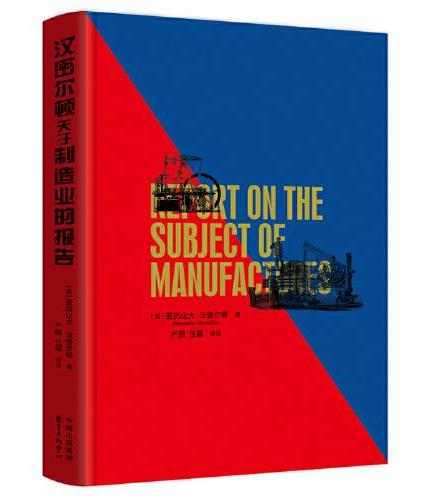
《
汉密尔顿关于制造业的报告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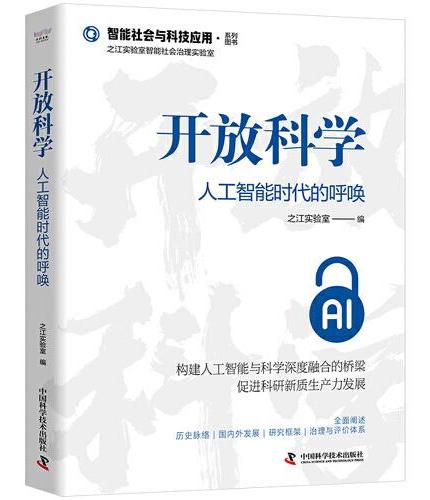
《
开放科学:人工智能时代的呼唤
》
售價:HK$
1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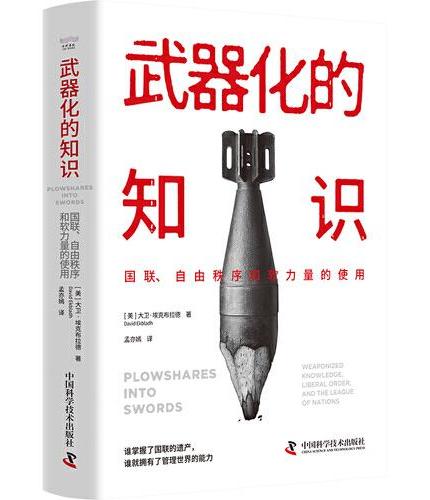
《
武器化的知识:国联、自由秩序和软力量的使用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
本书是师陀中短篇小说集精选,主要摘自其短篇小说集《谷》、《落日光》、《野鸟集》、《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等,展现了不同时期的作品个性。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史上,师陀是属“京派作家”的一员。他的小说中有着“田园小说”的特征,构建了诗意、静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人与人之间有着淳朴的人际关系,期待以一种理想的生命存在方式和社会制度模式。这样的“原乡神话”,感动了一代代阅读者。
|
| 內容簡介: |
师陀,原名王长简。1910年3月10日生于河南省杞县。1946年以前主要以笔名“芦焚”发表作品,之后,改用“师陀”。
本书是师陀中短篇小说集精选,主要摘自其短篇小说集《谷》、《落日光》、《野鸟集》、《无名氏》、《果园城记》、《石匠》等。他的作品充满了对黑暗旧世界的厌恶,文笔优雅、口语犀利、生动活泼,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少的贡献。
|
| 目錄:
|
结婚
第一封信
第二封信
第三封信
第四封信
第五封信
第六封信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落日光
民题记
落日光
牧歌
一片土
金子
鸟
父与子
江湖客
结婚
|
| 內容試閱:
|
第一封信
我惟一的亲人佩芳,你们终于走了,留下我,回到乡下老家去了!上海依旧人山人海,龌龊,杂乱,骚扰,谣言,暗杀,掠夺,红尘万丈;可是一阵风,你们走了,我心里也给刮光了。试想你的去恶有多可怜,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到他?你也许要说:
“你还有学生和同事,他们是经常跟你一起的。”
你说得不错,我的亲人,他们的确跟我经常相处。可是我在上一封信上不敢告诉你,我知道你到乡下去并不乐意,也是不得已,我怕你更为我担心。我们这是怎样相处的呀!先说同事,你自己明白,你父亲就是很好的例子。自从物价飞涨,生活就像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逐渐天天收紧。你只看见他们的脸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灰,一天比一天脏,衣服一天比一天破。当你在学校或校门外马路上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夹一大堆讲义,失魂丧魄,匆匆走来,忽然把你撞个踉跄,几乎把肋骨给你撞断。他们于是朝你瞪一眼,脸上毫无表情,冷冷地点个头,然后撒腿走去。你站住楞[愣]老半天,他们可始终头都不回,好像他们根本不认识你,好像你阻碍了他们的前程,抢了他们的饭碗,他们跟你有无限仇恨。
可是你不能怪他们,他们的心情的确很坏,事情的确太忙。为应付全家衣食,他们每礼拜至少得教三十个钟头,晚上还得上人家去教家馆。他们早上从家里出来赶不及吃早点,脸也来不及洗,便在马路上买个大饼,一面嚼,一面从这个学校赶到那个学校。中饭就吃点冷饭或面包。至于家里,谁去管他们家里呢?他们的好师母因营养不良病在床上,却没有钱买药;他们的孩子号哭着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却没有人理会;房子里到处是破布,蚕豆皮,坏玩具,卖不能卖,当无可当,看上去整个像活地狱。他们活着毫无希望,根本没有时间让他们希望,他们满心所想的是领下薪水买米。那么,你又怎能责备他们,让他们想到别人,关心别人?
我们现在再说学生。毫不惭愧地告诉你,我恨他们。今天我就逮住一个大骂。这是个我学生中顶娇贵,顶有钱,顶会打扮,顶不用功的女孩子,我平常就讨厌她。她背后送我个诨名,叫我“剃头师傅”。起因是我上课迟点,我走进教室,她高声嚷着,“剃头师傅来了!剃头师傅来了!”我实在忍不住了,走上讲坛尽可能损她,只差一点没有把最难听的骂出来,直损得她哭到下课;也许下课还在那里哭,我可不知道了。我承认我太过火,可是佩芳,请你老实告诉我,你不久以前还亲眼看见的,我近来外表纵然寒酸,纵然比人家穷,而我究竟也是“人师”,我的人格难道就那样下贱吗?
你也许要奇怪,我怎么骤然变得这么厉害。我原是出名的和气人,喜欢孩子,喜欢学生,做事肯负责任,你父亲也夸奖我是好教员,将来大有希望。这一切都不含糊。我的脾气的确越来越坏,但你只要设身处地想想,就明白这变坏的原因。首先,我花费极大精力将材料预备起来,对学生讲王莽的改革与失败,或兰格斯王室与约克王室的阴谋,他们却在下面看张恨水的小说,再不然就丢纸团,约会晚上看狄安娜·窦萍。他们丝毫没有尊敬我的意思,丝毫不把我看成先生。接着其次,我连讲几个钟头,熬得头昏眼花,终于下课铃响了,大家抢着跑出大门,他们哗笑,喧嚷,扮鬼脸,一阵风跳上汽车包车,把我远远的丢在后面,谁也不理会我;我是他们的先生,累得像牛,却不得不一步一步走去。这使我想起他们是少爷小姐,世间贵人,我则是他们门口要饭的。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顶脏的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假使过这种日子的是你,就是说你觉得马路也比你漂亮,比你尊贵得多,那时候你怎样想呢?
“那你以前怎么过的?”你可能问,“你以前难道好些?你不一直就这么穷?”
你理应问,佩芳,你问的有理。实不瞒你,学生们受气大半是冤枉的,我的脾气变坏还有个重大原因。我本是个好教员,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你怎么想得到!那全因为你们,全因为有你们在上海,你父亲母亲连你弟弟都把我当做亲人,每礼拜中我有个礼拜六和礼拜天。我从礼拜一便逐日计算,单等礼拜六晚上;其实永没有到过晚上,顶多六点,我已经飞奔到你们家里,谁也拦不住我,而你们也早已在等着我了。你弟弟蹦蹦跳跳,上来拽住我的袖子,我是他的大哥。你母亲——上天保佑她活一百岁,喜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见她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起东又忘记西,直唠叨嚷嚷。请别生气,她心里岂不早就承认我是她的女婿了吗?假使我有一天不来,她会整晚不高兴,有时竟可笑地要以为我病了,给车子撞伤了。你在家比较稳重,怕母亲笑话,你只轻轻点头。然而这种故意装出的冷淡,在我远比千言万语更亲切。你父亲生来喜欢喝几杯,酒后总发牢骚,然而我们也难怪他。他过去为社会服过务,为人类尽过力,心无二用,勤恳地当了三十年教员,目的无非希望国家社会进步,而在垂暮之年,许多学生都已自认为国家柱石,起居注经常登在报上,他自己却受近乎亡国之苦……想到这里,我们不但对他的愤懑衷心原谅,只觉得他的责备应该,他有权利,他的赤诚无私格外可亲。
我就这样在你们家里留到深夜。在你父亲的侃侃议论中,你母亲的只怕冻着饿着的唠叨中,你弟弟的玩笑中,你眼睛关心地静抚下,我精神又醒过来;过去六天的疲劳统统消失了。然后第二天,我门上悄悄地剥剥两声,刚转回头,一个小脸已经喜莹莹[盈盈]探进来了。这是你,佩芳。我不知道你是否在镜中观察过自己,你的因为还不曾十分成熟,稍微有点灰黄的脸蛋,淡淡的蛾眉,沉静的凤眼,调皮的翘起的鼻子,轮廓分明的嘴唇,丰满的下颔,综合来看,远不算漂亮——我是说它不能令人一见惊倒,但却有另一种美,要经过相当时间相当细心才能发见的,温柔,善良,诚恳,涵蓄,不可动摇的自尊。一种温暖随着你走进来,你不单照亮了我的屋子,并将照亮我的一生。
这一天属于我们两人。我们于是上公园,或上郊外,躺在香味刺鼻的软草上,轮流读狄更司,云就涌来涌去,在翠蓝的天上滑。其实我们又哪里会管狄更司扯些什么谰言!我们不过利用他占住时间,使大家不过分亲近。
我没有方法说明那时的幸福;然而现在,你想想我的现在吧!假使知道我的实在情形十分之一,你也会了解我了。我每天连教几个钟头,丝毫得不到安慰。我的鞋是打过补丁的;我的衣服没有钱洗;我在饭馆里,一个徒弟都吃两个以至三个菜,我只能吃一个菜的客饭;我的房子像被掘开的古墓,满目凄凉,地板上桌子上全是灰尘。这种种都销[消]磨我的志气,再加上孤独,更是越来越使我自卑,无论在饭馆在路上,我都觉得我是个罪人,不敢正眼看人。平常人家也不注意我,就像我是灰色的,无声无息,和谁也没有关系的物件。我恨人家穿的漂亮,讨厌成对的人在我前面走,怕看人家潇洒自在,没事时候我只该躲在屋子里瞎想。我近来的确消沉,对于功课毫无兴趣。一个问题老在我脑子里盘旋,像一只蜘蛛,结下无形的大网,把我整个的心都网起来。假使再继续下去,我相信我会发疯。
钱!佩芳。钱固然苦坏了我,同时可也苦坏了你们,你恨它还得爱它。在你们走后我曾反复想过,如果不打仗,我手里能多积攒点钱,按照预定计划,我们现在应该结过婚了。这就是我上封信里说要做生意的原因。我本来可以不告诉你,只因为太爱你,我才跟你商量。我没想到竟会遭你反对,你说我们大家都还年轻,等到战争结束不迟;你说做生意没有把握,太不清高;你又说真的幸福并非建立在金钱上面……可是我的小空想家,请容我问一声:假使战争打一百年,我们难道也得等它一百年吗?
我承认我需要结婚,也许比人家能想到的还要迫切。先让我们抛开我目前所受的痛苦,连别的重大理由也暂时不提,你只要知道我过去的生活——虽然我以前曾约略对你讲过,但你如果知道得更详细点,你更会明白我怎么这样需要家庭。
我母亲是世间至可怜的人(现在且让我从头讲起,看完后我相信你会更了解我)。她娘家是个小县城的败落主子,正所谓高门不来,低门不就,直到三十岁,父母双亡,兄弟们分了家,不得已才嫁给一位姓胡的老官僚作填房。这官僚就是我父亲。她过门时前房的儿子比她还大,就是说我父亲已经五十多岁,跟前好几个孙子了。
我父亲本来在京里做官,不算大,也不算小,就是不必每天画到,自然也就没有实权的那种角色。收入相当好,生活很优裕。但是他的后台,一位靠吹牛起家的现代说客,因政局变化忽然倒了。他奔走将近两年,后来看出别谋门路的没有希望,只得带着家眷回老家来。这事恰巧发生在他的前妻去世的时候。他有两个早已娶亲的儿子,一个守寡住娘家的女儿。因此你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地位非但不像婆婆,简直比做媳妇还糟。做媳妇还能讨公婆欢喜,她可是眼中钉。
我不清楚我懂事以前的情形。当我敢自己朝外跑,哥哥,姐姐,侄子,邻居,连用人都欺负我,我的耳朵忽然被揪住了,再不然便是背后飞来一脚。
P1-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