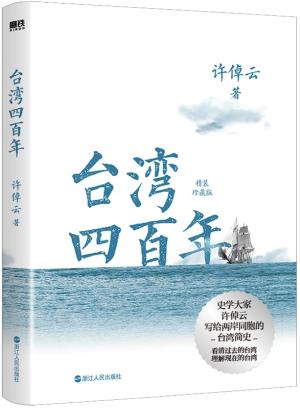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文化南方:中古时期中国文学核心传统
》
售價:HK$
7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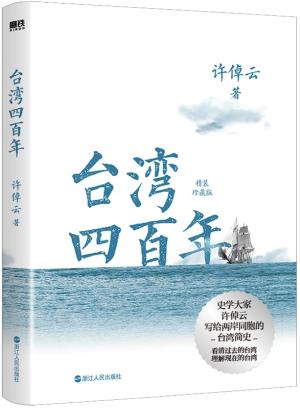
《
台湾四百年:精装珍藏版
》
售價:HK$
59.7

《
古玺印与古玺印鉴定
》
售價:HK$
141.6

《
中国官箴
》
售價:HK$
120.0

《
纽约四百年:为冒险而生的移民之城
》
售價:HK$
115.6

《
故宫还可以这么看
》
售價:HK$
198.2

《
高句丽渤海研究论集
》
售價:HK$
151.0

《
德国民法总论:法律行为理论(第二版)
》
售價:HK$
219.5
|
| 編輯推薦: |
本书是中国作家韩少功199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按照词典的形式,收录了一个虚构的湖南村庄马桥弓人的115个词条,这些词汇部分也是作者所虚构如晕街。
最早发表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杂志1996年第2期,后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之一。2003年8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a
dictionary of maqiao”。
《马桥词典》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曾荣获“上海市第四届中、长篇小说优秀大奖”中的长篇小说一等奖。
|
| 內容簡介: |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集录了湖南汨罗县“马桥”人日常用词,计一百一十五个词条。它以这些词条为引子,讲述了古往今来一个个丰富生动的故事,引人入胜,回味无穷。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马桥词典》没有采取传统的创作手法,而是巧妙地糅合了文化人类学、语言社会学、思想随笔、经典小说等诸种写作方式,用词典构造了马桥的文化和历史,使读者在享受到小说的巨大魅力时,领略到每个词语和词条后面的历史、贫困、奋斗和文明,看到了中国的“马桥”、世界的中国。小说主体从历史走到当代,从精神走到物质,从丰富走到单调,无不向人们揭示出深邃的思想内涵。
这是一次成功的创作实践,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
|
| 關於作者: |
韩少功,男,汉族,1953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1968年初中毕业后赴湖南省汨罗县插队务农;1974年调该县文化馆工作;1978年就读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任《主人翁》杂志编辑1982、副主编1983;湖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1985;《海南纪实》杂志主编1988、《天涯》杂志社社长1995、海南省作协主席1996、海南省文联主席2000等职。现居海南。
主要文学作品有《韩少功系列作品》九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含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长篇随笔《暗示》,长篇散文《山南水北》。另有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1981,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1997,全国鲁迅文学奖2007,华语传媒文学大奖2007以及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勋字2002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被两岸三地专家推选为.“二十世纪华文百部文学经典”之一。作品有三十多种外文译本在境外出版。
|
| 目錄:
|
一画
一九四八年续
二画
九袋
三画
三毛
三月三
三秒
亏元
马同意
马桥弓
马疤子以及一九四八年
马疤子续
小哥以及其他
乡气
下以及穿山镜
四画
天安门
不和气
不和气续
开眼
月口
公地以及母田
公家
双狮滚绣球
火焰
五画
龙
龙续
打车子
打玄讲
打起发
打醮
民主仓囚犯的用法
白话
台湾
汉奸
归元归完
发歌
六画
老表
夷边
压字
同锅
红花爹爹
红娘子
朱牙土
企尸
江
军头蚊
问书
七画
走鬼亲
呀哇嘴巴
你老人家以及其他
八画
现
枫鬼
肯
罗江
官路
话份
怜相
怪器
放转生
放藤
放锅
宝气
宝气续
泡皮以及其他
九画
科学
茹饭春天的用法
栀子花,茉莉花
挂栏
背钉
贵生
贱
荆界瓜
结草箍
狠
神
神仙府以及烂杆子
觉
觉觉佬
洪老板
津巴佬
十画
莴玮
根
格
破脑以及其他
哩咯啷
晕街
豺猛子
流逝
浆
冤头
罢园
十一画
梦婆
黄皮
黄茅瘴
甜
清明雨
十二画
散发
黑相公
黑相公续
隔锅兄弟
蛮子以及罗家蛮
渠
道学
十三画
碘酊
嗯
煞
十四画以上
模范晴天的用法
满天红
撞红
颜茶
嬲
飘魂
嘴煞以及翻脚板的
磨咒
懈
懒男人的用法
醒
后记
附录:
文学有副多疑的面孔——2011年2月国际纽曼华语文学奖授奖晚宴致辞
语言的表情与命运——2004年3月在香港国际英语文学节上的主题演讲
《马桥词典》评价摘要
|
| 內容試閱:
|
罗江
马桥的水流入罗江,村子距江边有小半天的步行路程。过渡有小划子,若船工不在,过河人自己把划子摆过去就是。若船工在,五分钱一个人,船工把划子靠到对岸了,稳稳地插住船头篙,站在岸上一一收钱。点一张票子,就蘸一下口水。攒下大一点的票子了,他就垫进一顶破旧的呢子帽,稳稳地戴在头上。过河钱无论冬夏都是一样。其实,夏天的江面要宽得多,水要急得多。惹遇到洪水时节,漫漫黄汤遮天盖地而下,昏黄了一切倒影,向岸边排挤一叠又一叠的秽物,还有一堆堆泡沫塞在水缓的浅弯,沤积出酸臭。但越是这个时候,岸边的人倒越多,一心一意等待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死鸡、死猪、破桌子或者旧木盆,还有散了排的竹木,打捞出来捡回家去,这叫发水财。
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有一个女人或者娃崽,泡成了巨大的白色肉球,突然从波涛中滚出来,向你投射直愣愣的呆目,骇得人们惊叫着逃散。
也有一些胆大的娃崽,找来一根长长的竹篙,戳着白色的肉球,觉得好玩。江边的人也打鱼,下吊网,或者下线钩。有一次我还没有走到江边,突然看见几个走在前面的女人,尖叫着慌慌张张回头就跑,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再仔细看,她们的来处,男人无论老少,也不管刚才正在挑担还是在放牛,刹那间全光了裤子,一顺溜十几颗光屁股朝河里跳踉而去,大吼大叫。我这才想起,刚才闷闷地响了一声,是炮声。这就是说,河里放炮了,炸鱼了,他们闻声而脱是去捞鱼的。他们舍不得湿了自己的裤子,也不觉得这种不约而同的紧急行动会吓着什么人。
在马桥的六年里,我与罗江的关系并水多,只是偶尔步行去县城时得在那里过渡。说起过渡,五分钱常常成了大事。知青手里的钱不多,男的一旦聚成了团,也有一种当当日本鬼子横行霸道的冲动,过渡总是想赖帐。有一个叫黑相公的,在这些事情上特别英雄,上岸以后拿出地下工作者舍己救人的作派,一个劲丢眼色,要我们都往前走,钱由他一个人来付。
他摸左边的口袋,掏右边的口袋,装模作样拖延够了,看见我们都走远,这才露出狰狞面孔,说他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给,老鳖,你要如何搞?然后拔腿就跑。他以为他是篮球运动员,摆渡的老倌子是无论如何也赶不上的。不料老人不觉得快慢是个什么问题,扛上一条长桨,虽然跑得慢,离我们越来越远,但决不停下步来,追了一里,追了两里,追了三里,追了四里……直到我们一个个都东倒西歪了挂涎水了,小小的黑点还是远远地咬住我们。谁都相信,只要没有杀了他,他今天不讨回这三角多钱,即便挥舞长桨追到天边,断不会回头的。他一点也没有我们聪明,根本不打算算帐,不会觉得他丢下船,丢下河边一大群待渡的客人,有什么可惜。
我们无路可走,只有乖乖地凑了钱,由黑相公送上前去以绝后患。我远远看见老人居然给黑相公还找了零钱,嘴里大张大合,大概是骂人,但逆着风一句也没有送过来。
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位老人。清查反革命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的一支手枪成了重点追查的问题。枪是在城里“文化大革命”时搞到手的,打完子弹,还舍不得丢,偷偷带到乡下。后来风声一紧,怕招来窝藏武器的罪名,才由黑相公在过渡的时候丢到河里,而且相约永远守口如瓶。这件事是怎么暴露的,我至今仍不清楚。
我只是后悔当时太自作聪明,以为丢到河里就干净了。我们没料到上面不找到这支枪,根本不可能结案,相反,还怀疑我们把这支枪继续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完没了的审问和交代之后,好容易熬到了冬天,罗江苏水退了,浮露出大片的沙滩。我们操着耙头,到丢枪的方位深挖细找,一心想挖出我们的清白。我们在河滩上足足挖了五天,挖出了越来越阔大的范围,差不多在刺骨的寒风中垦出了人民公社万顷良田,就是没有听到耙头下叮当的金属声。
一支沉沉的枪,是不可能被水冲走的。沉在水底,也不可能什么人把它捡走。奇怪的是,它到哪里去了呢?
我只能怀疑,这条陌生的江不怀好意,为了一个我们不知道的理由,一心要把我们送到监狱里去。
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它的神秘,也才第一次认真把它打量。它披挂着冬天第一场大雪,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像一道闪电把世界突然照亮,并且久久凝固下来。河滩上有一行浅浅足迹,使几只白色的水鸟不安地上下惊飞,不时滑入冰雪的背景里让人无法辨别,不时又从我想不到的地方钻了出来,几道白线划过暗绿色的狭窄水面。我的眼睛开始在一道永久的闪电里不由自主地流泪。
没有什么人过渡。摆渡的不是以前那个老倌子了,换成一个年轻些的中年人,笼着袖子在岸边蹲了一阵,就回去了。 我猛回头,岸上还是空的。
P1-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