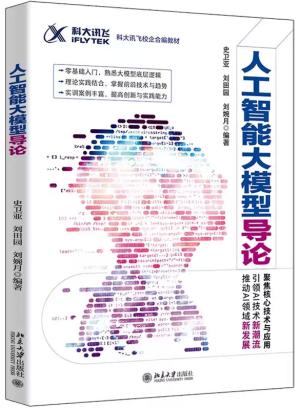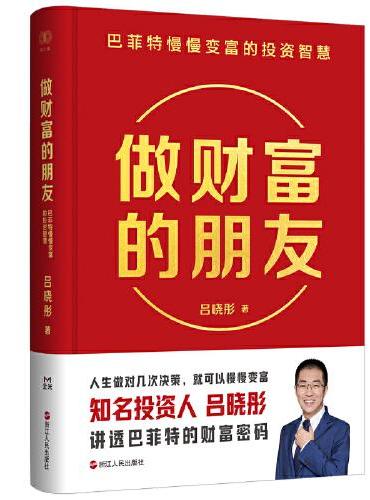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
》
售價:HK$
74.8

《
奴隶船:海上奴隶贸易400年
》
售價:HK$
75.9

《
纸上博物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诞生(破译古老文明的密码,法国伽利玛原版引进,150+资料图片)
》
售價:HK$
85.8

《
米塞斯的经济学课:讲座与演讲精选集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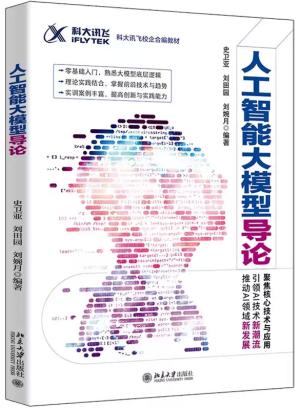
《
人工智能大模型导论 科大讯飞校企合编教材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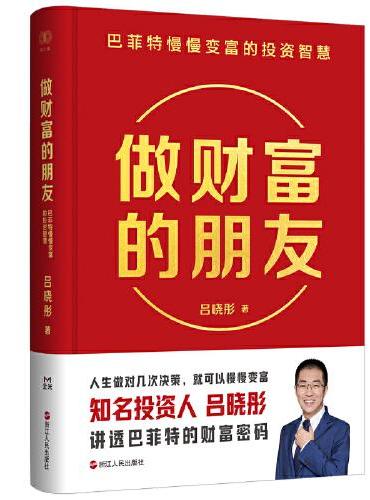
《
做财富的朋友:巴菲特慢慢变富的投资智慧
》
售價:HK$
82.5
|
| 內容簡介: |
沟口雄三先生的文章视角独特且广阔,别开生面,十分耐看,开启了日本学界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阶段。读他的书,一方面可以体味到他史学家式的材料严谨得甚至有些苛刻的态度,真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另一方面又可见出他那种哲学家式的宏观把握的魄力和高屋建瓴的气度。
本书前半部分的意图如下:自古以来,日本与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处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中。因此,往往产生这样的错觉:对同一汉字,两国亦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种错觉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汉学家那里表现得尤为严重,他们即便在读中国的文献时,譬如读到“天”,也只是把它作为日本的概念来理解,对于中国的“天”概念和自己的“天”概念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却不加以考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江户时代的汉学家将中国文献用所谓汉字训读作日本式的理解,即把汉文中国古典文化当作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通过中国文献研究中国。他们是作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的汉学家,却不是研究中国的学者。
上述情况一直持续到明治以降,实在令人感到吃惊。几乎直到现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在《文学》杂志上的尝试参阅参考文献,差不多是哲学概念领域日中比较的开创性工作。本书拟对此尽量简明地加以阐释。
后半部分的意图如下:谈起中国的思想,在日本最有影响的历来是孔孟、老庄。终宋之世乃至近代以降,朱子、王阳明稍有名气,然仅此而已,对其他的思想家就不得而知了。提起漫长的清代,甚至就在治中国思想史的专家中,也只存有一个“异族统治、思想迫害的黑暗时代”的形象,有关那个时代与近代革命思想之连续性的见解,则根本未能产生。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也有原因:对宋代以降之中国思想史的评述,历来几乎完全是以宋学的所谓理气论为中心的哲学史,而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便忽略了从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广阔视野中应能发现的连续性及展开的线索,从而又忽略了它们与清代思想的联系。
有鉴于斯,本书前半部分着重阐释诸概念的历史展开与联系,后半部分则进一步专力阐释宋至清末的思想史的连续性。作为比较,本书还将留出一定篇幅,探讨一下中国和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究意有何区别。
对于中国的思想,今后仍有必要在与日本思想及欧洲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凸显其特性。
|
| 關於作者: |
沟口雄三(1932—2010),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沟口雄三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中国的思想》《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的冲击》等。
赵士林,1954年1月2日生,吉林人。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8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李泽厚先生。曾任东京大学特邀研究员、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国内多所高校兼职教授,2004年被授予“北京市优秀教师”荣誉。兼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
学术著作有《心学与美学》《当代中国美学》《心灵学问》《荀子》《交叉的视野》《中国的智慧》《国学六法》等;学术译著有日本沟口雄三先生的《中国的思想》;主编学术文献:《中国学术年鉴》《西方美学史》(四卷)《美学百科全书》《基督教在中国》《黑春秋》《亚洲报告》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孔子研究》《读书》《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刊载学术论文近百篇;常在《新京报》《中国青年》《南风窗》《粤海风》“燕南网”等发表时评。
近年为北大、清华、人大、厦大、中大、浙大、中南财经、武汉理工等高校EMBA、MBA和中行、建行、厦门国际银行、申银万国、国信证券、中国移动、中航集团、恒信钻石等大型企业开设国学讲座;同时,受晋、冀等省府邀请与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主讲经济文化论坛,被称为“赵郎组合”。每场讲座均反响热烈,产生轰动效应和深远影响,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微博粉丝过万,被誉为“国学最佳教授”。此外,还应邀赴新加坡等国家讲学,受到新加坡、马来西亚企业家热烈欢迎。
|
| 目錄:
|
上篇
第1章中国的“天”上——与日本的比较
天的观念形成以前
天命观念的形成
与古代日本的比较
天与政治
天的根据性
天的条理性
日本的天道观与中国的生成调和的天
则天去私与道德?理法的天
第2章中国的“天”(下)——从天谴到天理
天谴论的形成
汉代的天谴论
唐代天观的变化
北宋天观的变化
天理性的天观
作为公理的天理
第3章中国的“理”(上)——与日本的比较
“理”这个词
日本的“理”
法与理
神与理
古学派的理观
第4章中国的“理”(下)——理气世界观
“天理”二字
理气世界观的诞生
理气世界观的结构
理气论的展开
走向理气一元论
天理人欲论的展开
肯定人欲的天理
作为社会性调和的理
情与理
第5章中国的自然
日语的“自然”
欧语的“自然”
中国语的“自然”
日语中的“おのづがら”自然而然
中国的“自然”的展开
吕坤的“自然”
戴震的“自然”
和谐的自然
第6章中国的“公”(上)——与日本的比较
公与オホヤケ
オホヤケ“公”的语源
“公”的语源
政治领域的オホヤケ与公
国家主义的オホヤケ与民族主义的公
公立与公有
ワタクシ“私”与私
第7章中国的“公”(下)
天下为公
宋代的公
明末的公私
清末的公私
《大同书》
多数国民的公与少数专制者的私
孙文的“大同”
下篇
第8章宋学的兴起
所谓“宋学”
宋学兴起的背景
王安石的改革
新体制的秩序观
朱子学的形成
朱子学的哲学特征
第9章宋学的发展
朱子学在日本的发展
日本对朱子学的吸收
近世社会的特征
朱子学的东渐
朱子学在日本的变化
日本社会中的儒教
第10章阳明学的兴起
朱子学的渗透
朱子学的体制教条化
明初的朱子信徒
修正朱子学的动向
王阳明的致知格物说
新圣人观
道德实践的平民化
道德实践主体的扩大
阳明学兴起的背景
第11章阳明学的发展
民众道德的扩展
无善无恶论的兴起
阳明学所完成的历史作用
日本的阳明学
大盐中斋的阳明学
西乡隆盛的敬天爱人
第12章16—17世纪的转换上——君主观的转换
与日本的比较
明末的君主观
新的君主观
民的自私自利与皇帝的大私
清代的变迁
第13章16—17世纪的转换下——田制论的新发展
井田论的传统
民土观基础上的新田制论
明末清初时期的田制论
清朝末期的田制论
土地国有论与公有论
作为中国近代开端的明末清初时期
第14章从清代到近代上——从“封建”到地方分权
作为时代标志的“封建”
明末清初时期的“封建”概念
地方官的当地论与地方自治
清朝中叶的封建论
清末的封建论
清末民初的连省自治运动
民国的“封建”
第15章从清代到近代下——“大同”的近代思想
近代政治思想的吸收
洋务官僚对议院制的关注
设立议院的舆论
革命派的兴起
辛亥革命与革命之后
孙文的三民主义
中国“大同”近代思想的特征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第1章
中国的“天”上——与日本的比较
中国的思想特别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见到的,从10世纪以降的宋代到20世纪初期的近代,非常重视天、理、自然、公这样一些概念。在这些概念中,“天”又特别地受到重视,被看成一个具有潜在力量的概念。所谓“潜在”,如后所述,宋代以降,“天”这一观念与“理”结合,甚且退而成为“理”的背景;但恰如近代以降的欧洲思想中,基督教之神的观念或与理性结合或成为理性的背景却仍有影响一样,中国的天的观念,一直也没有丧失它的影响。
天的观念形成以前
在中国,普遍认为天的观念形成于周代。在周之前的殷代,“天”字不过和“大”字意义相同,并未包含抽象的或超越的意义。就是说,“天”这个词在殷代和周代以降意义并不相同;换句话说,殷代所谓“天”还不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的存在。
殷人较之关注天,可说是更强烈地关注太阳。他们信仰这样一个神话:有十个太阳,它们每天每日地从地下升起,在天空中出没,十天轮流一次。这十个太阳的名字分别为日甲、日乙、日丙、日丁、……日壬、日癸,即今天所说的十个天干。和十个太阳相对应,地上也有十个王族,它们分别被视为十个太阳的子孙。这十个王族的族长轮流统治地上的世界,十个王分别崇拜一个作为祖先的太阳,将太阳信仰与祖先崇拜结为一体——就这一点来看,它与日本的天照信仰相似。但在殷人那里,更想象着还有一个掌管太阳的“帝”,这和日本的天照信仰就很不相同。在殷人的想象中,存在着掌管天空诸现象雨、风、云、雷等的上帝和掌管地上诸现象日月的出没、地震等的下帝。对天灾、地灾的有无或地上活动军事、狩猎等的可否,人们通过占卜而从上下帝那里获得明示。
殷文化就是基于对太阳的原始理解,以祖先崇拜、上下帝信仰及占卜为特征的原始文化。
天命观念的形成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以渭河盆地为中心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而兴起的周族,打败了东方的殷族,创立了周王朝。将这次王权交替,而且是异族间交替正当化的理由,就是天命观念,即西周青铜器铭文所载之周文王受命于天。另一方面,周文王之受命于天又与他的有德联系起来。这样,依据所谓对有德的周室授受天命的思维模式,周王朝就将自己的权力正当化了。
对这一天命意义上的天的观念在周族中是怎样形成并延续的,固已无法弄清,但却可以推测几个重要原因:诸如渭河盆地是适于农耕的肥沃土地,还有从甘肃传入的西方文化等,都应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周人对与农耕关系密切的天空的关注、西方一神教的影响乃至吸取殷人的上帝信仰等,都可能是形成天命观念的重要原因。总之,在中国大陆,与上帝信仰相结合的天命观念历来是王朝权力的背景。因此,在王朝更替期或皇帝的即位典礼上,都要举行祭祀天之上帝的盛大隆重的祭天仪式。
于是,从西汉文帝郊祀在京都的郊外筑坛拜天,表示该皇帝受命于天的仪式开始的祭天仪式,经武帝、宣帝、成帝,遂作为儒家倡导的国家仪礼而体系化;不久,在王朝更替频繁的南北朝时期,作为异姓间更替皇位之正当化手段的祭天仪式已走向普遍化;唐代以降,这种皇帝即位的仪礼更成为一种习惯性的活动了。
与古代日本的比较
在日本的古代,一般都奉行自然物信仰。天皇的权位依据所谓太阳神之子孙承续的血统观念而正当化。
天皇即位时,即位仪礼的中心仪式是天皇就位于高御座,这个高御座只允许天神的嫡系子孙就座。所谓天神就是太阳神天照大神。这样一种天神嫡系子孙继承皇位的观念到了8世纪以降,就已经在即位典礼上明文宣示,这显然与中国的受命于天的观念完全不同。此外,到了后世,在天皇即位仪礼的一环——大赏祭中,更出现了将新谷贡献给神的仪式。这一祝祷丰收的农耕的祭礼,如一般所谓“稻魂”这个词所显示的那样,应该说是自然物崇拜的遗痕。
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来和日本比较。中国古代,天文学格外发达,这是日本古代不可同日而语的。
文明古国,无分东西,天文学都很早便发达起来,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在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代,对农耕十分必要的历法及预卜事之可否的占星术,都已相当发达。在有关天体构造的理论方面,有汉代甚至更早形成的盖天说,更有浑天说,显示了理论的先进。所谓盖天说系指天与地上下平行并列的一种思考,所谓浑天说系指球形的天包围着平面的地的一种思考。这样一些天体构造理论的诞生,表明了古代中国人对天的不寻常的关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天上的自然现象与地上的政治活动具有密切的关系。
天与政治
可以《史记》之“天官书”为例,来说明天与政治的关系。西汉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撰《史记》,在与“礼书”“乐书”并称的“天官书”中记载了占星术及星宿的作用。从“天官”这一名称可以看出,天上也被认为存在着宫廷、官僚。在星座的名称中亦有大帝之外的三公、天相、天将等许多官名,这反映了汉代官僚机构的完备。但更直接地阐释了天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论,却是西汉董仲舒约公元前176—前104年著名的天人感应论。
这一理论认为天的自然现象与地上的人事互相对应。譬如,人有三百六十个骨节,正相当于周天之三百六十度;人的仁义与天的阴阳亦相感应等。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将自然的祥瑞紫云或珍奇宝物的出现或灾害水旱灾等与政治的清浊治乱联系起来的休祥灾异说。是即皇帝依天命统治地上的民众,如果其统治有过失而殃及民生,就会招致天之阴阳二气的不调,并通过灾害受到谴责;反之,如果满足天意有利民生时,就会出现祥瑞之象。其中将灾害视为天的谴责,将异变日月食等视为天的警告的天谴论,从汉代开始,历经隋唐直到宋代,一直为朝廷的政治中枢所采纳,影响着实际的政治运作。
这一将自然界的现象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滥觞于殷周革命之际形成的天命说。后来,如我们在《诗经》《书经》里看到的那样如在《诗经?小雅》之“十月之交”中,便有将日食的原因归咎于暴政的吟咏,在春秋战国时代广泛流行,再经阴阳家继承,终于由董仲舒加以理论化。因此,把天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与其说是出于某位思想家的个人创发,不如说是基于原始中国最深厚的传统,它不过是碰巧由作为个人的思想家董仲舒加以理论化而已。换句话说,把天与政治联系起来的政治思想,是在中国独自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思想,它在日本或欧洲均未曾出现。这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天的根据性
前述主宰的天,从哪个角度说也可以被看作拟人化的主宰者,但不应忘记,也还有与它并列的作为存在根据的天。
万物是根据什么而存在的呢?现在如此存在的事物是由于什么力量而如此存在的呢?这样一些问题,对于古代的人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问题。就人来说,生死寿夭是怎样被决定的,贫富贵贱与命运的反复是由什么力量所促成的,都是问题;就宇宙论来说,宇宙的始源是什么,宇宙万物是怎样生成的,都是问题。
古代有许多关于宇宙始源的哲学思辨。《老子》尝云“道生一、一生二……”的“道”或《周易?系辞传上》所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太极”等,便都是这样的哲学思辨。它们被理解为这样一些“形象”:作为超越的主宰者的“道”,或作为超越的实体的“无”,或作为混沌之气等。
后来,关于宇宙始源的看法又有王充的命定论的“自然”、唐代孔颖达的偶然论的“忽然自生”,这些看法都认为宇宙的根源是不可知的。
进入北宋以后,针对这种不可知论,周濂溪著《太极图说》,将太极视为气的运动本体。不久,南宋的朱子一语道破:太极是理。从而得出结论:宇宙的根源对于人是可知的,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天的条理性
上述之外,天又具有法则性,换句话说,也存在着条理性的天的观念。
天的观念原本就具有多义性,首先可以将其粗略地分成四类:①自然运行的天;②主宰、根源的天;③生成调和的天;④道德、理法的天。在这里,①之自然运行、③之生成调和、④之道德理法全都以条理为根底。
把天作为条理来理解的思想,多出于道家。
有关天为主宰的观念,在被视为周初文献的《书经?召诰》中载有:“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后来的《论语?八佾》载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孟子?告子下》载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那里流转传承。但与此同时,以儒家为中介,主宰的天开始与道德、理法的天联系起来。与儒家并峙的道家,则将天与道的观念统一起来。依道家的理解,天是超越人为的自然秩序,是最根本的理法,是即道家的条理意味的天。对道家这一天的观念,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譬如,《庄子?秋水》云:“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里的天与人,前者系指自然,后者系指人为。再如《庄子?达生》云:“不开人之天,而开天之天。开天者德生,开人者贼生。”这里的“人之天”系指狭隘的人欲等人的自然,“天之天”则指包含人的自然同时又超越人的自然的宇宙整体的理法的自然。在这些论说中,都赋予天比人更高的价值。对天的这样一种思考或态度,同样表现于《庄子?在宥》:“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道家的天道观在这里获得了直截了当的表现。这样一种排除人类作为,换言之即超越人为将天理解为自然条理的天观,不久亦为儒家所接受,由此而产生了《荀子》的“天人之分”的思想。
《荀子》的“天人之分”,否定天的主宰性、人格性,将自然界的天与作为界的人的世界区别开来。如其《天论》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表述的那样,他是完全否定了周初以来的天命观:天的自然运行有其独自的法则,和尧的善政或桀的恶政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以现代人的目光来看,将天理解为自然法则的天观,较之理解为主宰的、拟人的天观,肯定是一种思想史的进步。因此,后来汉代的董仲舒否定前者而主张类似后者的天人感应论,就或许会被视为一种退步。但如果这样看,却未必是中肯之见。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所谓自然法则,从理论上说只能归于阴阳五行说之类,而不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自然科学。此外,还应看到,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固然肯定了天谴论的人格性的主宰性的天,但同时也统合了基于阴阳五行说理解自然现象的自然法则,亦即条理性的天。在这一意义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应该说是对春秋战国以来主宰的天观与条理的天观的统一综合。
日本的天道观与中国的生成调和的天
这里要回溯的日本天道观念的流行,是15—16世纪战国时期的事。我们只能大略地思考那并不古老的往事。
这个天道有时也与“太阳神”或神佛并列,被作为道德或正义的依据。如果说和天观有什么联系,那么他属于这样一种观念:他是一种超人类的绝对的存在,对于人具有不可知的巨大力量,是一种裁判人类、人类又无法见到的存在。而中国的天观进入宋代不久,就已由“天即理”而强化了客观的法则性、条理性。前后二者显然是不同的。
准确地说,在日本的天道中也存在着道义、公正等观念,这与中国的道德、理法的天有相通之处。此外,在能够裁判人类这一点上也与主宰的天相通。和日本的天道观相比,中国的天观之最独特的思想创造,是有一个生成调和的天,特别是调和人的生存的天。
《庄子?达生》云:“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大宗师》云:“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样一种认为天之生成遍及万物而不偏的思想,并未表现出对人自身的珍视。然而,将其与《诗经》〈大雅?荡〉“天生烝民”之民为天生的看法联系起来,均等地成就民之生存的思想便展开了。这应该被视为中国独有的思想。
《礼记?礼运》所描述的“天下为公”的状况与“大同”之世的状况被视为一种乌托邦。但那里之无依无靠的老人、病残者、孤儿都能保证生存,人们不仅为自己打算,而是将货财、能力等与他人分有,表现出一种生存的均等的实现。在这里,“天无私覆”的天的均等关怀,已经不仅是公正的意志与普遍的惠及,而是表现了人之生存的具体的均等、均分问题。从这里已开始表现出中国的“公”与日本的“オホヤケ”的区别,有关“公”的问题暂不讨论。这里只想指出,在天的调和中包含着这样一种人的生存均等实现的问题,这在和日本的天的比较中,是值得注意的。
时代发展下来,明末思想家吕坤1536—1618年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世间万物,皆有所欲。其欲亦是天理人情,天下万世公共之心,每怜万物有多少不得其欲处……常思天地生许多人物,自足以养之。然而不得其欲者,正缘不均之故耳。”《呻吟语》卷五这里所说的“欲”系指生存欲、所有欲。本来,对于这些欲望,天是应该都能够满足的。而之所以多数人得不到满足,是因为存在着社会经济的不平等。这一生存欲、所有欲的社会均等化问题,在16—17世纪以降的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史课题。这和日本的天的观念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别。
则天去私与道德?理法的天
在日本的幕府末期,如大盐中斋“吾心即天”参阅第11章所显示的那样,向着人的内在化的天观念发展膨胀。西乡隆盛的“敬天爱人”同上,明治时期夏目漱石的“则天去私”等,都汲取了这种观念。这些“天”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要摒弃世俗的名誉、地位、财货等欲念,甚至清除有关世间事物的任何计较、打算,从而确立所谓绝对自我,将其作为人生目的。这里的天,是内在自我又超越自我的无限自我,亦即由天的无限性成就自我,即所谓天人合一的自我,因此有所谓“吾心即天”。这个自我还在自身中实现自然,就其完全抛却私欲和作为来看,这个自然也就是天之自然,亦即日本意义的“诚”。这样一种诚或自然本于天,它和中国的天相比,可说是极具日本的独特性。
在中国,诚啊、自然啊,也是与天相结合的概念。但是完全抛却私欲和作为的存在,在宋代以降,不是天而是天理。诚、自然等是标示天理纯粹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指向天理之外的独特境界的概念。
由诚或自然而形成的纯粹的天,在中国是天理,亦即道德、理法之天。总之,它应是遵循一种客观的条理。日本的诚与自然的天,与其说是客观的条理,毋宁说是纯粹主观的东西,是个人内在的心境,这是一个极大的区别。与日本的天相反对的客观的条理性,作为中国的天的特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