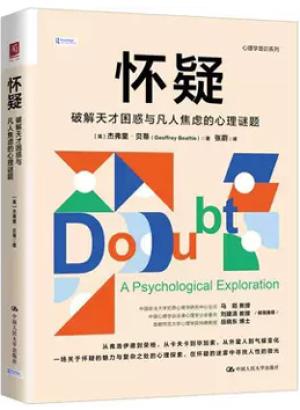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荷马社会研究(增补版)
》
售價:HK$
165.0

《
万千心理·与弗洛伊德的咖啡漫语: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精装】
》
售價:HK$
151.8

《
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 精装 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162.8

《
山中岁月:在日本小镇与传统相遇、与自然相融
》
售價:HK$
66.0

《
创伤自救指南:如何摆脱消极模式、修复人际关系并获得自由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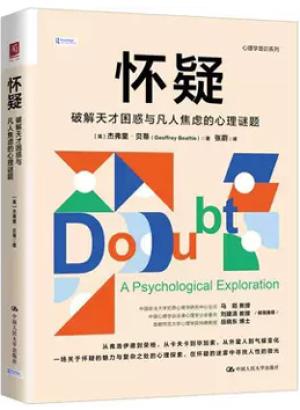
《
怀疑:破解天才困惑与凡人焦虑的心理谜题
》
售價:HK$
87.9

《
神圣的异端:法国中世纪纯洁派叙事研究
》
售價:HK$
107.8

《
甲骨文丛书·莫卧儿王朝的灭亡:德里1857年
》
售價:HK$
163.9
|
| 編輯推薦: |
1 首部以陆游和唐婉传颂千古的凄美爱情为题材的经典人物传奇。
将一段蕴藏在家喻户晓的《钗头凤 红酥手》中的南宋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承接《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口碑传颂。
2 恋爱虽易,婚姻不易,且行且珍惜!
因为爱情,所以会有悲伤。多少爱情回想时只剩结局和开始。不要等到人生垂暮,才想起俯拾朝花。
3 文字古典而不晦涩。
语言上采用了半白话的创作方式,颇有阅读《红楼梦》之韵味。
4 情节跌宕而不繁杂。
除却爱情故事,本书还花费大量笔墨描写了深院宅斗,以及几个性格各异的丫环与唐婉在磨难中结下的生死
情谊。这使得全书内容丰富好看,不输宫斗剧之趣味,并驾《甄嬛传》人艰要拆。
|
| 內容簡介: |
在绍兴这座水城,离鲁迅故居和三味书屋不远处,有一处极富江南特色的私人花园——沈园,乘着乌篷船可沿河而至。其历经岁月沧桑,至今仍得以流芳,全因一个千年不老的凄美爱情故事。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相传南宋诗人陆游与表妹唐婉青梅竹马,婚后原本举案齐眉、伉俪情深,但陆母不满儿子沉溺于温柔乡中不思进取,误了前程,唐婉又始终未能生养,于是逼迫孝顺的儿子休妻,终致二人劳燕分飞。此后,陆游另娶,唐婉改嫁。公元1151年春日,陆游与唐婉再次邂逅沈园。陆游触景伤情,在壁上怅然题下《钗头凤》两阕,唐婉见而和之,情意凄绝,不久后便抱憾离世。晚年陆游数度访沈园,哀痛至甚,多次赋诗咏沈园寄相思,直至终老。
曾经美好的时光,辗转缠绵的爱情,生死两隔的憾恨,最终只是泛黄史书中的篇章。再相见,已是戏文章节。
掩卷喟叹:爱恋虽易,相守不易,唯愿青山故人皆无恙,且行且珍惜。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陆游 题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唐婉 和
|
| 關於作者: |
|
高小潘,八零后天蝎座女子,亭亭而立,清扬婉兮。文则行云流水,武嘛——揍人时才算文武双全。喜红楼,善翻译。柔顺好养,极乖,欢迎欺负。
|
| 目錄:
|
第一卷 彼年豆蔻,谁许谁地老天荒
百千万劫以来,我是如何挣扎着趟过了流沙般的时光,又是如何才跋涉过茫茫人海,才终于蹒跚着,来到了你的身旁?
绿鬓朱颜,年少好时光
烟雨冥蒙,庭院深深深几许
东风初来,此意复谁解
红酥手下,满城春色
双眸翦秋水,唯他独爱绕指柔
第二卷 执子之手,只愿君心似我心
三生三世的守望,终于等来你的今生。在因果石上,刻上你我的名字,但愿从此以后,可以陪着你一起轮回。
凤钗为盟,东风欲障新暖
毕竟相思,不似相逢好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
执子之手,一寸愁思千万缕
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
第三卷 不如愿,人到情多情转薄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高堂不负卿
朝来寒雨晚来风
半笺娇恨寄幽怀
仲卿既已得罗敷
桃花依旧,乱落如红雨
第四卷 烟花易冷,此情可待成追忆
情未了,缘却已尽,原来,不是所有的情都来得及给予,不是所有的爱都来得及付出。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豆蔻梢头旧恨在
镜暗妆残,为谁娇鬓尚如许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
第五卷 天不老,情难绝
缘聚、缘散、缘如水,背负万丈尘寰,只为等待,下一次相逢。
人间四月,此处桃花始盛开
桥下春波,曾有惊鸿照影
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
独吊遗踪,美人已归
人间亦有痴如我
|
| 內容試閱:
|
第一卷 彼年豆蔻,谁许谁地老天荒
绿鬓朱颜,年少好时光
南宋绍兴八年,老贼秦桧二出山门,又任了宰相。秦桧人称老奸雄,为人既奸且狠,才到了任上便引得朝野动荡,一时间主动归隐的、被秦桧排挤出局的、受到他人牵连的官员不计其数,朝堂之上熙熙攘攘,那一番非同小可的忙乱!官员之中有一位贾先生,名怡字斋堂,原是个知府,此时一则不愿与秦桧之流鬼混,二则也深恐一朝受其陷害,坑倒了家中老小,因此赶着秦桧上任之初的忙乱辞官,只说要回山阴老家去。
秦桧此时也正忙着排除异己,见这位贾先生赶这会子辞官,便晓得他必然是个异类,如今自己请辞倒也好。因此也不论斋堂先生真回老家也好、假回去也罢,哄着皇上草草准了了事。
谁知这位贾先生原是个生性旷达不羁之人,岂肯从此拘泥于一宅之内、三五妻妾之中?交代过公事,将历年做官积得的一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安排妥帖,却是自己担风袖月,游览天下胜迹去了。
如此一年有余,这日才回到江阴不过三日,还未回家,却在酒肆之中闻得本地有一位名士唐闳,原也是大族出身,正是鸿胪少卿唐翔之子。这位唐先生膝下有一女,名婉,字蕙仙,不过十二三岁年纪,生得相貌楚楚,人也聪敏。唐翔夫妇膝下无子,所以对这个独生女儿十分珍爱,欲使她读书,能够识得几个字,因此欲为小姐聘一西宾,正四处托人寻先生。
这位唐小姐原本跟着母亲读过几年书,并非蒙昧无知的幼童,教起来倒也不算吃力;再讲她很有几分千金小姐的派头,身子娇弱,又不似男学生有进场科举的压迫,所以功课不限多寡,做她的先生倒也十分省力。贾先生听说,便托人谋了进去,果然待遇优厚,事体又不重的,因此一径做下来,如今已经做了两年光景了。
唐府上的夫人向来身子不大牢靠,肺上有些难好的毛病,这二年更觉得沉重。平日里妯娌们凑到一处讲闲话,因为妒忌这位能诗能文的唐夫人,又恨一样是唐家的小姐,为什么婉儿就生得这样好,自家的女儿就那样难看相,所以总归要用唐夫人做由头,笑嘻嘻地说:“二嫂嫂的毛病也蹊跷的,缠缠绵绵地搞了五六年也不好,难怪生不出儿子,只有一个婉儿。那小姑娘如今也是一副病面孔,不晓得是不是叫她娘过了病哦。”
另外一个细声讲:“婉儿本来身子也不大好,针线活又不会,生的么一副薄命面孔。再叫二嫂嫂过了毛病,将来不要出嫁了噢。”说得众人大发一笑,手里摸着牌九,嘴巴上讲着闲话,都觉得蛮解气的。这话辗转传到唐夫人耳朵里,难听是难听的,生气也是生气的,可也算得上一记警钟,她自此便留了心,时时谨慎、处处当心,生怕把毛病过给女儿。况且女儿如今又大了二岁,男先生女学生终归不大好,弄不好又给人家讲闲话,女儿如今差不多算与陆家表兄定了亲,给婆婆家晓得了将来也麻烦。因此与唐老爷商量,不再请先生教习,送了女儿去城中一位同宗的姑妈家去客居几日,待唐夫人好些了再回转来。
唐婉这位姑妈夫家姓陆,在江阴也曾经算得上是个大族,只是这二三十年因人丁不旺,所以渐渐衰微了。只因陆府上也有读书的公子小姐,如今西席告老,正欲再聘新先生。况且教男学生终归和教小姐不同,男学生是要进场考试的,果然能够金榜题名,先生的身价自然水涨船高。所以唐翔打算请斋堂先生与唐闳一道送了唐婉去,也是把他荐给姑丈家、替他谋一番前程的意思。贾斋堂自然谢之不迭,领了荐书,便勤勤恳恳地跟着唐家父女走了。
陆家虽不敢说是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倒也算得书香门第、诗礼世家,现今的家长陆宰原为京西转运副使,十二三年前因靖康之变遭了罢免,只得带着家眷、仆妇一众人等往江陵的岳丈家去了,如今才回原籍三四年光景。
陆夫人原为江陵唐介之孙女,也是大家小姐出身,虽说不曾上过几年学,只些许认得几个字,生的么又是一副没啥颜色的寻常面孔,可倒也算得上宽怜体下、谨言慎行、治家威严,更有乐羊子妻停机之德。
陆家如今支庶不盛,子孙有限,虽有几门亲眷,却俱是堂族而已,并无亲支嫡派的,几房妻妾也只有陆夫人膝下有一子务观,另外四房姨奶奶,只有前面两位各养了一位小姐罢了。足见陆母治家严格,姨奶奶皆不敢出头。
贾斋堂在路上问唐闳:“陆夫人原为江陵人士,贵府上却是江阴本地的原籍,想必本不同宗,再讲他们又算不得高门大户,做啥要与他们攀亲眷呢?”
唐闳呵呵笑道:“虽说并没有同族连枝之亲,可是两家的祖辈曾一同在京里为官,有同僚之谊,所以渐渐有了来往,颇为投契,这才认了同宗。两家的小辈便以姑伯姊妹地相称,当做亲眷一般走动。如今这位陆夫人很信神佛,因她一贯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家下女眷虽都略识几个字、会读几句书,却不敢出头,只推不认字,她便常央了拙荆替她抄写经文。拙荆娘家与他陆家原本就有祖上的情谊,如今又往来密切,儿女便对我们以姑舅相称起来了。”
贾斋堂点头道:“原来如此。只是听老先生说起来,那陆家正室只有一位公子,两个年幼的小姑娘都是妾室所出,咱们家蕙仙小姐去了,自然不好与表兄同进同出的,可是二位表妹妹,身份似又嫌太低呀。”
唐闳道:“斋堂先生不晓得,他家的那位公子比小女只大了一岁光景,从小虽不很常见,可却像上辈子有缘似的,见了面总归十分亲热的,倒恍如亲兄妹一般。婉儿又是个十分爽气的小姑娘,和表兄要好,便总吵着要往陆家去,并不晓得避男女大防的嫌疑。其余几位小姐如何我倒不大晓得了,上趟见面还是两三年前。我忖着,如今她们也都大了两岁,都讲女儿像娘,听我夫人讲,她二人的娘年轻辰光都是绝色,性子婉约伶俐,女儿自然也不会逊色罢。”贾斋堂深知这唐闳亦是倜傥不羁之人,如何会注意这等微末小事?口中自是称是不迭。
二人说着话,又走了一时,便到了陆府。门房的人见唐家的人来了,都忙接着,那一派殷勤小心自不必说。及至进去,才走了不远,轿夫便停下不走了,自有三四个穿戴得齐齐整整的小厮上来替唐小姐抬轿子。早有人引着唐闳和贾斋堂二人往陆老爷书房去了,看他们走远了,方出来三四个婆子,跟着小姐的轿子往内宅去了。
这唐婉小姐原是冰雪聪明之人,往日在家时,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任意,言语亦可不避。香车画舫,红杏青帘,唯我独尊,原是自在惯了的,她爹娘也不肯拘束了她。如今见陆府上这情状,便知必是那等家风严谨的所在;况且她过去在家时,曾听母亲说过这位姑母治家极严格,因家里有两位小姐,所以仆妇们所生的那些略大些的小子便不许进内室,若有违反者,一概重罚。她家里两位妹妹平日里跟着母亲去做客,都不许大说大笑的,更不许与亲眷家的兄弟说话。姑母这些规矩大异于唐家,因此那唐婉暗暗谨记,从今往后寄居陆府倚松而栽,必要谨言慎行,照着那两位表妹妹的样子说话做事,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以免招姑母厌弃。
第五卷 天不老,情难绝
人间亦有痴如我
一时士程赶来,只见那唐婉直挺挺躺在床上,手足冰冷,双目紧闭,唯口鼻之处尚有一丝气息而已,士程是经过父母之丧的,稍微看看就晓得唐婉大限已至了。再看看,珍珠和小翡翠伏在唐婉身边痛哭,凄惨不可名状。
来仪见士程来了,先迎上去道:“少爷别心急,奶奶兴许也只是一时昏厥呀。”士程晓得她见多识广,此时听她这话讲得委婉镇定,自己也心定了些。来仪又上前挽了珍珠的手,和和气气地对她讲:“珍珠,少爷来了,你不要哭了,快点起来呀。”珍珠倒也肯听她的话,果然起身,士程便坐到唐婉身边去了。小翡翠在唐婉身边这一年日长夜大,此时也是一位豆蔻少女了,看见士程坐过来,登时便涨红了面孔,连忙揩揩眼泪起身,立到珍珠身边去。
士程坐下来,又把唐婉的面孔细细地看了一遍,心里难过,颤抖抖地问珍珠:“你奶奶白日里还好好的,怎么才几个时辰工夫,突然就这样了?”
珍珠此时哪敢说是因思念务观之故?只得忍悲道:“也要怪陆大爷实在莽撞,明明晓得小姐身子不好,还要对她讲乌头死了的事体。赵姑爷您也看到的,小姐当时面孔就变颜色了呀。后来上车,我就对她讲,乌头虽然死得冤枉,可是小姐那会子到底没有亏待她,奈何她命薄,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呀。可是偏偏我们小姐看陆家老爷太太这般狠心,不由又想起那辰光自己受的气来,凭我说什么,她也不睬我,只是落眼泪。后来回到家里,她就嚷肚皮难过,身子底下又不大干净了,临睡前还换了一回衣裳被褥。到了夜里,我见小姐睡了,就想靠着她迷糊一会子,谁知梦里竟听见小姐与乌头说话。我只当是乌头舍不得小姐,显灵了,或者小姐把哪个丫头认错了。哪晓得等我起来看看,房里并无他人,只有小姐一个人在那里自己对自己讲话。我听她讲的倒也还通顺合理,仿佛真有个乌头在身边似的,把我真正吓煞。后来她就喊累,要和乌头躺着说话,一躺下便昏厥过去,气息也微弱了。我哪里还有主意,只好赶快请了姨奶奶来呀。”
来仪听见唐婉与乌头说话,便有几分疑心,暗忖道:“都讲死人接死人,奶奶既与乌头那般好,兴许是那乌头来接她了。再或者乌头以为自己是为了奶奶冤死,后悔了,所以来索命。”想到这里,凭她怎么见多识广,也觉得吓丝丝的,因问:“奶奶与乌头说点什么,你可听见了?”
珍珠哭道:“当日在陆家时,因太太喜欢乌头,有一次开仓库,看见里头还有些昔日老爷当官时候攒下来的好料子,便叫乌头去挑几匹。乌头原是个识货的,什么也不要,只捡了四种颜色的‘软烟罗’,回来给我们奶奶做了一条雨过天青色的裙子,她自己做了一条秋香色的,穿上了,难得的雅致清逸。她二人时常换着穿。方才奶奶与乌头就是在讲这两条裙子。”
来仪听了,又不似阴灵索命,不由暗叹一声乌头好忠心,因抚慰珍珠道:“只怕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奶奶想念乌头过度,所以一时神智不大清爽,你不要害怕。”
士程听她们这样一来一去地讲话,心里其实晓得唐婉还是为务观伤心,嘴巴上却不肯说破,叹口气顺着她们讲:“婉儿也曾对我说过那乌头,听讲是个不可多得的聪慧女子,对婉儿又忠心,不逊于她家里带来的人。今日务观实在有些鲁莽,竟直直地告诉婉儿乌头死了,婉儿身子本就不好,乌头死得这样冤枉,告诉给她,自然更加折损她了。”说罢,摇头长叹,半日又落眼泪,道:“婉儿就这样苦命!白受了一年多的气,如今在我们家,福还不曾享过几日,偏又叫务观往她心窝里捅了一棍子。”引得珍珠和来仪愈发痛哭失声。珍珠是个没主意的人,过去在陆家便是依靠乌头,如今在此地便依靠来仪,此时见来仪哭得这样痛,晓得唐婉是没救了,不由神智也有些昏乱起来。
那来仪落了会儿眼泪,忽然醒悟道:“今日我们收拾了东西走时,曾路过一块好大的影壁,上头提着两首《钗头凤》,都是新墨,仿佛后面一首是与前头相和似的。后来我听他们说前头那首是陆大爷写的,咱们奶奶回家时经过,看到了,便下车来和了一首,奶奶向来是不肯张扬自己的才学的,所以一写好便上车走了。后来我去看了,真正是难得的好句,我就随手抄下来了,兴许倒是个线索。少爷请看看。”士程听了,便命来仪拿来。
士程看时,只见: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句子不过是尚可,难得的是情真意切,使人观之泪下。士程不由哭道:“凤头金钗原是婉儿与务观兄的定情之物,所以他们都以此为词牌。婉儿心地纯良的,陆家人那般待她,她仍不肯说婆母小姑不好,只一味忍气吞声。如今既嫁入我家,她虽思念务观兄,可为了我,仍肯‘咽泪装欢’‘瞒,瞒,瞒’。我娶到这般万里挑一的贤妻,理应开心的,可是如今她命悬一线,只怕她嫌弃我,一时狠心舍我而去呀。”珍珠和来仪听了便又哭起来。
这时只听见床上有微微的声响。他三人忙止了哭声,一起围上去看时,只见唐婉星眸半开、朱唇微启,仿佛有话要说似的。珍珠忙凑上去,连叫了几声“小姐”。唐婉微微点头,又拉了她的手道:“好姐姐,难为你跟了我这些年。”说罢,两行眼泪直流下来。
珍珠听见这一句话,便知唐婉必死了,愈发哭了起来。唐婉摇摇手不叫她哭,又道:“我死了,你别叫咱们家里知道,也别回去,就在此地跟着黄姨奶奶过罢。能瞒一日是一日,就算是成全我的孝心。我爹娘只有我一个,若晓得我死了岂不痛心。”说到这里,气喘吁吁,垂下手来合目歇了一会子。珍珠和来仪听她方才那一篇话,早哭得气梗声噎了。幸而士程拍着哄着,叫她二人不哭,又爬上床去叫唐婉,问她可还有什么话。
唐婉便又勉强睁开一双妙目,对士程道:“士程兄,谢谢你了。我原是死过一回的人,所以更知你难得,难得你待我这样好。”摇摇头又叹道,“你若是因贪爱美色或是为子嗣计,所以才待我好,倒也罢了,普天下男人善待女子,大多是因这两条,并无稀奇之处。难得你最仗义,我如今病弱之人,并无色相,更不能生子,你却三媒六聘的娶了我回来。自此你受了多少闲话?你却任人诽谤,一概不入耳的,只管善待我。如今不是我临死讲一句后悔的话,倘或当日务观兄能有你一半,或者我初嫁便嫁入你家,我也不至得这个要命的毛病,年纪轻轻便断送了自己。”又喘息一回,微微带上一点笑影,又道:“俗话说的,初嫁从亲,再嫁从身。虽说我这趟仍是我爷娘做的主,可到底也是我愿意的。”说罢,也滴下泪来。
这士程原来一直以为唐婉不过是为替爹娘争气才嫁与自己,其实心里仍牵记务观。今日听她这话,方知她是个知己,竟能这样体会自己的用心,临别之时竟说出这样一番体己话,讲明她是愿意的。他原本就有十二分的不舍,此时愈发大恸起来,搂着唐婉落眼泪,哽哽咽咽讲:“你既知我好,为什么还不留下?”又叫着乌头道:“婉儿从来讲小姨奶奶好,今儿听说小姨奶奶去了,她比殁了亲姐妹还痛。你果真与婉儿要好,为什么要索她的命啊?”来仪和珍珠乃至底下一干小丫环听了,无不动容,都一起哭起来,一时房里愁云弥漫、泪雨倾盆,好一派昏惨惨的景象!
那唐婉说了几句话,便又合目躺于枕上。士程这番话她竟闻所未闻。士程只当她闹乏了,便不许来仪等人再哭,好叫她静静地歇息一会子。一时众人都静悄悄的,忽听唐婉道:“乌头,你可来了,我正等你呢。”众人忙凑近了看时,只见唐婉已经醒了,脸上不似方才那般惨淡了,倒有了几分鲜艳颜色,便知她大限将至了。来仪珍珠愈发痛哭,那士程只目不转睛地看在唐婉身上。
只听唐婉又道:“我方才已与他们一概别过了,若再别一回,反使他们更加伤心难舍。不如这就随你去罢!”说罢,又转向士程,含笑道:“士程兄,承蒙你一向待我这样好。如今我随乌头去了。兄长有所不知,天上原缺一个司掌海棠花的花神,所以才召了我们乌头去的。如今听讲翡翠也做了桃花花神了。今日我去,也是做花神去的,专司芙蓉花。你们倒不必舍不得我。”说罢,长吐一口气,便合目不语了。来仪上来看时,已经芳魂离体、气绝而亡了。
士程扑上去看看,只见她面色如生,且反褪了病容,愈发鲜妍起来,不由伤心难耐,搂尸大哭一场,来仪好歹劝住了他,便有珍珠上来与来仪一起替唐婉换衣裳。士程在一边看着,抽泣道:“这大红织金与宝蓝闪银的衣裳虽华丽,只是不大与婉儿相配,倒不如婉儿那套绛紫色绣嫩荷叶的长衣裳好。也罢了,且把你们预备的这两件穿在里头,外头再套一层罢。”珍珠答应一声,忙把士程所说的衣裳拿来,来仪便替唐婉换衣。
士程又命家下众人:“如今奶奶去了,我虽不敢说厚葬她,到底也要尽我的心力。奶奶在时曾说不许叫唐府上知道她的死讯,所以咱们不好铺张,只是装裹棺木一概要用头等的,且多多地放首饰珠玉。”众人自然应了,从此尽心下力,按士程吩咐办事。那珍珠因唐婉留下话,不许她回唐府去,她便自愿往家庙里去,从此带发修行,替唐婉守灵。
果然士程办事严谨,且严命家下众人不许说唐婉的事体。因此直到这一年秋天,唐、陆二府方知唐婉已死。原来唐婉自嫁入赵家门,便时常归宁,远不似在陆府那会子拘束。如今唐婉既去,士程便只好编出“家里来了一位老仙人,替婉儿看病,说婉儿须得九九八十一日不见外戚,毛病方可大好”的话,命来仪去对唐家禀报。因士程待婉儿极好,来仪又贤惠,唐老爷唐夫人倒也肯信。谁知到了这年八月十五,那唐母又念起婉儿来,疑疑惑惑地讲:“如今八十一日已过许久,却仍无婉儿音信,是何缘故?况且今日是三五之日,婉儿便是今儿不得回来,明朝也该回来瞧瞧才是。倘或她不来,我是一定要去看看她的,虽然讲赵姑爷待婉儿不错,可当日游儿不也是待婉儿好的?俗话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畏井绳,我是怕婉儿又落入龙潭虎穴呀。”唐老爷听了,也深以为是。果真次日唐婉未到,第三日一早,老夫妇二人便带了仆妇,坐车到赵家来寻唐婉。
士程见唐氏二老驾临,便晓得唐婉之事再瞒不过了——当日唐婉虽留下那样一番话,可到底算不得什么瞒天过海的妙计,不过是能捱一时是一时罢了。如今唐老爷唐夫人上门寻女儿来,可见此事在外人看来也是蹊跷的,再掩饰不过去了。士程只得回明了此事,又有珍珠和小翡翠出来替士程作证。
唐氏二老这一悲痛可非同小可!幸而有珍珠在身边信誓旦旦地讲:“赵姑爷和黄姨奶奶待小姐都是极好的,小姐死的那会子说,倘或当日初嫁之时老爷太太便将她许配给赵姑爷,她如今想必已经儿女绕膝、定定心心地做夫人了。”唐家二老深知珍珠老实忠诚,此时听她这般说,倒不像替士程开脱,想必婉儿当日过得是好的,只是婉儿命薄,没熬过病去。这方心里开解了些。
士程因想着唐氏二老仅唐婉一个独养女儿,如今女儿既去,他们依傍谁养老?因苦劝他二人到自己家里居住,就当做府上老爷太太一般看待,自有来仪日日如侍奉公婆般殷勤小心。且士程又接了珍珠回来服侍,唐老夫妇方勉强开解痛苦,相携苟活度日。
然而那唐老爷是不羁阔朗之人,实在熬不过丧女之痛和对陆府的憎恨,到底去了陆府一趟,细说务观懦弱、陆母严厉、陆父昏聩、绿玉歹毒的罪状,倒说得陆老爷陆夫人都讪讪的,务观更是羞愧难当,唐家二老此举算是替婉儿鸣冤,且与唐家门豪爽大方、不拘小节的门风十分契合。
再说那务观,此时虽已是二子之父,却只一心一意念着唐婉,对王氏倒淡淡的。他才得知唐婉已死时,心里难免悲痛异常,后来听到“词曲相和,泪尽而死”的典故,又听了唐婉与乌头上天司花的传说,别人都说做了天神也是个上好的结局,唐婉这般归宿,务观也该开解了,谁知他的心境反而愈发凄凉起来,因长吁短叹地道:“原来婉儿对我这般有情义,士程兄对她再好,也是得着她的人,得不着她的心。只可惜这样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原该夫妻恩爱、福寿双全的,却因嫁了我,生生落得个遇人不淑、英年早逝的结果。”说着便落下泪来,那王氏虽百般开解,他却只是听不进去,每日里翻来覆去地伤心,难能释怀,从此将唐婉当做第一知己,日夜思念,且终年在窗前供奉芙蓉花。
四十年后,务观以七十五岁高龄重游沈园,其实心里也晓得是不该去的,自打岁数大了,这几年他已去过沈园许多次,再去一趟又何必?况且这样多年过去,昔日那个人早已香消玉殒,把她藏在心里也就罢了,何苦再为她伤害了身边举案齐眉许多年的人呢。可到底年事日高,这趟再不去,只怕这一世就再也与沈园无缘了,务观却不过许多年的思念,终究还是去了。
去了才知,倘或没了那个人,沈园也不过就是沈园罢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地方,老眼昏花的务观实在找不到当年唐婉留下的芳踪了。
离去之前,他留下了那篇最著名不过的《沈园二首》,当做他对心上人最后的悼念。
他这样写:
其一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其二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
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很多看诗的人都说这两首诗写得淡而又淡,笔力反不如当年的“红酥手,黄縢酒”,难道是许多年过去,务观已把唐婉忘了?但也有人说这两首诗于平淡中透出深刻的哀思来,若不是思念之情在心尖上碾了几十年,务观断不能写出这样让人越读越痛的句子来。
后人的评价,务观不会挂怀,他写诗,也不过是实在熬不过相思罢了。
公元1210 年,务观寿终,时年八十六岁。留下一首《示儿》传世,他说:“但悲不见九州同”,仿佛这只是他人生唯一憾事似的。后人奇他为何只字不提那个女子,却不知对务观而言,与其把唐婉留在这俗世上被后人当做一桩风流艳事,倒不如清清静静地把她藏于心底,从此尘封在他一个人的记忆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