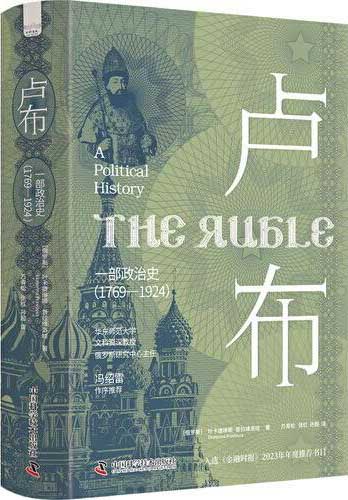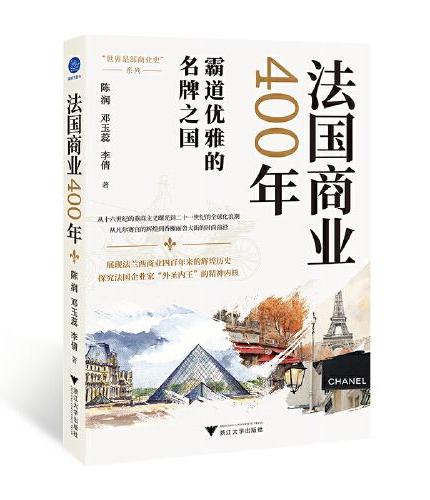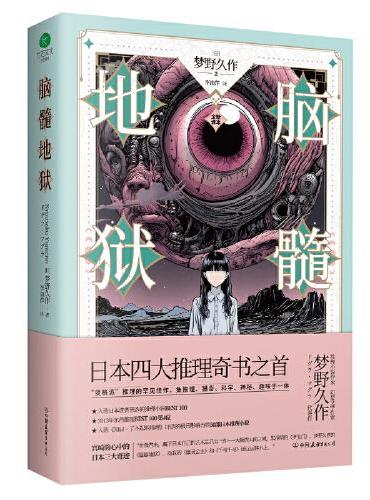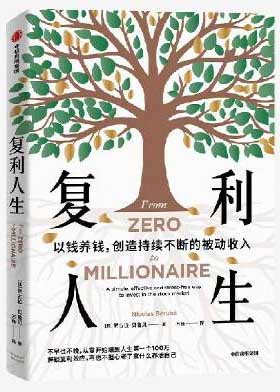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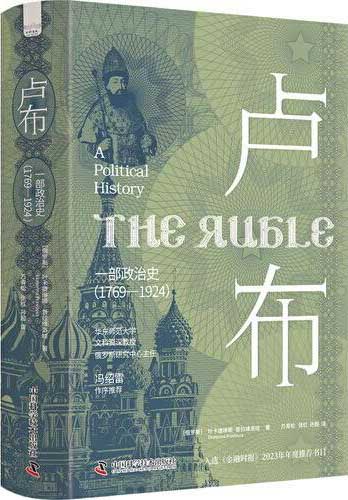
《
卢布:一部政治史 (1769—1924)(透过货币视角重新解读俄罗斯兴衰二百年!俄罗斯历史研究参考读物!)
》
售價:HK$
11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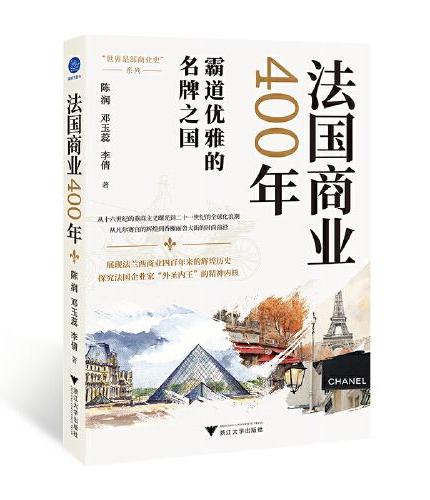
《
法国商业400年(展现法兰西商业四百年来的辉煌变迁,探究法国企业家“外圣内王”的精神内核)
》
售價:HK$
74.8

《
机器人之梦:智能机器时代的人类未来
》
售價:HK$
7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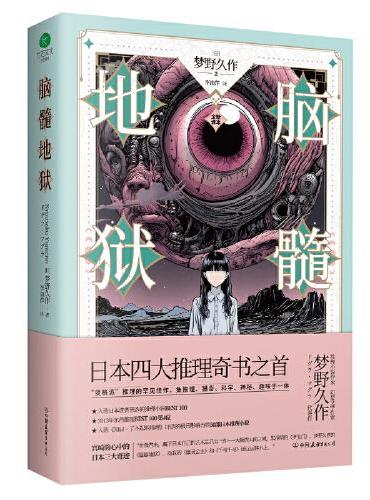
《
脑髓地狱(裸脊锁线版,全新译本)日本推理小说四大奇书之首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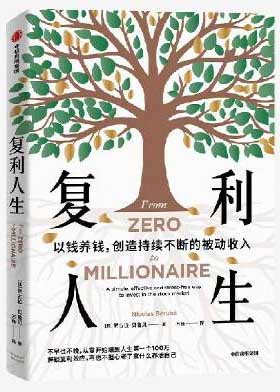
《
复利人生
》
售價:HK$
75.9

《
想通了:清醒的人先享受自由
》
售價:HK$
60.5

《
功能训练处方:肌骨损伤与疼痛的全周期管理
》
售價:HK$
140.8

《
软体机器人技术
》
售價:HK$
97.9
|
| 編輯推薦: |
从历史看现在,因现在想起历史
揭秘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历史演变,亲历朝堂内外的阴谋与阳谋
还原你所不知道的官场假面,揭露史实之外的另类真相
官场"闹鬼",大师"装鬼",历史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卸下假面,抛弃伪面,究竟是权术书写历史,还是历史被政治玩坏?
朝堂内外,阴谋阳谋,贯穿中国两千年官场的"关键词"重新演绎。《张鸣说历史:朝堂上的戏法》说的是朝堂,折射的却是大国的兴衰与蜕变。
|
| 內容簡介: |
张鸣说史,总能化繁为简,睿智,明白,让人眼前一亮。——吴思
张鸣的文笔是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梁文道
张鸣的文章,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易中天
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学者李零
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陈丹青
|
| 關於作者: |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个性鲜明,在嬉笑怒骂中藏着严肃的悲悯之心。社会责任感使然,张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为历史与当下人物事件揭下虚华假面,使真相豁然,真知毕然。
主要学术著作有《重说中国近代史》《辛亥:摇晃的中国》《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历史文化随笔有《历史的坏脾气》《中国心绞痛》《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等。
|
| 目錄:
|
目 录
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002
帝王的“封神”怪癖005
来自古代的超能力008
不懂规矩,不能成好马012
庭院深深深几许015
真话全不说,假话不全说019
天子门生的得与失022
门客列传026
少年得志与老年得志029
京官的生财之道033
百用全才是书生037
钱谦益和柳如是的风月韵事040
文曲星的家族史043
曾国潘和刺马案047
三白饭与三毛饭051
权力史中的倒影
沐猴而冠的政治游戏056
当“进化论”沦为统治工具059
当“孝道”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063
再谈官本位067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一)069
古代地震那些事儿(二)073
古代法制演变076
神经过敏的掌权者079
农民起义者的国家意识082
还原历史的价值086
正史的外表,野史的的里子089
万民伞“庇护”下的父母官092
鬼界的人间镜像095
送礼“哲学”098
观棋必语真君子101
世说新语浮世绘
鸡同鸭讲的巴别塔困境106
兽性与人性百相109
我所知道的对牛弹琴112
作弊与反作弊的历史考证115
“祖宗”去哪儿118
造假派大师的名利场121
今之名片,古之“明骗”123
东北的“人性化”演变126
也谈大城市户口限制130
后殖民时代的东方明珠133
梅兰芳的戏骨136
叶问如镜,照亮族魂140
常谈常新话赤壁143
“性”的遮羞布147
进化论视野下的代际对立152
激情燃烧的禁令155
择偶方式大起底159
今昔婚姻自由论162
放养、圈养,孩子教育的困境166
谣谚里的北大荒169
朝堂下的人事情
难得糊涂才是福174
读书最快的人177
我的完人朋友180
老板式文人183
朋友圈,圈朋友186
性情中人的直脾气189
海归文人的世情192
侠骨柔情汉195
大隐隐于市的文人198
“漂来”的学问201
环保疯子——汪永晨204
电视精灵——李蕾207
桀骜不驯的韩寒210
肚里有货,落纸有墨215
我与命题作文219
求知若渴的年代222
我被学校开除了225
我与《读书》230
|
| 內容試閱:
|
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
帝王排场虚荣政治学
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称帝称王,都要讲排场。就是泥腿子翻身,黄袍加身,称孤道寡,也一样。难怪当年跟陈涉一起刨垄沟的伙计,见了造反的陈涉要惊叫:“伙颐,涉之为王者沉沉!”其实,陈涉这点儿讲究,不算什么,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仪仗要排出几十里,这边进了王府,那边还在城门外呢!
最能讲排场的皇帝,要数隋炀帝杨广。他父亲杨坚,虽说小舅子鹊巢鸠占,天下取自北周的孤儿寡母之手,没费刀兵,但却懂得勤俭持家的道理,日子过得相对抠门儿,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好不容易挣下个大帝国来,谁想天下落到儿子手里,手脚大得不得了,好像这个皇帝当起来,就是为了花钱,不,糟蹋钱的。大兴土木,广修宫室,里面塞满了各处来的美女,自己坐上羊拉的车,走到哪里,随幸哪里的美女。这种把戏,西晋武帝司马炎已经玩儿过了,隋炀帝一试,也就够了,他要出去走走,让四边的蛮夷之人,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威仪。
就这样,隋炀帝在位那些年,每年都要出行,或者游幸,或者巡边,或者督师征讨,每次都排大阵仗的仪仗,数十里长。队伍里不仅有卤簿、舞乐,而且还有别的皇帝没有的和尚、尼姑、道士和女冠(女道士),以“四道场”自随,大概是边走边让这些出家人为自己念经祈福。这一套流毒甚广。直到民国期间,有钱人死了娘老子,大抵还是要安排“四道场”念经超度,排不出四队人马,就让人看不起。
破落贵族项羽发了,好好的阿房宫不住,立刻要回家,说是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漂亮衣服白穿了,显摆富贵,显摆给家乡人看。无怪乎当时就有人讥笑这个西楚霸王,说是楚人没出息,沐猴而冠。人家隋炀帝杨广就不这样想,他的排场主要给外国人看。只要巡边,就一定设法招引边外的胡人来瞻仰汉皇天威。第一个节目,就是参观皇帝的仪仗,第二个节目,奏九部之乐,演鱼龙之戏,把自家的宫廷乐队和舞蹈队,统统派上用场。最后一个节目,最惬意,就是皇帝散钱,来者有份,玉帛金珠,毫不吝惜。为了配合皇帝的排场,在哪儿“演出”,哪儿就得打扫得干干净净,装饰得金碧辉煌,仕女穿上最好看的衣服出来,连车马都得漆得耀眼锃亮,马头上要扎上花,尾巴要编上辫子。总之,来的外国人只能有一个感觉,中国皇帝的排场大,中国有钱。
排场的皇帝,在都城接待外宾的时候,更是排场。知道的人,能来看看,都会来,陆路海路,相望于道。每年正月里,是各国使节和番客集中的时候,因此,皇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起,一个月内,都城洛阳,全城街道,路两旁的树上,都要用彩绸结成花球,处处张灯,昼夜不息,皇城前面的端门街,天天上演百戏,不是后来那种有情节的戏剧,而是杂耍和杂技,成万的乐者奏乐,丝竹之声,声闻几十里以外,张灯结彩,灯火通明,全城不夜,钱花得就像流水一样。
当然,排场里面,也有不用皇帝从国库掏银子的好事。为了向外人证明中国的富庶、国人的好客,隋炀帝还下令,凡是城中的店铺,一律装饰得漂漂亮亮不说,凡是来吃饭喝酒的番客,任其酒足饭饱,不许要钱。过后皇帝给补偿吗?不给。负担不起了,想要关张,对不起,不行。借钱也要撑住,否则,有碍国家形象,吃不了,兜着走。只要能换得外人的惊叹、夸赞,再大的代价,也值。
来到中国,足吃足喝,还能带走大把礼物的外国使节和番客,虽说都是化外之人,但奉承话都无师自通,一点儿都不吝啬,变着花样,成筐成筐地说给通事(翻译),传达给皇帝大人。反正说好听的,没有什么成本。他们都知道,中国皇帝下了这么大的本钱,要的就是这个。
不过,老实人哪儿都有。还真就有番客指着树上结彩的绸缎对接待者说,我来的时候,也见过中国有不少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什么不用这些去救济他们?不用说,说这样话的人,此后的接待,自然而然就被怠慢了。活该,谁让这些人不识趣来着!
从来跟国人虚荣心最匹配的,都是外人的表扬,当表扬变成奉承,这边的虚荣也就升了级,为了得到这种奉承,对于爱虚荣的人来说,花点儿银子,什么时候都是值得的。
帝王的“封神”怪癖
中国文明发育得早,有文字的历史长,留下的文字多,因此弄文字的人也多。为政者,处理公务,实际上多半是在处理公文。秦始皇做了第一个皇帝,每天要翻阅的公文,多达上百斤,那时没有纸,都是木牍竹简,沉得了不得,换成纸之后,皇帝如果事必躬亲的话,公文依旧是看不过来。朱元璋废了宰相,所有事都自己抓,几个月下来,光看公文就累得不行,只好聘上几个秘书顶替,最后演化成内阁。
既然公务略等于公文,就挡不住人们在文字上弄名堂。事做得怎样无所谓,文字一定要说得好听。在很多情况下,只要没有捅出大娄子来,说得好,就等于做得好。清朝末年,一位方面大员要给自己一个总吃败仗的亲信开脱,巧手的师爷,只需将“屡战屡败”四个字掉个顺序,变成“屡败屡战”,就将一个无能的废物变成了愈挫愈勇的好汉。
当然,身为皇帝的人,一般不屑于玩儿这种小巧的把戏,他们要玩儿就玩儿大的,给人或者事物命名。最常见的是封神,中国神仙多,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得到过皇帝的册封,也就是说,这些神仙的名字,至少大名都是皇帝给起的,否则就不怎么值钱,香火上面要差上很多。其次是封人,最多的是给那些苦守不嫁的寡妇,算是表扬好人好事。据说每个贞节牌坊上面的字都是皇帝赐予的。当然给看得上眼的臣子也有封号,特别是那些死节之臣,人死了,身后的名头一定会响响的,恭维死人,让活人学,给活人看。有时候,后面的皇帝,也给前面的皇帝命名,加谥号,除了极个别实在不像话的,多半的都是美谥。当然也有急性子,等不及后辈出面,自己给自己戴高帽子的,比如慈禧太后,生前头上就有十几个字的头衔,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几乎把适合中老年妇女的好听字眼囊括一尽,比眼下的情歌还肉麻。
不过,皇帝命名的把戏,也有玩儿砸了的。史书上的王莽,名声不好,那是因为这位老兄,夺了汉家天下之后,把戏给演砸了。皇帝如戏子,自古皆然,穿上龙袍的人,总免不了要装模作样,演戏给天下人看,但俄国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演戏不能太入戏。政治舞台亦然,太入戏了,让人看着不自在,如果明明是演戏,却不自知,反而要台下的人跟他一起演,以至于影响到了观众的生活,饭都不要吃了,那么,皇帝自然也就做不成了。不仅戏不能演了,连戏班子一块儿都给毁了。王莽就是这样一个皇帝戏子,自家在台上演古装戏,居然要观众脱了衣服,一起换装,连货币都得随场次换古币,结果大家碍手碍脚,危及饭碗,于是都不高兴了。
这些古装戏中,有两个小场次恰好跟命名有关。一个是从古书上查来,说是《周礼》上没有封王一说,因此恢复西周的五等爵,公侯伯子男,把原来封的王都废掉,这一政策在国内实行起来也还凑合,原来被封王的人纵然一肚皮不乐意,也没办法。可是他把所有周边少数民族的王也要都撤掉,换成侯(周礼,边地诸侯封侯,地位并不比公爵低),可就惹出麻烦了。这些蛮夷之人,可弄不明白王莽托古改制的深刻含义,只觉得原来是王,现在变成了侯,等于降了级,大为不满,使者又解释不清楚,于是呼啸一声,反了。四边的危机还没了结,内地人祸未已,天灾又至,水灾、旱灾、蝗灾齐来。老百姓没饭吃,王莽有办法,派使者下去,教老百姓煮草根树皮,名之曰“酪”,这也是从古书上查出来的古义,果浆类食物。可惜,这种酪,救不了命,老百姓随即也反了。
王莽在历史上,虽然穿过龙袍,坐过大位,但只能算是半个皇帝,因为一辈子没过完,就连帝位带脑袋都丢了。
来自古代的超能力
神比人大,比人牛,古今中外皆然,但凡叫个神,似乎都有福人祸人的能力。但是在中国,人神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却有点儿糊涂,说不清到底谁厉害。
佛教传入中国,开始奉行老规矩,“沙门不敬王者”,意思是神职人员可以不敬帝王。但是,过不了多久,规矩就变成了沙门必敬王者,不仅对王者要敬,连王者委任的官员都要敬,地方官上香,住持必定亲陪,还时不时地要给官员做一场升官道场。沙门比官员牛的好时光,仅仅在元朝有那么一段,西来喇嘛,可以横着走,连一般的朝廷命官都敢欺负,不过这也是因为上面有皇帝(大可汗)宠着的缘故。
不过,佛教毕竟是外来的,固然要对权力低头,其神佛体系,还是自己做主,顶多给某个特别喜欢礼佛的君主,送上顶某某菩萨的高帽子,其他的天王菩萨,再到西天诸佛,都还是佛祖西来意。可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就比较不一样,不唯道士们从来没想过不敬王者这回事,而且连自家的神仙,都得劳驾皇帝连同大官来帮忙制造命名,如果哪位神仙没有得到过皇帝敕封,神气与仙气都会大打折扣。
尽管佛教、道教的创始,都不一定有礼敬权力的意思,人间的荣华富贵,也未必入了两教的法眼,但是,一个宗教若要光大,不取得世俗权力的认可(或者干脆政教合一),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再高妙的宗教,终归要沾染俗气。刻薄地说,佛道之间两千年的争斗,大抵是两教比着谄媚皇帝的过程,这期间,佛教的人间俗气大约比道教要少几分,因此有过三武法难,皇帝灭佛。刻板的儒者,有时也加入进来毁僧谤道,以毁僧为主,形成三家混战局面。不过,到了后来,明白人开始强调三教合一,搅成一团,有饭大家吃,僧道间的敌意才逐渐消失。民国时候大户人家做道场,一队和尚,一队藏传佛教僧人,一队道士,一队尼姑,多声部念经大合奏,乡村的庙宇,也多半佛道合一,观音菩萨和玉皇大帝合署办公。
分也好,合也罢,宗教在中国,服从皇权的格局是定下来了。尽管不乏笃信宗教的皇帝,但大体上,皇帝对于宗教,无非是用做工具。说宗教是鸦片,从工具这个角度,没什么错。不过,鸦片能够麻醉人,多半在于人自身有弱点,而且克服起来很难。皇帝也是人,无论头脑多么清醒,做彻底的无神论者,都不可能。一边用,一边自家也将信将疑,如果和尚道士不失时机地送上几顶高帽子,做皇帝的,被自己的工具忽悠了,也未可知也。
道士自创教以来,按道理说,最受宠的朝代,应该是唐朝。唐朝的皇帝姓李,不管这“李”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真的里面掺了点儿假,反正唐朝的皇帝自我感觉,是李耳的后人,于是唐朝的李家,跟道教遥奉的始祖,有了直接的关系。然而,实际上道教在唐朝,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尊贵,在某些时候甚至还处在佛教的下风,道教真正得意的年代,是后来的宋朝。
北宋自宋真宗开始,道教就开始得势,到了宋徽宗当家的时代,达到了顶峰。宋徽宗是个风流皇帝,有艺术家的气质,字写得漂亮,画也画得漂亮,坊间还传说他跟名妓李师师以及词家周邦彦大闹三角恋爱,有很多风流韵事。这个精力充沛、爱好广泛的皇帝,最喜欢的事,除了艺术和女人,就是跟道士腻腻乎乎。
能讨皇帝或者其他大人物喜欢的和尚、道士,大抵有两下子,不是会点儿幻术,就是有点儿口才,再不就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宋徽宗喜欢时间最长的道士,是林灵素。此道口才极佳,在宫中讲道,可以把深奥的道家经典,高度通俗化,引入俚语笑话,甚至黄段子,一个包袱接一个包袱,让听讲的人笑个不停,至于经上的内容,反倒不甚了了。史书上讲,林灵素还擅长幻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会魔术,只要有人配合,可以把东西变没了,再变回来,让大家惊叹不已。
如果仅仅是说书说得好,戏法变得巧,不过是东京汴梁瓦舍里一艺人,在皇帝面前,就算得宠,也只是东方朔一样的俳优,没什么大不了。可是林灵素得意大了,最得意的时候,他被封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可以把自己的家乡温州升格为应道军节度,出门前呼后拥,敢跟诸王争道。我们可以说,在他身上有件道教的外衣,无论说黄段子还是民间故事,都有一层神秘的面纱,因此东方朔比不了。但仔细考证起来,林灵素最拿手也最灵验的高招,其实很平常也很古老,就是拍马屁,唯一的特殊之处是,借着神仙的名义拍马屁,送高帽子换取功名利禄。
一出场,林灵素就说他可以通神见鬼,能知天界之事,说宋徽宗是上帝长子,长生大帝君下凡,于是圣颜大乐。林灵素不仅拍皇帝,凡是皇帝周围得宠之人,也一律奉上仙界高帽一顶(库存较多),皇帝的宠妃刘贵妃,是九华玉真仙女转世,权臣蔡京是左元仙伯,王黼为文华吏,连没了命根子的宦官童贯,也有一顶。如此这般地拍起来,林灵素就变成了人上人,大半仙之体,谁见了都得让他三分,走在路上,见了皇太子即后来的宋钦宗,也不避让。整个朝廷,神烟仙气,或者乌烟瘴气,正事没人做,自皇帝以下,整日见神见鬼,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直到金兵打上门来,围困京师,众人依旧未醒,本来汴梁城池高大坚固,远道而来的金兵缺乏攻城之具,一时半会儿还攻不进来。可是,来了一个名叫郭京的妖人,说是精通六甲之术,练一批六甲之兵,可以将金兵打退。守城之将,居然深信不疑,一任他披发作法,装神弄鬼,打开城门,遣六甲神兵出城杀敌,结果金甲兵不中用,撞上金兵就哗啦了,反被金兵乘机杀进城来,破了城,一股脑儿,将宋徽宗父子并皇族和嫔妃、宫女以及北宋积累多年的财宝掠走,北宋就此亡了。
有权有钱者,但凡到了不自信的时候,跟神就近,殷勤,把本该自己办的事情,托给神或者假托神的人来办,一边侥幸,一边投机,人与神都越了界,人的国有了麻烦,神的国也一样麻烦。
不懂规矩,不能成好马
立仗马就是皇家仪仗用的马。这样的马,现在的欧洲国家还有,比如法国每逢国庆阅兵,就会看到高大威猛的骑兵骑着同样高大威猛的马,在队列里行进。中国古代,每个朝廷都有仪仗用的马。以唐朝为例,皇家用马,分为三厩,祥麟、凤苑和飞龙,所谓麟、凤、龙三厩。当然,厩里面既非麟凤,也不是龙,都是上好的马。这些马的模样,我们在唐太宗的昭陵六骏和诸多以马为题材的唐三彩上可以一窥风采。那时候,轿子已经发明了,即所谓的步辇,但舒适程度还不够高,阎立本的《步辇图》里的步辇,比现在的滑竿还简陋,加上唐朝的皇帝,有胡人血统,对骑马不仅不打怵,而且有爱好。所以,立仗马的用途,理论上首先是给皇帝拉车,或者骑乘之用,但是皇帝只有一个,天天出行,能骑几匹?所以,这些马大多用在了给皇帝出行或者庆典的时候做仪仗,一队白,一队黑,一队红,再加上装饰、铠甲、威武的骑手,好看煞人。有些经过特别训练的马,还可以做马戏性质的表演,比如跳舞,类似于今天奥运会马术比赛中的盛装舞步项目。那年月如果有奥运会,中国人绝对不可能在马术项目上无所作为。
有资格做立仗马,绝非高大威猛、出身好(品种优良)就可以胜任的,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性格温顺,听话守规矩,不仅绝对不能尥蹶子,而且不能随便嘶鸣。恰是这一点,立仗马跟唐朝的政局,就有了那么点儿关系。
唐明皇是一个过于有色彩的皇帝,不仅因为此老跟杨贵妃之间的风流韵事,让后世文人渲染成帝王的爱情,也不是因为此老雅好舞乐,亲自操鼓奏乐,留下了梨园佳话也被尊为梨园鼻祖,而是同为一个皇帝,前半截励精图治,后半截荒怠朝政,大唐盛世由盛转衰,就落在此老手里。当然,这么有规模的大唐,由盛转衰,纵然是皇帝,一个人是办不来的,他还有帮手,排第一号的,就是李林甫。
李林甫在历史上有地位,不仅提供了一个奸相的样本,而且为我们的成语词典,增添了一个成语:口蜜腹剑。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不过,李林甫最著名的一句话,被载入史册的话,是跟立仗马有关的。
敢说话,是唐朝某些官员的风气,言官御史则更是如此,前面有魏徵的榜样在那里,谁不乐意做皇帝的“人镜”,博得历史上的声名呢?敢说话,就意味着批评。人之患,在于爱听吉祥话,批评的人多了,当政的人,就比较难受,宰相难受,皇帝也不舒服。但是,从太宗到玄宗,这么多年形成传统,不爱听,也得忍着。到了李林甫把持朝政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因是善于体察皇帝意思的他,发现这个沉湎于爱情和舞乐的皇帝,实心实意地希望耳根子清静了。自打很能干、也很爱提意见的张九龄被赶出相府,贬到外面做刺史之后,皇帝就愈发不耐烦听意见了。
因此,善于替皇帝排忧解难的李林甫,就招来了御史们,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是明君在上,群臣当谨听圣旨,不必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食料,一鸣则斥去,悔之何及!这个比喻太生动了。在朝堂上为臣,谁不知道立仗马呢?三品食料,内容是什么,我不清楚。如果说官家养马,食料的品级不同,那么皇帝的御马,理应食头品食料,不会是三品,另一个可能,是按三品官待遇供给。唐朝官员品级不像后面的朝代那么滥,一般宰相,也不过三品而已,这么说来,立仗马就等于享受高级官员待遇。这样的高级别待遇,因为忍不住胡乱叫了一声,就被罚下去拉车,实在代价过于沉重。言官御史也是人,都会理性判断,自然知趣。其实不知趣也没辙,因为从此以后,关于言官说话,制度变了。每个御史发现问题,想要说话的话,首先得关白上级,即向上司汇报,先报告给御史中丞,然后御史中丞再报告给最高主管御史大夫,最后还得请示宰相,才能决定这话该说不该说。
我们知道,在古代,御史是监察官,专门监督干部的,在特别开明的皇帝治下,也可以给皇帝提意见。既然是监督,就有特权,可以闻风上奏,像这样层层汇报,给皇帝提意见自然就免了,弹劾大官或者给大官提意见也没戏了,实在忍不住要说,也只能就芝麻绿豆大点儿的官,说点儿芝麻绿豆大点儿的事儿。就这样,大唐盛世,从万马齐喑到群臣齐喑,大家都成了立仗马,不,立仗臣。
可惜,消停的立仗日子,没过上几年,冷不丁的,“渔阳鼙鼓动地来”,安禄山反了,盛世从此不再。盛世不再,言官不能随便说话的习惯,却传了下来,玄宗的儿子肃宗当家时,诗人杜甫做左拾遗,本是个专门给皇帝提意见的官儿,结果多了嘴,被罚下去,从此只好在野苦吟,朝廷坏了,却成就了诗人的万古名。
庭院深深深几许
中国的古董已经日见稀少了,不仅地下文物被盗得差不多了,连国家文物局也得从海外往回买。地上的文物,这些年为了给经济唱戏,拆旧更新,也被毁了不少。不过还好,我们总算还有一个旧日的皇宫——故宫博物院在。
早就听说,故宫经过翻新改造,许多昔日不见天日的宫殿,都对游人开放了。三大殿粉刷一新,新是新了,可看着俗艳俗艳的,村意盎然。让人惊喜的地方也有,从前看不到的东六宫,里面摆了很多故宫的藏品,开放参观,看上去真的有点儿像一个博物院了。新摆出来的藏品中,招人喜欢的是金器、银器、瓷器和青铜器,不招人喜欢的是一套雍正的行乐图(胤禛行乐图)。
故宫现藏的帝王行乐图,据说还有康熙和乾隆两位的,但不知为什么只摆出来雍正的,雍正这套行乐图很多,整整摆了两层楼,画师画得也相当精细,工笔画,每笔都很用心,看得出来,给皇帝作画,谁也不敢马虎。但参观的人却不多,不管什么时候,都稀稀落落几个人,还要算上看上一眼大呼上当走人的。从传下来的画上看,清朝皇室都长着一副标准的黄瓜脸,而画上的这位,脸型尤其典型,长、弯,而且干瘪,严格地说,像晒干了的黄瓜。
万幸的是,画上的皇帝,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严肃,正经八本,动不动就圣颜大怒,要人家脑袋搬家。每幅画里的皇帝,都着便装,一副闲人模样,或炉边看书,或闲敲棋子,或山间漫步,或溪边垂钓,或行舟江上,或行吟篱畔。或近景,或中景,或远景,但中间位置,都固定要留给那个干黄瓜脸的皇帝。皇帝刻意潇洒,画师也想画出潇洒来,但怎么画,人都不自然,五官四肢都伟大,都庄严,但就是搁的不是地方,看上去别扭,绝对不像在行乐。
手脚不自在的皇帝,在现实中,肯定没法真的像画里画的那样悠闲自在,没有一大堆太监和随从跟着,到处游山玩水。溥仪回忆,他一个废帝,走到哪儿,都一堆人跟着,何况说一不二的雍正?可以说,这些画无非体现了一个深宫里的皇帝的某种向往。每个君临天下的皇帝,都想跟传说中的严子陵和陶渊明这类隐士一样,四处走走,钓钓鱼,看看书,徜徉于山水之间,尽享自然之乐。可惜,皇帝处处受拘束,身为皇家画师,在皇帝面前缩手缩脚,他们也的确想不出眼前这位成天被太监和宫女包围的皇帝,怎样去山水之间行乐。皇帝行乐图,尴尬地展示了一个皇帝和隐士之间的距离。除非有一天,皇帝真的丢了皇位,而且成功保住性命脱逃,不过,真的有那么一天,也许皇帝就该变乞丐了,隐士依旧做不成。
皇位意味着荣华富贵,意味着熏天的权势,也意味着金子做的囚笼。几乎所有的皇帝,为了钻进这个囚笼,都费尽了心机,行乐图的主人雍正正是这样一个人。在清朝历史上,没有哪一个皇帝坐上大位,有过他那么多的非议,即便如热爱他的史学家和文学家所云,这些非议都是谣传,恐怕也没人敢说,在康熙众多儿子争位的纷争中,根本没有他的身影。人之常情,凡是得到的东西,尤其是得到似乎就不会失去的东西,哪怕为了得到它而曾经费尽心机,吃了千般苦,遭过万种罪,都会不大在意,相反,想的,都是那些得不到的。皇帝富有天下,可以为所欲为,但唯一求之不得的,就是布衣之乐、闲人之乐和隐士之乐。皇帝行乐,事实上就是一种非分之想。进了那个金子的囚笼,即便喜欢逛街,也得找太监宫女装扮好了,假模假式地装一回,聊以过瘾。
一个住在故宫里的皇帝,这种非分之想,肯定特别强烈。清朝是个富有理学气息的王朝。理学本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但明人讲理学,主要用在科举考试的时候,其他的时候,该放荡就放荡,该纵欲就纵欲,案头上摆的可能是《四书集注》和《朱子语类》,但案子下肯定是《金瓶梅》和《肉蒲团》。只要没有人看着,其实都在看案子下面的东西。从关外打进来的满人,山野、生猛,也较真,学习明朝制度,不知道人家还有案子下面的一套,因此,整个政治文化很有些禁锢,皇帝自己带头,把宫女打发掉了大半,然后还把宫墙加高,弄得像今天游人看到的那样,走到哪儿都小院高墙,阴森森的,抬头只能看见不大点儿的天。加上城外的护城河水流得又慢,所以,当时宫里人就传,紫禁城是红墙、绿瓦、死水沟。红墙高,绿瓦长,死水沟深。
其实,原本明成祖朱棣建紫禁城的时候,这个皇圈圈就是个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从天安门到乾清门占宫城的三分之二,纯粹是摆仪式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的空间,狭小逼仄,还塞满了宫女和太监,一个后花园,巴掌点大,一转身就出去了。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加高宫墙,人在里面生活,怎么能不憋屈?记得小时候第一次逛故宫,第一个感慨,就是替皇宫里的人抱屈,而且总算明白了,为什么《红楼梦》里贾元春会说,皇宫是个见不得人的去处。
当然,因此也理解了为什么清朝的皇帝会玩儿命地修园子,修园子,就是为了不在宫里住。有了三海这样的去处还不够,还要在城外修一个又一个的皇家园林——地方大,有山水,而且能长住的园林。一个万园之园的圆明园,经过康、雍、乾三代经营,不仅把各地的名胜囊括一尽,而且在园子里修建了正大光明殿,上朝办事,都可以在里面。嘉庆和道光,算起来属于比较窝囊的皇帝,不敢像前辈那样大笔地花钱,南巡北狩,但一样住在园子里的时间比在宫里多。据寿阳相国祁寓藻记载,道光只是在春节头几天在宫里摆摆仪式,不到十五,就溜回圆明园纳福。试想,如果清朝的国力还能维持,如果英法联军没有一把火把园子烧了,那么,原来的皇宫是不是会变成一座专门摆样子的弃宫?很难说。反过来,一旦外面的园子被烧掉了,后面的皇帝只能委屈住在皇宫里了,于是,接连几个皇帝,却连半个子嗣都生不出来了,要说不育症,好像不至于这么整齐。坊间还传说,同治皇帝私自出宫逛窑子,染上梅毒才翘了辫子的。尽管一直有人出来辩诬,但即使查留下来的宫廷档案,同治的死,还是有些说不清,唉,说来说去,都是那红墙、绿瓦、死水沟的皇宫给憋的。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