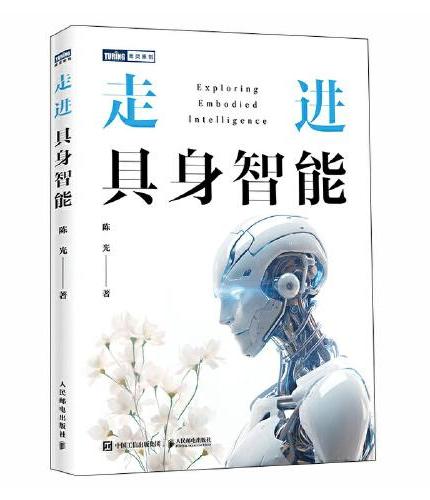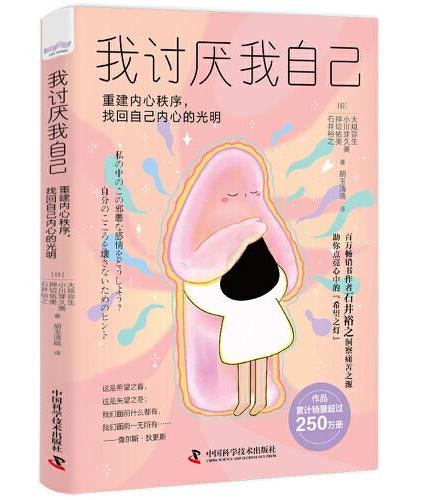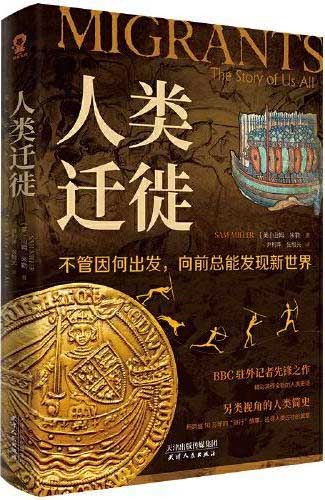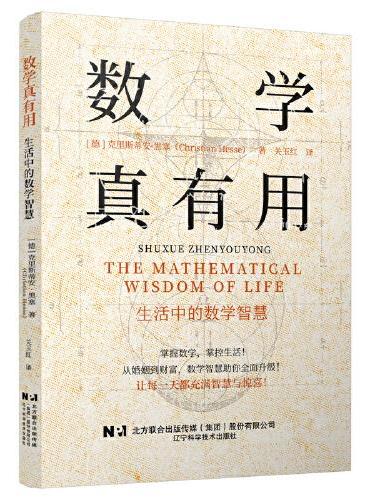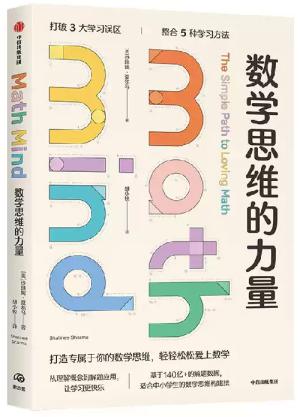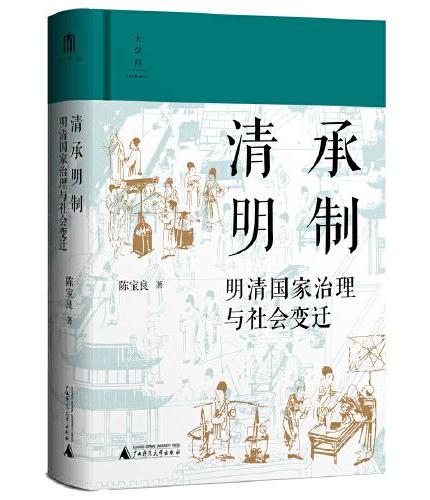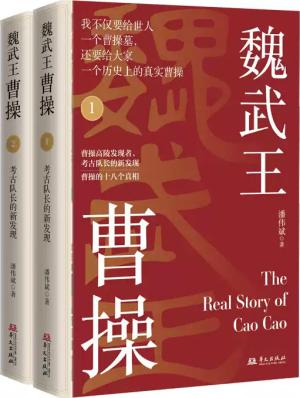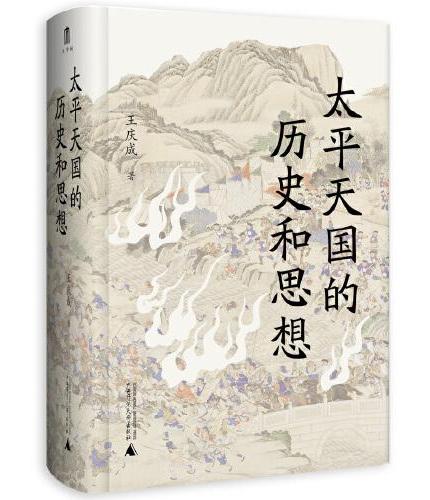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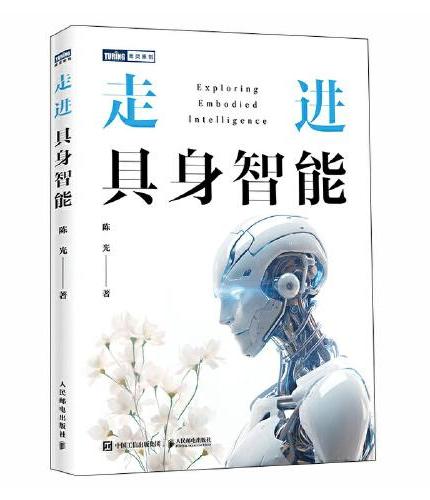
《
走进具身智能
》
售價:HK$
8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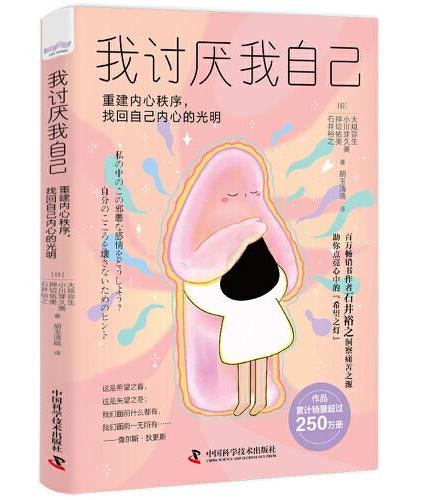
《
我讨厌我自己:重建内心秩序,找回自己内心的光明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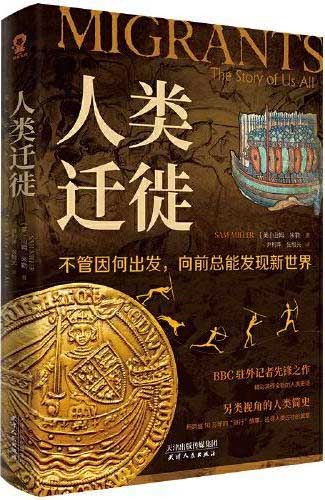
《
人类迁徙(BBC驻外记者先锋之作,另类视角的人类简史)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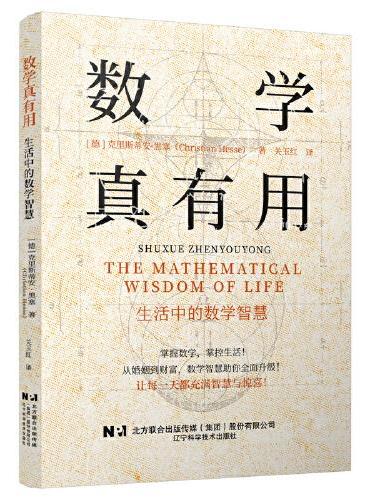
《
数学真有用:生活中的数学智慧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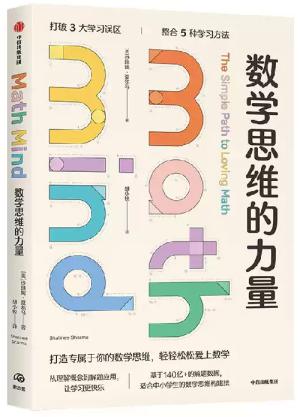
《
数学思维的力量
》
售價:HK$
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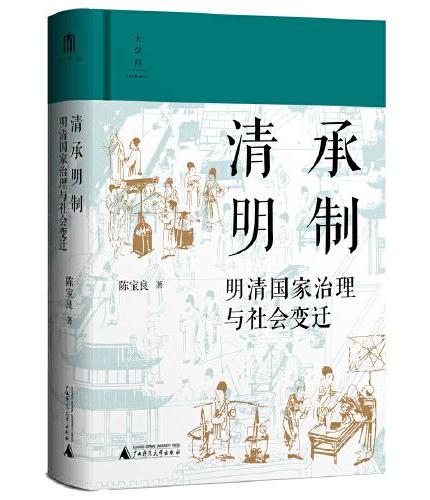
《
大学问·清承明制:明清国家治理与社会变迁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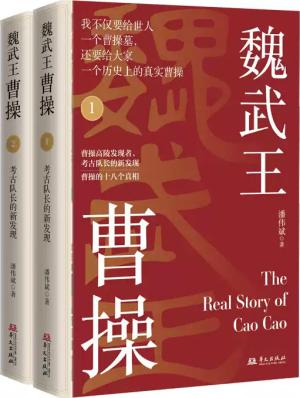
《
魏武王曹操(共两册)
》
售價:HK$
17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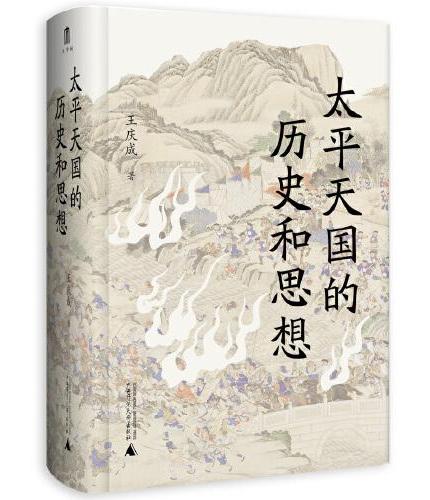
《
大学问·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一部研究太平天国的经典著作)
》
售價:HK$
140.8
|
| 編輯推薦: |
章开沅作序并推荐
一位善良而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晚清民国至1949年以来近百年的历史记录
背离真实的历史记述,不管是有意无意,都是对读者的误导乃至欺骗。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
--章开沅
|
| 內容簡介: |
叶笃庄先生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农史学家、民主人士,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
他的一生起伏跌宕,出生于封建大家庭,曾就读于南开中学,之后留学日本,抗战爆发后毅然归国投身抗敌事业,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主持编译委员会,对建国初期农业知识的普及、提高,贡献至伟。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含冤入狱18年,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本书即是他这一生的缩影。包括叶家往事、过眼烟云、解放以后、狱中记四个部分,详细讲述了他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用章开沅的话说:“本书中,我们看不到‘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之类痕迹,一般都是秉笔直书,既不夸饰溢美,亦不求全责备。对于自己,老人更是毫无忌惮,直书全部人生,勇于自我解剖,即令丢人现眼的往事也不回避,自我开涮,妙趣横生。”
最后,在大唐帝国的帮助下灭百济、平高丽的新罗国终于完成了统一朝鲜半岛的大业,持续许久的战火终于平息。
|
| 關於作者: |
叶笃庄(1914—2000)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农史学家、民主人士,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生前曾任民盟北京市委常委、民盟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
叶笃庄先生在他们兄弟行中,是一个异数,三哥叶笃义、六弟叶笃廉(叶方)、七弟叶笃正、九弟叶笃成(方实)走上革命道路,都受过他的影响。南开中学毕业后,叶先生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农学院、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实科。在日本留学时,即投身“左翼”活动,参加过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华留日剧人协会”。抗战军兴,毅然放弃学业,归国投身抗敌事业。先与几位弟弟一起在天津创办“知识书店”,宣传进步爱国思想。北平、天津沦陷,转战敌后,历经千难万险,到山西一带打游击,初隶属陈赓所部129师386旅,任敌工干事。1939年“双十二事变”前,受党委派,到河南泗水一带做土匪收编工作,短短数日,即动员得二千余人。后至山西晋东南长子、沁源地区,帮助筹办“对敌军工训练班”,亲任班主任,教授日语。再后,受党指派,在重庆潜入国民党“特种情报所”,与于光远先生的岳父孟用潜一起创办“太平公司”,在昆明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GBT小组、AGAS(美军陆空辅助队),赴北平营救盟军战俘。1940年代末又受党指派,加入民盟,参与民盟北平市委筹建工作,参与国共和谈。1950年代后,长期任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主持编译委员会,对建国初期农业知识的普及、提高,贡献至伟。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敌特”嫌疑,被捕入狱,含冤受屈十八载。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晚年以翻译达尔文著作为职事,出版译著多种。2000年1月30日逝世,享年87岁。一生爱国,终始不渝。
|
| 目錄:
|
第一部分.叶家往事
我的家世
河北住宅室内陈设
高祖情况
曾祖情况
祖父情况
父亲情况
祖母
大夫人
二夫人
三夫人
三叔
四叔
大哥
二哥
三哥
四哥
六弟
七弟
八弟
九弟
十弟
十一弟
十二弟
二姐
三姐
四姐
五妹
我的奶母
我家的老师们
我家的仆人们
姚妞
姑母
日常生活
过年、过节
小孩过生日
忌日
卖零食的
第二部分.过眼烟云
上私塾
上中学
退婚
追求孙竦
大学
留学日本
参加八路军
晋东南军政干部学校
民族革命大学—渭南师范学校—第三国际
全民通讯社——工业合作协会(工合)
特种情报所
太平公司
GBT小组
1946年初至北平解放
补记两件事
第三部分.解放以后
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
“反右”前奏
被捕
第四部分.狱中记
草岚子监狱
亲笔写供词,转入甲监
从甲监转到乙监
转入乙监的小号
转移到功德林监狱
从功德林转移到自新路的法院看守所
保外就医
病号看守所
团河劳改队
良乡劳改队
安徽白湖农场改造
调回北京,进秦城监狱
由秦城又回到白湖农场
由副业队调到试验站
特赦“国民党县团级”时被释放
转业到怀远县荆山湖鱼苗场
十四年后与亲人团聚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整理后记
|
| 內容試閱:
|
从甲监转到乙监
在甲监住了六个多月,又转到乙监。乙监的规格和甲监一样,生活也一样。“值星员”姓张,很快我就发现他是甲监那个姓张的“点传师”的侄子。他是通县法院的秘书,懂得法律,他估计,他犯的是“包庇反革命罪”,顶多判七至八年;至于他叔叔,就不好说了,重则是“死缓”,轻则“无期”,不至于枪毙。所谓“死缓”,是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长期饥饿之后,有几种感觉:
(1)头晕、头涨,脑子里很少想别的事,就盼那两个窝头。听说劳改队的生活好,可以吃饱,所以许多人都尽量“坦白”,争取早日判刑,参加劳改队。北京的公安局看守所,当时有两个:一个在草岚子胡同,专押“反革命”犯人;一个在北新桥炮局子,专押刑事犯。这两处都是解放以前的旧监狱,犯人被逮捕后,在这里预审。预审结束后,写“亲笔供词”,叫做“结案”。“结案”后,送往检察院起诉。起诉后,送往自新路法院看守所,在那里等候法院审讯,一般大约审一次,然后等候判决。判刑后,还要在法院看守所等候分配到劳改队。到了劳改队,又由公安局管理。被捕后,最重要的一关是公安局的预审,预审结案后,公安局即提出参考性的刑期意见给检察院和法院,法院大都根据公安局的意见判处犯人刑期的长短。此外,公安部也有看守所,先在德胜门外的功德林。这里也是一处老监狱,是清朝末年修建的,李大钊就绞死在这所监狱内。现这所监狱已拆毁,改建化工部的职工宿舍。解放后盖的一所新监狱在秦城,故名“秦城监狱”,是关押要犯的地方。话扯到别处去了,再拉回来谈饥饿的感觉。
(2)小便时用头顶着墙,闭着眼睛,用力才能小便出来。有人小便后立即晕倒在地,过一会儿才会醒过来。这是由于膀胱把尿排空之后,血液立即下行,造成血压突然下降,引起脑缺血而致昏迷。由于长期饥饿,血压本来就低,在低压的前提下,再行降低,人就不能支持了。
(3)在开饭前一个小时内,嘴里泛甜,等到吃下那两个窝头后,甜味也消失了。
(4)睡觉时经常梦见吃东西,夜间起床小便时,也经常听到入睡的人们吧嗒嘴。平常休息时聊得最多的,就是谈吃谈喝,但这不被允许,是违反监规的。
(5)如果敞开吃,总不觉得吃饱,吃了还想吃,以致胀死。我在安徽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牛棚里的犯人,趁着别人出去开会、留下他看门之际,偷偷把夜班饭的锅巴和喂牛的黄豆混在一起煮,吃了又吃,等到别人开完会回来之后,看见他躺在锅台旁边,手里还拿着半碗黄豆锅巴,人却已胀死半天了。我亲身也有胀肚的经验:在白湖农场劳改时,有一个星期天休息,说可以随便买饼干,因为梅雨季节就要来到,怕饼干发霉,我买了两斤,准备留着一点一点吃的,岂知吃了之后,欲罢不能,一个下午就把两斤饼干都吃完了。开晚饭时喝稀粥,其实我已经吃不下了,但舍不得不吃,又把那份稀粥也喝下去了,不一会儿肚子就觉得胀得疼,我赶紧到厕所用手抠嗓子眼,希望吐出来,但无论怎样抠,都吐不出来,想拉屎,蹲在那里半天也拉不出来。这时一个老犯人过来警告我,说千万不要躺下,不要喝水,要慢慢散步。我照他说的溜来溜去,足足溜了三个小时,才拉出屎来,拉出来的都是没有经过消化的白色饼干。
星期日不学习,上午洗衣服,下午缝补衣服。洗衣服时,把所有犯人的脸盆都集中起来,再加上两只打饭用的绿色大瓦盆,去号外打水。因为洗衣服的人不是很多,所以水也够用。脸盆和肥皂都是家里送来的。犯人有钱不能放现款,都得存入银行。用这些钱可以买脸盆、肥皂、缸子、牙刷、牙膏、毛巾等日用品。买东西时,管理员送来一张表,上面有可以买的东西,谁买什么,就在表上填好,然后把存折交出,过一两天后,就可以把东西买回。买东西叫做“开大账”。洗好的衣服,由“值星员”用脸盆端出,晾晒在院子里,下午再由“值星员”收回,发还给每个人。
下午缝衣服时,由管理员发针和线,线有限制,每个人两三根,有些犯人不缝补,这些人的线,大家可以分着用。我对于缝补很有兴趣,但缺少碎布,于是我把一件布中山装拆掉,一部分捐给号子作洗碗布,一部分留下了缝各式各样口袋。缝补时,最要紧的是不能丢针,这是为了防备犯人藏起来,把针插进血管里自杀。有一次一个犯人把针丢了,全号动员起来炕上炕下来回地找,足足找了两三个小时,最后总算找到了。如果找不到,就不给开饭,什么时候找到,什么时候开饭。丢针的犯人为此还要自我检讨,大家分析其思想根源,进行批评帮助。“值星员”常说,在监狱丢了一根针,等于在社会上毁掉十只电线杆子,罪莫大焉。
洗衣服之前,就是打扫号内的卫生,把房内墙壁和屋顶的尘土打扫干净。此外就是扫被子,每一个人的被子都要打开打扫。每周这样打扫了后,就会在地上撒上一层白色的皮屑。由于缺少油水,人很容易落皮肤。
每逢十月一日国庆节、阳历元旦、春节,都给吃一顿大米饭,管饱,可以随意尽量吃。因而这一天犯人们在饭前就不喝大量的水了,甚至不喝菜汤以便腾下肚子吃大米饭。即使没有菜,也觉得大米饭非常好吃,又香又甜。我一次吃过四大碗冒尖的大米饭;还记得一个犯人吃了九大碗,后来还是怕他吃坏,“值星员”强迫他不要吃了,这才停下来。这一天可以说笑话、小声地唱,不过大家吃饱以后,谁也不愿再动了。
在乙监住了大约两个月,又调到丁监。在甲监时,看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员。这人大约已判刑,留在草岚子监狱内劳动改造,如修理电灯、修理水管等,干一些轻劳动。他吃窝头不受限制,吃多少,打多少,一个人住在甲监的一个小号子。他可以买点酱油。
丁监关的全是“劳动号”,即从事一些轻劳动的犯人。另外这里有一个病号监房,吃窝头也不受限制。关在这个监房的犯人,有的是真有病,有的是受优待,我则属于后者。这个监房里关有以下几个人。一个真正的国民党特务,山西人,大陆解放后,他跑到台湾,和特务接上了关系。他在解放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少校电台台长,三十余岁。在台湾,阎锡山还亲自接见了他。领了一笔特务经费后,潜回大陆。他患有严重的肺病,已判刑,大约是“死缓”。他有一点存款,准许他买点心和咸菜。有一次他买回来一包“自来红”月饼,给号内每一个人吃一块,真是香极了。他整天躺在那里,咳嗽,吐浓痰,真叫人恶心。有一天,他病重了,把他抬出去送往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又回来啦。当抬他出去时,他大声喊叫,“我自由了!我自由了!”回来后仍靠墙睡在紧里边。一天夜里,他不行了,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第二天清晨他死去了,没有哼一声。管理员叫我和另一个人用褥草把他抬到院里,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抬死人。
有一个华侨,讲一口广东味的官话,他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和一个人骂共产党,那个人把他揭发了,因而被抓起来。他总是傻乎乎地微笑,若无其事,一点也不着急。只是刚一吃窝头就皱起眉头,咽不下去,他把窝头掰成小药丸那么大,一点一点地往下咽,他抱怨说:“就是咽不下。”过了一个星期,他也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了。
有一个工业中专的教员,二十三岁左右,南方人。划了“右派”之后,他向一个年纪比他大的朋友透露,他要跑到国外去,后来这个人把他检举了,于是被抓了进来。有这样行为的人,大都以“企图偷越国境”判罪。他会体操,会玩平衡木等。他说,划为“右派”后,把他关了起来,他曾打破玻璃窗,借助一件斗篷,从三层楼跳下,而未受伤。有一天下午,他用扑克牌过关,一下子拿通了(这是很不容易拿通的),他非常高兴,说:“通了!通了!”当天七时左右,天黑以后(冬天),他要去厕所大便,便一去不回,逃跑了。厕所房顶有一个大气孔,刚容下一个人的身子,他从这里钻到房顶,由房顶跳到大墙,又向下跳去。不幸的是,当时地面上有冰,没有站稳,把腿摔断了,结果没有跑成。他逃跑后,监狱长亲自提审号内所有的犯人,问他逃跑前,号内的人是否知道?是否合谋?还有,问当时值班的管理员是否是那个?果然,后来那个值班的管理员不见再上班,听说这个管理员因失职受到了惩罚。又过了两三天,开了一次斗争会,把他架出来挨斗,这时他的腿已经摔坏,但还是给戴了脚镣。据说此人后来被判了无期徒刑。
病号监里还有一个犯人,姓宫,四十余岁,山东胶州人,是一个“三八式”的老干部(1938年入党),被捕前是中央某一个部的人事司副司长。他的案情是:土改时,把他家划为富农,他不服。当时他在部队里任职,于是返乡和村干部理论。回乡时,带着一个警卫员,腰间挂着手枪。不料返乡第二天,就和村干部吵闹起来,以致扭打一团。他急了,拔出腰间的手枪,准备行凶,被他的警卫员夺下,未酿成人命案。这么一打,他家的富农问题未得解决,他只好回到部队。村干部跟着把他告到军区,说他“武装镇压土改”。他也有理由,说划他家为富农是错误的,因为他是独生子,他参军后家里没有劳动力,只好雇工。像这种情形,根据当时规定,不得划为富农。他不承认他用枪威吓,只认为那是互殴。这是四十年代的事,后经军区和行署联合调查后决定,给宫某以警告处分。这件事本已了结,可是1958年搞“反右倾运动”时,村里又把他告了,部里不得不受理,叫他重新交代。他认为这个问题本已解决,有当时军区和行署的决定,所以认为村里是在无理取闹,拒不交代。部里开会“帮助”他,他完全采取对立态度,结果被送到监狱里来了。
有趣的是,这个人在抗日战争时,做过“敌军工作”,他还记得“缴枪不杀,优待俘虏”那两句日语口号,而这两句口号正是我在八路军129师时,和几个留日同学共同拟出的。他和我一样,抱有幻想,认为政府不会判刑,只是因为在社会上态度不好,教育教育就会释放的。他常向我说:“抓住两只刺猬,判也判不得,放也放不得。”后来听说,他瘐死在狱中了。
还有一个小青年,二十岁左右,是一个未考入大学的高中生,戴深度近视眼镜,北京人。一进号子,就若无其事地高谈阔论:“我是搞哲学的,信仰斯宾诺莎。”表现极为狂妄。他和他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研究斯宾诺莎的读书会,从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结果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抓进来了。
另一个青年,二十多岁,他父亲是北平的军统头子,北平解放后留下来了,后被枪毙。他父亲枪毙后他去收的尸,他把他爸爸从刑场背出来放进棺材。后来他找到了一个工作,由于一个偶然的事情,他旷了工,没有去上班,最后索性不去上班了,住在他的一个女朋友家,很快就发生了关系,吃住均在这个女朋友处。这个女人知道他父亲是军统头子后,便以为他有特务关系,曾在床笫间问过这件事。他便顺竿爬地说:“我是反共救国军的司令,正在发展成员。”于是把她发展进来,后来又把她的姐姐也发展了进来。他还向一个吹小号的朋友借过钱,也把他发展了进来。这个大骗局暴露以后,连男带女,一起抓将起来。这本来是假的,可是却把他当真的特务抓起来了。
后来,这个病号监房也要参加劳动。这里的劳动是制作小孩玩的玩具木剑,我们做的一道工序,就是把木剑上涂的用石灰、胶等物制成的腻子用砂纸打磨光,然后送出监号,由另一道工序涂银粉、油漆。这一道工序最脏。打磨下来的细粉末飞满屋内各个角落,鼻子眼里、耳朵眼里,都充满了这种粉末。而且监门关着,粉末都落在屋内,无法飞出去,满屋灰尘滚滚,令人不堪。后来,我们向狱医反映,说我们都是肺病号,这样大的灰尘,对于病情有害。狱医果然替我们反映了,于是给我们换了一个工种,就是用纸在一个模型内,脱制宝剑护手。这个活既干净又轻松,大家都很高兴。
这时竦仍按时给我送鱼肝油,不过不是清鱼肝油,而是鱼肝油糖浆。有一次,还给我送来一点酱姜芽,这是我最爱吃的,她还记得这点,我真感激极了。我吃送来的东西,心里很难受,万分过意不去。我无法想象她们母子四人在外边怎样生活,这种内疚的心情,至今想起来,还感到心痛,非语言所可形容。
在丁监里还关着两个女犯,一是北京某教派主教的夫人,她的丈夫就关在隔壁。他们犯的什么罪就不得而知了。这位夫人会织毛衣,给监狱管理人员编织毛衣。丈夫是单独关押的,情况不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