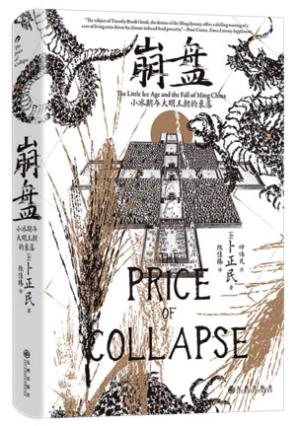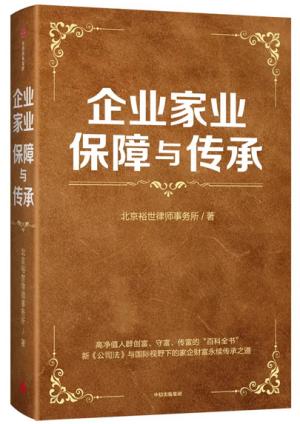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爱得太多的父母:14组家庭,20年追踪的家庭教育调查实录
》
售價:HK$
65.8

《
人偶游戏(东野圭吾竟然写过这种惊悚悬疑之作)
》
售價:HK$
65.8

《
自然、权利与正义(重思古典自然法 探索人类生活的永恒根基)
》
售價:HK$
74.8

《
汗青堂丛书155·糖与现代世界的塑造:种植园、奴隶制与全球化
》
售價:HK$
11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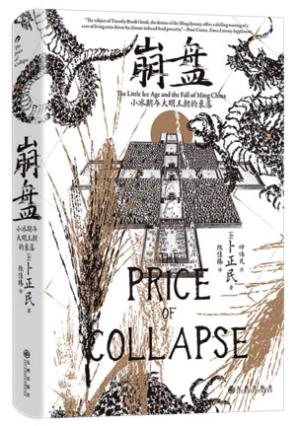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54·崩盘:小冰期与大明王朝的衰落
》
售價:HK$
9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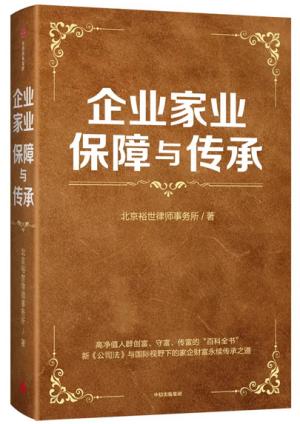
《
企业家业保障与传承
》
售價:HK$
187.6

《
世界武器装备知识图解
》
售價:HK$
174.6

《
南方丝绸之路与欧亚古代文明
》
售價:HK$
233.6
|
| 內容簡介: |
《荣格自传》是分析心理大师荣格于83岁高龄之时回顾自己一生的作品,包含了荣格从青少年时代的经历到成年后的所见所闻;从作为医生所治疗过的症状到作为思考者所经历的梦境和幻觉;从与弗洛伊德相识相知到分道扬镳;从现世中的种种人事到对死后生活的见解等。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荣格自传》虽为自传,实际却是荣格毕生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书中,荣格打开自己的心灵,以平实的语言跟人们一起探讨他丰富的人生和浩瀚的精神世界。
|
| 關於作者: |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年),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倾向性格和外倾向性格、心灵四层次、集体无意识、情结与原型等观点。
1907年,荣格结识弗洛伊德,并成为其主要的合作者,1909年,弗洛伊德把他定为精神分析运动的法定继承人,称他为“王储”。1911年,在弗洛伊德的举荐下,荣格担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后来,因观点不同,荣格与弗洛伊德分裂。与弗洛伊德相比,荣格更强调人的精神有崇高的抱负,反对弗洛伊德的自然主义倾向。
荣格一生著述浩繁,思想博大精深。他所创立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不仅在心理治疗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而且对哲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荣格终身都致力于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探索,晚年的荣格更是离群索居,独自居住远离城市喧嚣的苏黎士湖边塔楼中。1961年6月5日,这位当代心理学思潮中最重要的变革者和推动者,安然病逝于苏黎士湖边。
|
| 目錄:
|
序 言
一、童年时光
二、中学岁月
三、大学年代
四、精神病治疗活动
五、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六、直面潜意识
七、著作
八、塔楼生活
九、游途
Ⅰ 北非
Ⅱ 美国:贝勃罗印第安人
Ⅲ 肯尼亚和乌干达
Ⅳ 印度
Ⅴ 拉文纳与罗马
十、幻象
十一、死后生活
十二、后期思想
十三、我的一生
|
| 內容試閱:
|
四、精神病治疗活动
作为学徒,我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工作了几年。其间,我的兴趣点及进行的研究工作都是围绕这样一个重要、迫切的问题展开的:“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中究竟都发生了什么?”我那时尚不清楚,我的同事们也全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精神病医生不在乎病人的言辞,他们感兴趣的只是如何诊断那些症状、描述并编制成统计数字。用当时盛行的临床学观点进行解释就是,病人的人格就是其个性,那些与精神病的医治有关。医生需要随身携带剪贴好的诊断病历及各种症状的详尽记录去见病人,然后对病人进行定性分类,最后在诊断书上盖上图章。多数情况下,事情至此便结束了。精神病人的心理,是根本不被关注的。
伯戈尔茨利精神病医院弗洛伊德在此方面对我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他在关于癔症和梦的心理分析方面所进行的那些基础性研究。对我来说,他的观点指明了对个体病例进行深入研究和理解的道路。尽管他只是个精神病学专家,但他却也把心理学引入了精神病学。
现在,我仍能十分清楚地回想起在当时令我印象极深刻的一个病例:
一位女士因为患上“抑郁症”住进了医院。医生仔细为她进行了常规检查:询问了既往病史,进行各项检验及身体检查。诊断的结果为精神分裂症,用当时的术语来讲就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
该女士恰巧在我所在的那个科室进行治疗。最初我并不敢对此诊断结果表示质疑,因为我那时还仅是位经验不多的初学者,不敢莽撞地提出其他的诊断结论。但这个病例却使我觉得奇怪。我认为她表现出的并非是精神分裂症的症状,而应属于一般性抑郁症。于是,我决定实施自己的治疗方案。我那时正忙于与联想相关的诊断性研究,于是和她共同进行了一次联想实验。此外,我们还一起讨论了她做过的各种梦。我通过此方式再现了她的过去,而这些是她的既往病史中无法解释、没有记录的。我是直接从潜意识中获取的信息,该信息也展现了一个悲剧故事:
该女士婚前曾结识了一名腰缠万贯的企业家的儿子,这名男子是她附近地区所有姑娘们所仰慕的对象。她因为长得漂亮便自信有机会可以得到他的爱。但他却对她没有好感,于是她就愤恨地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
5年后,一位老朋友来拜访她,他们谈起了往事。他告诉她:“你结婚之时,有个人,就是某某先生(那个大企业家之子)——受到了打击。”就是从那一刻起,她开始抑郁,几周之后便导致一场大灾难事件降临:她那会正在给孩子们洗澡,先给4岁的女儿洗,然后再给2岁的儿子洗。由于住在乡下,那个地方的水源并不是很卫生。他们喝的是泉水,但洗澡和洗衣服却要用河里的脏水。她给小女儿洗澡时见到孩子啜了几口水,但却没有制止,她甚至还给小儿子递了一杯不干净的水喝。当然,她做这些时是无意识的,或者说仅有半点意识。因为她当时的思想已受到先前出现的抑郁的影响。
过了不久,在这病症的潜伏期过去之后,她的女儿因患伤寒病死掉了。那小姑娘是她的掌上明珠,小儿子却并未受到感染。此时,女士的抑郁症也发作了,于是便被送进了医院。
我从对她进行的联想测验中得出结论:她是一个谋杀犯,而我也知道了很多她内心的秘密。事情马上就要明了——这就是她患上抑郁症的原因。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心理性的精神紊乱。
弗洛伊德那么,现在我应当采取怎样的治疗方案呢?截至当时,这位女士为了治疗失眠症一直在注射麻醉剂。同时,还会有人随时对她进行监护以避免出现自杀倾向。但对于其他方面却未采取过什么治疗措施。从体质上而言,她的健康状况尚且良好。
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要公开地向她说明这一切?应当由我来承担这其中的主要责任吗?这是我首次遇到工作方面的矛盾冲突,在以往的经历中,这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一个良心方面的问题,且我需要独自处理。如果我请求同事们协助,或许会被警告:“看在上天的份上,千万不能向那位女士说。那样只会让她发疯。”但我认为结果很可能相反。一般来讲,心理学上的各学派貌似并没有明确的法则。一个问题可以这样回答也可以有那样回答,这要取决于我们是否将潜意识的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当然,我也深知自己所要承担的个人风险:若病人病情加重,我就会陷入困境!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尝试一下新的治疗方案,尽管其结果尚无法预料。我将由联想测验获得的一切结果都告诉了她。这样做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直截了当地指责一个人为杀人犯的事情非同小可。对于必须听取这种指斥并接受它的病人来说,特是极为痛苦的。但结果出人意料,两周之后,她出院了,而她从此也再也没有进精神病院。
关于这个案例,我之所以对同事们守口如瓶还有其他原因。我担心他们会议论纷纷,并且这还很可能引发法律诉讼问题。当然,他们也拿不出我对这位病人不利的证据,但这样的议论对病人来说却可能带来灾难。命运施加给她的惩罚已经够悲惨了!她应当回归正常生活,并在生活去赎罪。这才更有意义。她是背负着沉重的思想负担出院的,当然,也被迫背负起了这样的负担。对她来说,失去孩子已经痛心疾首了,而她的赎罪行为也从患上抑郁症并被隔离在医院的那一刻开始了。
在精神病学中,多数情况下,前来就诊的病人都会有某些无法说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通常也都是秘密。我认为,只有对这些完全属于个人隐私的秘密进行研究,才算是真正的治疗。那些故事是病人埋藏心底的秘密,是致使他们得病的因素。作为医生,我必须了解秘密的真相,那样才算掌握了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即找出并弄明白他们经历了什么。这样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仅探讨意识方面的材料是不够的。有时候,进行联想测验则可能打通这条通道,对梦境进行阐释或与病人进行长期而耐心的接触也有同样的功效。在治疗上,问题应从病人的整体而绝非仅从症状入手。我们必须涉及触及那人格的种种问题。
1905年,我在苏黎世大学担任精神病学讲师。同年,我又当上了精神病诊所的高级医师,此后4年我一直担任此职位。后来,在1909年,我获得了晋升,就离开了此职位。在那几年间,我私下接了很多病人,日常的工作也忙得不可开交,然而同时我也获得了教授的职称。1913年,我讲授心理病理学,也讲授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基础课程及原始心理学——这些是我主讲的科目。在前两个学期,我主要讲催眠术,也讲雅奈和弗劳内伊的理论。到后来,我就主要讲授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课程了。
在讲催眠术期间,我喜欢对给学生进行示范教学,会对病人的既往病史进行详细询问。其中有个病例回想起来至今记忆犹新:
一天,一位有着强烈宗教信仰的老妇人前来就诊。她已经58岁了,拄着拐棍,她的女仆也一同前来。17年来,她因为左腿瘫痪吃过很多苦。我让她在一把舒适的椅子上坐下,然后要她讲述自己的既往病史。她将那与病相关的冗长故事,完整且详细地说了出来——那个病史很可怕。最终,我打断了她的叙述,说道:“恩,好的,今天没有时间详谈了。我现在就对您催眠吧。”
话音刚落,她就闭上眼睛进入了深度睡眠状态中——她根本不用催眠。我对此万分惊异,却并没打扰她睡。她连续不断地说话,还说了各种令人深感诧异的梦话,这些梦表征着潜意识并且是体验极为深刻的各种东西。然而,直到多年后我才明白了这点。我当时感觉她是正处于一种神志昏迷的状态。这样的状况令我感觉很不舒服。当时还有学生在场,我本打算要她催眠的!
此情形约持续了半小时,当我想将病人唤醒时,她却不能醒来了。我很震惊:我突然想到,或许我是无意中接触到了潜在的精神病。我花了约10分钟才将她弄醒。与此同时,我也很不愿意让学生们看出我那紧张的神情。醒来后,她感到有些头昏迷糊。我对她说道:“我是医生,您现在一切正常。”听到这些她大喊道:“这下我被治好了!”然后她扔掉拐棍,自己站起来走了。我尴尬得满脸通红,却仍要硬着头皮向学生们讲解:“现在你们看出催眠术有多么神奇了吧!”事实上,我根本就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是促使我放弃催眠术的体验之一。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但那女人确实被治愈了,并且还兴高采烈地走了。我请她及时告知以后的状况,因为我估计最多24小时她就会旧病复发。但她疼痛的老毛病却未再复发。尽管我心存疑虑,却也不得不接受她确实已经痊愈了的事实。
第二年夏季那个学期,在我第一次授课之时她又过来了。这一次,她抱怨说背部剧痛,据她说这也是刚开始发作的。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这是否与我再次开始讲课有着某种关联呢?或许她是在报纸上见到了我开设该课程。我问她这疼痛开始的时间及原因。她回想不起来在发病的确切时间,及她发生过什么事,也提不出一点儿这病的原因。最后,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是在报纸上看到我开课之时出现的背疼。这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但我还是不能明白她那病症神奇地被治愈的真正原因。我第二次对她进行了催眠,她再次自动进入了昏睡状态,此后她那背便再也不疼了。
这一次,我为了更多了解关于她生活的细节,讲完课后便将她留了下来。得知她有一个弱智的儿子,现在恰巧也是在我所在医院的科室进行治疗。我先前对此毫不知情,因为她现在使用的是第二任丈夫的姓,而她的儿子却是她与前夫所生。那是她的独子,她自然希望儿子才华出众、有所成就,岂料他在幼年时就患上了精神病,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时候,我还是个年轻的医生,我身上具备她希望儿子所成为的一切。她希望能成为一位英雄母亲,于是就把这样的愿望转移到了我身上。她在内心把我认作儿子,还到处宣扬说我奇迹般地将她的病治愈了。
我在当地还获得了“巫师”的名声,实际上这要归功于她,且我能有第一批自己的病人也是她的功劳。我的心理疗法开始了,是始于一位想让我取代其儿子地位的精神病母亲。自然,我向她详细地解释了整个事情,来龙去脉也讲到了。她很理解地接受了这一切,她的病也从此再没有复发过。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在精神病医治方面的经历,也可以说这是我最早进行的分析。直至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与这位老太太的谈话。她是个聪明人,很感激我对她的认真接待,以及我对她儿子遭遇的关心。这的确对她帮助很大。
刚开始进行私人诊疗时,我同样使用催眠术。但很快,我就放弃了该做法,原因是采用该方法时很麻烦,但对于病情的改善程度或该疗效能维持多久却是一无所知的。我对这种毫无把握的工作方式感到反感。我也不喜欢自作主张告诉病人他应该做些什么,而更愿意是病人本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寻找发展方向。为此,应对各种梦境进行仔细的解析并对潜意识的其他表现形式进行研究。
1904~1905年期间,我在精神病诊疗所创办了一个精神病理学实验室。我找了几个学生,一起进行精神性反应(即联想)的研究。老弗兰茨·里克林是我的助手。路德维格·宾斯旺格当时正在写他的博士论文,是论述与心理电击疗法心理电击疗法指皮肤的电阻暂时性显著下降的现象,该状况是由于精神兴奋而诱发的汗腺活动加强。有关的联想实验的,而我则在写论文《论从心理学角度对事实诊断》这篇文章在《精神病学研究》上发表,1905年第28期,第813~815页。,还有几个美国人,如卡尔·彼特森、查尔斯·里克什等。他们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了美国专业期刊上。正是这些关于联想的研究,让我后来在1909年接到克拉克大学的讲学邀请,在那里我就自己的研究工作举办了专题讲座。与此同时,他们也邀请了弗洛伊德。我们两人均被授予了“荣誉法学博士”的头衔。
联想实验和心理电击疗法实验使我在美国声名鹊起。很快,当地的许多病人来找我进行治疗了。在我的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个人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是一位美国同行转介给我的一个病人。他被诊断为“酒精中毒性神经衰弱”,预后:“无法治愈”。那位同行担心我的治疗效果不明显,作为补救措施,他建议患者同时也到柏林某位神经病权威那里求治。那位患者来到我的诊所,经过一段时间与他的交谈,我发现他患的是一般性神经官能症,对于该病在精神上的起因他却一字不提。在对他进行联想实验后发现,他正逢受着可怕的恋母情结等各种情绪的困扰。他出身于一个富裕且有名望的家族,有个可爱的妻子,生活也无忧无虑——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子的。他只是有些嗜酒,喝酒是想使自己处于麻痹状态以忘掉那受压抑的情景,但这似乎也只是徒劳。
他母亲拥有一个规模庞大的企业,这位智力超群的儿子则在公司里担当领导者。他确实早应挣脱从属于他母亲的这种压迫性的处境,然而他却鼓不起勇气,下不了决心抛弃掉这一优越的地位。这样,他就一直受制于自己的母亲。每当他们在一起,或当他不得不屈从于母亲对他的干涉时,他就酗酒以麻痹或消除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其实并不愿真的离开这个温暖安逸的家,尽管这有违他的本意,他却仍愿意让自己享有财富和舒适。
经过短时间的治疗后,他不再嗜酒,于是自认为已经痊愈了。但我告诉他:“如果重新回到您以前的环境,我不敢保证您不会旧病复发。”他不相信我的话,兴高采烈地返回了美国的家。
当他再次处于母亲的干预影响之下时,他又开始酗酒了。为此,他母亲来瑞典时,前来向我询问医治办法。她是个聪明的女人,权力欲也很强。我明白了她儿子为何不得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