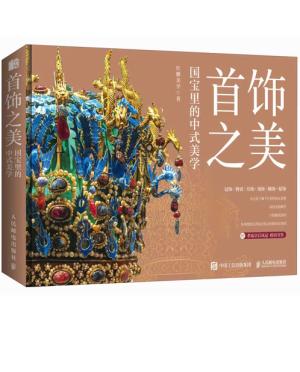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画龙西方传世影像里的中国形象1500-1949
》
售價:HK$
173.8

《
似锦 冬天的柳叶 凤鸣九霄
》
售價:HK$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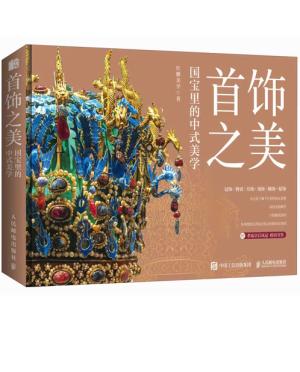
《
首饰之美:国宝里的中式美学
》
售價:HK$
173.8

《
旧庙新神——晚清变局中的孔庙从祀(论衡)
》
售價:HK$
63.8

《
道心惟微: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战略文化与历史启示
》
售價:HK$
107.8

《
重写灵魂:多重人格与记忆科学(共域世界史)
》
售價:HK$
119.9

《
新伦巴第街:美联储如何成为最后交易商
》
售價:HK$
63.8

《
权力与财富 晚清时期的金融博弈(以金融视角重构晚清史,揭开晚清金融体系背后的权谋暗战)
》
售價:HK$
79.2
|
| 編輯推薦: |
|
文化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竞争力。营造和谐的人文书香社会,提倡全民阅读,提升大众文化修养,已成为有识之士致力推动的一项社会活动。“书魅文丛”是一套展现书香魅力、倡导全民阅读的系列丛书,旨在通过展现读书的魅力,引导国民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提升国民文化素质,为构建和谐的人文书香中国插秧播种。
|
| 內容簡介: |
|
《夜读记》是一本日记体的读书笔记。作者易卫东用清雅的笔调、凝炼的语言、日记体的形式,细致地讲述了自己得书、读书的过程和乐趣。对作者来说,这一年有书为伴的快乐生活,既有得书的欣喜、购书的酣畅,又有读书的沉醉、品书的愉悦。本书的特点在于形式活泼,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且稍显私密。作者不吝将自己的思想、趣味、性情、感悟通过书情书话呈现出来,引领读者爱书、悦读
|
| 關於作者: |
|
易卫东,1966年2月生,中学数学高级教师,新余市高中数学骨干教师。课余好读闲书,以聚书为乐,爱好书话,创作有读书随笔及日记体书话《戊子读书记》《有不读斋日记》等,在读书类报刊发表读书札记,出版读书随笔《学步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5月)。
|
| 內容試閱:
|
2月17日,正月十一,星期日
今天读到一篇文章:《巴金的“底线”》(蒋泥著),心里很不是滋味。
“读巴金的每一部作品,我都特别难受与难过,不住地问:这就是巴金的文章?这就是‘大师’的作品?我困惑。我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蒋泥在《巴金的“底线”》一文开头说的话,也道出了整篇文章的基调:质疑作为文学大师的巴金在1949年后其人其文的道德底线和真诚与否。对于“文化大革命”后巴金在一系列随想录中所表现的忏悔和说真话的告白,蒋泥的质疑是丝毫不留情面的。在蒋看来,巴金对自己在极“左”年代的所作所为是随波逐流,虽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其实是懦弱,害怕受牵连。再如在胡风去世之后巴金写文章忏悔了自己当年在批判胡风时的行为,并说现在胡风不在了,他写上迟到的忏悔。对此,蒋泥道:为何在胡风生前,巴金不道歉?蒋对巴金的真诚很是怀疑。
有人说蒋泥是“一位思想随笔型的作家,他那所向披靡的犀利文字,深刻而无城府,是他行走于文坛的名片”。很遗憾,我以前没有读过蒋泥的“思想随笔”,他的小说我也没有读过,这篇《巴金的“底线”》是我读过的唯一一篇蒋泥的文字。“文字犀利”和“无城府”看来是事实,“深刻”和“所向披靡”就难说了。巴金说过没有神,自然巴金也不是神,巴金说过许多假话,也曾参与过批斗和揭发。惟其如此,浩劫过后,巴金才呼吁“说真话”。巴金的呼吁是真诚的反思,不是矫情的表演和造神,经历过那场劫难的人都能体会到巴金的真诚。许多人都知道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铭刻着一位名叫马丁·尼莫拉的德国新教牧师留下的短诗:
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我们都希望在别人被追杀的时候,能有人站出来说话,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理解别人的不说话,我们尤其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过去的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普通人的行为。没有人为马丁·尼莫拉说话,我们不能说“活该”,同时我们也不能责备马丁·尼莫拉的“没有说话”。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在别人受难时巴金还没有受难,也作为巴金的一个污点来言说。有一句话说,时势造英雄,在没有人说话的时候,张志新说话了,遇罗克说话了,他们当然是英雄,值得敬佩,但是不能由此判定大多数没有说话的就该在此后得到责难。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有“追杀”,为什么有“造英雄”的“时世”?巴金也好,参加过“梁效”的冯友兰、周一良也好,“懦弱,害怕受牵连”,是最正常不过的表现,把这样的表现也理解为为虎作伥,是不厚道的。1971年出生的蒋泥,没有感受过极权统治的酷烈。
自序
《戊子读书记》是我在2008年尝试写的日记体书话,当时贴在博客上与书友们交流,得到朋友们不吝啬的鼓励;到2012年,又写了《有不读斋日记》。除了这两年的完整日记和此前的《读书消暑录》之外,我是不常写日记的。虽说是“事无不可对人言”,可是我们升斗小民的吃喝拉撒睡,写在日记本上,自己看着也要失笑了,拿出来给人家看,当然更无必要。只有伟人或名人的日记,哪怕是流水账,都是研究的资料。胡适的日记,事无巨细,都有记录,甚至还有许多报道、消息的剪贴;鲁迅的日记里有书账,成了许多人的读书门径,据说孙犁先生就是以鲁迅日记为参考,按图索骥来找书读的。我读过施蛰存的《昭苏日记》,有时候一天的日记里只有“某某来”几个字,来干什么也不记,当然更无议论,这样简省的日记显然是被日记与书信带来的文祸吓怕了的结果。想想曾几何时,日记和书信都是白纸黑字的罪证,而今的日记和书信却被主人大肆发布在网络上,时代到底是不同了。
我闲时随便翻翻,久而成为生活习惯,读书偶有会心,不免也顺手记一点感想。聚书日多,对书话一体就有了格外的爱好。书话如果粗分,当为“得书记”和“读书记”两类,而今旧书颇不易得,新书多来自网购,“一点掌故,一点故事”都无从谈起,剩下的一点散文抒情的气息,也就成了脱皮之毛,无所附丽。所以我尝试的日记体书话侧重于“读书记”,略记日常读书的思考,或有一得之愚。之所以要写成日记体,只为着它的不拘形式,可以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比拉开架势来写一篇书话,究竟要随意得多。这些年来,坊间日记体的书话渐成读书风景,有基于一刊的,如董宁文之《开卷闲话》;有基于一店的,如范笑我之《笑我贩书》;有基于一人的,如阿滢之《秋缘斋书事》、彭国梁之《书虫日记》,还有谢其章之《搜书记》、孙卫卫之《喜欢书》等等,都为书爱家们津津乐道。与这些名作相比,要说区别,则我的重在“读”书。我在《学步集》里主张书话要写出“读书之我”与“我读之书”。这些读书日记,是“我读之书”的一种表现吧。回头看,我觉得自己的尝试并非毫无意义。
我把《戊子读书记》和《有不读斋日记》做了一些删减,编为现在这个样子。我的本职是一名高中数学老师,和所有的高中数学老师一样,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备课、讲课、改作业或者批试卷,也要解题,也要练习,留给自己读书的自由时间,其实是不多的,甚或只有夜间的一点空闲。本来我们读别人的日记,就是想要从字里行间的闲笔里寻些趣味,现在把日记里与读书无关的事一概删除,倒好像我这个人整天除了读书,并不干别的事。这样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未免清雅得太不真实。您想象我并非如此清雅,也就是了。
好书名都给别人用过了。想给书起个名字,让它简洁一些,实在辞穷。只好先老实地叫个《夜读记》吧。想用《也是集》,表示这也是一本日记,也是一部书话,也是一种生活,可是这样别致简洁的书名,钱锺书先生用过,我就不敢再用了。读书多的朋友会说,钱先生这个书名也是抄来的。钱老抄得,你也抄得!也是!可是,我究竟还是不敢。
感谢孙卫卫先生、邱建国先生的勉力推荐。
也要谢谢您,乐意阅读这样的一本书。
2014年1月18日于有不读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