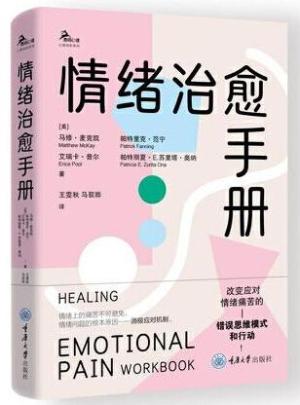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生物钟与抗衰革命
》
售價:HK$
109.9

《
压缩现代性的逻辑(西方韩国研究丛书)-以东亚视角重塑对现代性的认知,揭示现代东亚社会矛盾底层逻辑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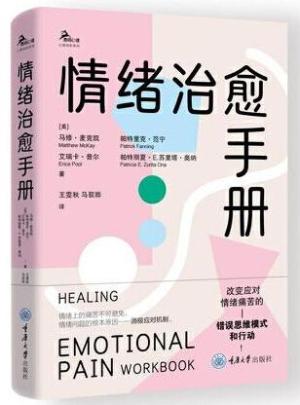
《
情绪治愈手册
》
售價:HK$
75.9

《
宋代文人与党争 知名宋代研究学者沈松勤代表著作 宋代党争史研究开山之作 全面讲解宋代朝堂之争和灭亡的内在根源
》
售價:HK$
195.8

《
执念(“执念”从不改变你的命运,只是让你发现命运)
》
售價:HK$
64.9

《
散落在书页上的出版往事
》
售價:HK$
74.8

《
中国统计学史
》
售價:HK$
547.8

《
投资你自己
》
售價:HK$
120.9
|
| 編輯推薦: |
|
著名书法家、作家、浙江美术馆馆长斯舜威继《随性论书》之后又一本书法随笔佳作。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作家、书法家斯舜威有关书法辩证法的随笔。分“阴阳方圆”“清浊柔刚”“俯仰动静”“骨肉肥瘦”“繁简易难”“雅俗取舍”六辑,共收录随笔五十四篇。这些随笔,每篇二千字左右,分别对书法学习和创作中阴与阳、方与圆、大与小、古与今、白与黑、圆与阙、纵与横、曲与直、虚与实、清与浊、柔与刚、浓与淡、藏与露、与重、正与副、真与似、离与合、生与熟、俯与仰、动与静……等五十四对矛盾进行了思辨式的阐述。认识书法中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现象,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可以从中领略到书法艺术深刻的哲学内涵,不但能够为欣赏书法作品提供一把新的钥匙,而且有助于在创作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书中附相关书法图片100余幅。
|
| 關於作者: |
斯舜威,现为浙江美术馆馆长,国家一级美术师。曾任《美术报》总编辑达十年之久,长期从事书画理论研究及创作。出版的书画学术著作有:《学者书法》《名家题斋》《百年画坛钩沉》《中国当代美术30年(1978-2008)》《海上画派》《陈之佛致傅狷夫手札69通释评》等。另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多部。系《书法报》《书法》《青少年书法》《光明日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等多家报刊的专栏作者。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本社已出版其书法随笔集《随性论书》。
|
| 目錄:
|
序论:笔底矛盾,书中乾坤
第一辑 阴阳方圆
阴与阳:负阴抱阳,外柔内刚
方与圆:方以圆成,圆由方得
大与小:结密无间,宽绰有馀
古与今:继古开今,推陈出新
白与黑:分间布白,计白当黑
圆与阙:月有阴晴,圆阙相因
纵与横:四方取势,纵横有象
曲与直:能伸能屈,方可为书
虚与实:阴阳互补,虚实相随
第二辑 清浊柔刚
清与浊:腹有诗书,激浊扬清
柔与刚:乾刚坤柔,刚柔相济
藏与露:用舍行藏,神奇出焉
轻与重:轻重于心,妙用乎手
正与副:笔心副毫,将帅齐心
真与似:拟之者似,几欲乱真
离与合:妙在能合,神在能离
生与熟:生中求熟,熟中求生
第三辑 俯仰动静
俯与仰:俯仰之间,气象万千
动与静:静以会神,动以观变
忙与缓:沉着痛快,宽猛相济
松与紧:执之欲紧,运之欲活
收与放:云卷云舒,收放自如
行与止:若行若藏,探骊得珠
深与浅:水到渠成,深浅自知
疏与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
疾与涩:宛若龙转,如推若引
第四辑 骨肉肥瘦
肉与骨:骨肉匀停,爽爽有神
肥与瘦:肥瘦相和,骨力相称
老与少:老少皆宜,人书俱老
老与嫩:通会之际,老嫩皆宜
巧与拙:大巧若拙,保持本真
长与短:随体结之,各有分寸
迟与速:迟速妍劲,刚柔相济
呼与应:起承转合,相呼相应
强与弱:强者弱之,弱者强之
第五辑 繁简易难
繁与简:以简驭繁,删繁就简
易与难:虽难亦易,虽易亦难
润与燥:润含春雨,干裂秋风
湿与干:干墨湿笔,湿笔干墨
擒与纵:中宫收紧,张弛有度
意与法:法随意远,意由心生
肆与谨:闳中肆外,穷幽极渺
平与险:平正险绝,不为腾溢
顺与逆:将欲顺之,必故逆之
第六辑 雅俗取舍
雅与俗:避俗求雅,雅俗共赏
取与舍:取舍万殊,取法乎上
奢与俭:书合于礼,俭得奢失
奇与正:奇正相生,循环无端
专与泛:博古通今,自成一家
提与按:提按顿挫,千古不易
违与和: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乖与合:五合交臻,神融笔畅
常与变:兵无常阵,字无定形
后记
|
| 內容試閱:
|
纵与横:四方取势,纵横有象
“纵与横”,即纵向和横向。南北曰纵,东西曰横;经曰纵,纬曰横。
书法书写,不管是从左到右,还是从右到左,或是从上到下,都如同阡陌交通,大道朝天,经天纬地,交错互织,纵横取势。
确实,书法的章法布局,不管如何千变万化,都离不开横向、竖向两端,不是纵,就是横,纵则从右到左,横则从左到右。这种取势,讲求承前启后,承上启下,左顾右盼,左右映带。纵横得当,便收奔放自如、汪洋恣肆之效。纵为竖画,笔势向上下伸展,不仅仅拓展长度、高度,更在于增添挺拔伟岸之气。书法家们写行草、狂草时,往往会在一篇中选择一两个、数个适宜于拉长的字,在作竖笔或左下方撇时,作纵情的延伸,如瀑布悬挂,白练飘逸,或大漠孤烟,气贯霄壤,一笔就占据数个字的位置,成为全篇点睛提神之笔。横为横画,横势是行笔向左右拉伸,增加字体的宽阔度,同时增加开张舒展之气。古人云“横如千里之阵云”,谁能一笔写出阵云的模样?谁都不能,但谁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一横要写得舒展开张,并有起伏之势。以这“一横”之理推及整个横势,其理不言而喻了。相比而言,“纵”可以极度夸张,一笔下去,兴尽乃止,有的甚至产生顶天立地的效果;而“横”则有所节制,一般情况下,不会一横就占据数个字的位置,更不会如同门杠一样拦腰横上粗粗一笔。
写字如同做体操、练八段锦,拉伸、舒展时尽量拉伸、舒展,手与脚似乎有着无限的延伸的可能性,以与天人合一;但始终掌握重心,否则便站立不稳。字也一样,不管纵横如何拓展、延伸,“中宫”始终是收紧的,凝气成团。主纵主横,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取向,不同的书法家也有不同的偏好。一般而论,自殷至秦,书体大体取纵势,如殷墟的甲骨文全部都呈纵势。汉魏、晋、南北朝书体多呈横势。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如魏晋时钟繇书法取横势,王羲之大体取纵势。唐代欧虞柳取纵势,褚薛颜取横势。宋代米黄取纵势,苏蔡取横势。法无定法,纵横皆宜。在整幅呈横式的作品中,也不排除个别字体呈纵势,以求整体和谐。如王珣的《伯远帖》,整体是呈横势的,字体较扁,横向用力明显,为了避免单调,个别字则作了拉长处理,这就叫作横中有纵。赵孟頫《胆巴碑》也是整体取横势,兼取纵势,纵横相间,端庄中不乏潇洒之姿。
孙过庭《书谱》云:“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又云:“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元常就是钟繇,他不写草书,只写楷书,却也精于使转,可见楷书也需要强调使转纵横。
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谈了他特地到东洛向张长史请教笔法的经过,有一段对话颇有意思:“乃曰:‘夫平谓横,子知之乎?’仆思以对曰:‘尝闻长史九丈令每为一平画,皆须纵横有象,此岂非其谓乎?’长史乃笑曰:‘然’。”又曰:“‘夫直谓纵,子知之乎?’曰:‘岂不谓直者必纵之不令邪曲之谓乎?’长史曰:‘然。’”在颜真卿和张旭的对话中,“纵横有象”四字已经把纵横问题高度概括地说明白了。所谓“有象”,就是纵横得宜后呈现出的气象、景象。宋代朱长文《续书断》中列颜真卿的书法为神品,并评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
“纵横”二字,是历代作家、书评家笔下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
陆游《跋乐毅论》云:“《乐毅论》纵横驰骋,不似小字。”
解缙《春雨杂述》云:“上字之于下字,左行之于右行,横斜疏密,各有攸当。上下连延,左右顾瞩,八面四方,有如布阵。纷纷纭纭,斗乱而不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破。昔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纵横曲折,无不中意。”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祝京兆季静园亭卷》云:“祝京兆书《季静园亭诗》以大令笔作颠史体,纵横变化,莫可端倪。”
蒋衡《拙存堂题跋》云:“于法度森严中纵横奇宕,所谓端庄杂流丽也。”
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云:“纵横者,无处不达之谓也。”
孙退谷《庚子消夏记》云:“然纵横之极,却笔笔不仿古人,所谓如‘屋漏痕’‘折钗脚’,此其是矣。”
李瑞清《匡喆刻经颂九跋》云:“《鹤铭》取势纵,故字形长。此则纵横兼备,无法不备也。”
姚盂起《字学忆参》云:“字之纵横,犹屋之楹梁,宜平直,勿倾欹。”
不同书体,对纵与横也有不同的要求与取舍。如隶书取横势,篆书取纵势。楷书结体方正,根据书法家爱好不同而表现出或长或扁的形态,草书普遍偏长形,但也有扁状的。不管纵横如何,有骨力,有气韵,则自然美观。
曲与直:能伸能屈,方可为书
大自然到处都是有形的曲与直,树木的枝干有曲有直,河道溪流有曲有直,大道小路有曲有直,各种建筑有曲有直。杭州有九溪十八涧,诸暨有五泄,以为那山那水已经“曲”尽其妙,而到了贵州荔波小七孔,发现在十多公里峡谷里竟有六十八道跌水瀑布,真是无地不曲,处处见奇了。人世间还有无形的曲与直,比如人生经历有曲有直,世态万象有曲有直,公私事务有曲与直,人人几乎无日不面对是非曲直等问题。做人贵直,中直、正直、刚直,都是很好的品质,离开直,人就不可能直立于世。但“直”并不排斥“曲”,有道是大丈夫能伸能屈,没有“曲”的“直”很可能走向极端,乃至于绝途。退一步海阔天空是“曲”,韩信胯下之辱是“曲”,勾践卧薪尝胆是“曲”,苏轼被一次次贬到黄州、惠州、儋州是“曲”不单单人,社会也是在曲折中前进的。“曲”并不意味着退缩、懦弱,相反,在很多时候“曲”是一种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大智慧。为文亦如此,袁枚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而“人贵直,文贵曲”一直是文章家们普遍认可的准则。另一方面,文章又讲究开门见山、开宗明义,这便是“直”,只曲不直,那文章便成“博士买驴,书卷三纸,未有驴字”了。
书法更是曲中见直、直中见曲的一门艺术。笔画线条不可能处处都是一条直线,或处处都是曲线,甚至在一条笔画中也有直有曲。王羲之在《书论》中总结出“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若直笔急牵裹,此暂视似书,久味无力。”他把迟急、曲直、藏出、起伏并列为书法必备的要素,又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提出“每作一波,常三过折笔”的主张,一波三折便是“曲”,可见“曲”在他心目中有着相当的重要性,书法正是一门“曲直”的艺术。
曲和直,既指笔画线条,也指汉字结体,更指书法章法。曲直与方圆有着密切关系,方中有直,直中有方,曲中有圆,圆中有曲。从大的方面来说,圆恰恰是曲的一种形态。当然,两者还是有区别的,是不同的书法美学概念。作为方块字,汉字的基本笔画横、竖、折、撇、捺所表现的皆为曲与直的基本形态,哪怕最简单的点,在书写时也蕴含着曲与直的要素。在指导初学者的“点”的写法的图示中,那“点”里演示笔锋走向的箭头恰似一个钩,曲得很别致。书法以汉字为载体,自然承袭了汉字的方正的形态特征,但书法线条的曲与直,绝非简单的曲与直,而是曲中有直,直中有曲,横与竖是直线条,却有波折的意味在,带有曲,否则,变成僵化的美术字了。
从汉字字体演变历程来看,甲骨文是刻写的,易直不易曲,以直线为多,转折也硬劲有棱角,曲中带直。金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直笔中带有曲意,转折处有明显的圆痕。小篆用毛笔书写,变得圆润流美,使转自如,使转处以圆为主,但线条还是讲究直,铁线篆、玉筯篆,听那名字便觉得是直线。陈澧《摹印述》云:“篆书笔画两头肥瘦均匀,末不出锋者,名曰‘玉筯’,篆书正宗也。”说的是书写时线条无粗细变化,竖笔无垂脚,且结体圆长。这种笔法出自李斯《泰山刻石》,点画谨严,字体修长,字型大小一样,章法纵横有序,别具姿态。后人将用笔圆浑遒劲的其他字体亦称为“玉筯”。当然,篆体字转折处环曲的弧线是其主要特征,这便是曲,以曲为主,曲中有直。隶书线条则由小篆的圆曲,改为方直。而隶书的书写,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强调“蚕头燕尾”“一波三折”,这就是直中有曲。隶书之美,首先在方直之美。楷书形体方正,线条平直,曲直分明。草书笔画则呈曲笔圆势,直线也带有曲意,以曲为其主要美学特征。
书法作品的章法,非常注重曲直之道。篆、隶、楷不必说,行距、字距排列布局严整有致,曲直有度。草书布局,看似“曲”,甚至“乱”,其实整体还是“直”的,形曲而骨直,形曲而势直。一句话,曲折错落,有序有度。否则,杂乱无章,形势全无,便没有美感了。我曾经以农民种田比喻书法布局:“农人种田,极重布局,所谓横是横,直是直。横呈弧形,则直线必歪;直线一歪,则一亩皆乱。田欲种直,若一株紧跟一株,反易游动;若隔株对齐,甚至三株左三株右,近看似乱,远观则笔直如棍,全田井然。如此乱中有序之法,于书法布局,未知有否裨益?”这是自己的真切体会。
书法用笔,也蕴含曲直之道。古人说“无往不收,无垂不缩”,强调的是用笔的回锋与收缩,收缩之间,顿挫提锋,欲往而返,在不经意间,已经将曲直的原理贯穿到毫端。提、顿、留、驻,用笔到精微处,自有曲直之妙。
曲和直,还和柔与刚有关。赵宦光《寒山帚谈》云:“直则刚,曲则柔。”然而,一味直,没有曲,并非刚劲之道。“永字八法”中直竖称“努”,柳宗元《八法颂》云:“努过直而力败。”唐太宗《笔法诀》云:“努不宜直,直则失力。”他们都强调竖画不能过直,过直反而无力,要带有一点曲意,才有动势。曲之柔也同理,没有一点“直”的味道,那“柔”便显得绵弱了。
赵宦光《寒山帚谈》还说:“古字直,今字曲,时也,习也。小儿直,老人曲,势也,趋也。学则直,不学则曲,正学也。学古则直,学今则曲,俗学也。”这段话,信息量非常丰富,似乎已经超出了书法本体之外,可以细细咀嚼,体会其话外之意。
虚与实:阴阳互补,虚实相随
“虚”是中国古代哲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与“实”相对。周易的阴阳学说道出了“虚”与“实”的本质,大千世界就是由“虚”和“实”构成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图分交互抱的阴阳两个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最高智慧的体现。这种虚实相随、有无相生、相反相成的运动图式,恰好是“虚”与“实”的最形象化阐述。蔡邕说:“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这“阴阳”,就是“黑白”,就是“虚实”。
老庄哲学对“虚”和“实”也有淋漓尽致的阐述。《老子》开宗明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这里所说的“道”之“无”与“有”这一矛盾的统一体,就是与“虚”与“实”相对应的概念。老子又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河上公注曰:“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虽自知昭昭明白,当复守之以默默,如闇昧无所见,如是则可为天下法式。”后以“知白守黑”谓韬晦自处,但书画界则一直根据老子的思想,将“知白守黑”“计白当黑”当作一种非常重要的创作思想和表现手段。中国的书画世界,又称水墨世界,就是由“黑”和“白”、“虚”和“实”组成的。不懂黑白真谛、虚实之道,就无法进入中国书画之门。庄子的“虚室生白”(《庄子·人间世》)也值得关注,虚,使空虚;室,指心;白,指道。庄子认为心无任何杂念,就会悟出“道”来,生出智慧。这里的“白”虽然指的是“道”,但每当看到这四个字,我们还是会联想到“虚”和“白”的对应关系。长期以来,许多书画家都奉“虚室生白”为圭臬。
其实,非独老庄所说的“无”“白”,包括佛家、禅家所说的“空”“寂”,都属于“虚”的范畴。虚静、虚灵、虚无、虚幻、虚白、虚名、虚寂、致虚极,等等,表述各异,意思相似。如“虚静”指人的精神进入一种无欲无求的非常宁静的状态;虚灵指返璞归真、宁静荡淡而富有智慧;虚无指道的本体,性合于道,有而若无,实而若虚,故能包容万物;其余的意思,大致如此。
“实”是会意字,从宀,从贯。宀是房屋,贯是货物,货物充于屋下即为实。本义为财物粮食充足,富有。除了富有,还有满、塞、荣的意思。哲学概念的“实”,是与“虚”相对应。离开了“虚”,“实”也无所依托,无从成立,万事万物莫不如此。如果太“实”了,缺乏“虚”,也是不行的。就中国书画来说,过于“实”,便显得死板、僵化。
“虚实”关系落实到书法美学上,最显而易见的对应关系便是“黑白”,“黑”为“实”,“白”为“虚”。也即毛笔留下的笔迹为“黑”,经由笔迹分割而形成的空间为“白”。有点画处为实,无点画处为虚;浓湿处为实,淡枯处为虚;密处为实,疏处为虚。一句话,眼睛能够看到的为“实”,眼睛虽然看不到,但在一幅书法作品中无法脱离、可以感知、可以引起联想的为“虚”。“虚”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因“实”而赋予意义的一种存在。比如一张空白的宣纸无所谓“虚”,而当书法家在宣纸上动了笔墨之后,那空白处便形成了有生命气息的“虚”,由此可见,无论“虚”还是“实”,都是书法家心灵世界的再现。“黑”是有形的,“白”是无形的,不管有形还是无形,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相互依存,形成对比,形成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共同体。书法家的思想感情、笔墨技巧、旨趣情怀,就通过这“黑白”“虚实”的灵活转换、变化而表达出来。
书法的虚实关系,直观地说,我们欣赏一幅书法作品,如果疏密得当、布局合理、浓淡适宜,就会赏心悦目,觉得舒服,也会自然而然感受到笔墨所传递的美感。但是,如果行距、字距太过紧密、局促,就太“实”了,看了不舒服。一些初学者在抬头、天地处留的空间太大、太散,行与行之间、字与字之间距离太大,松松垮垮,就未免太“虚”,影响美感。可见“虚”与“实”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关系到书法作品的内在生命,不可不引起高度重视。通常所说“行气”,指的就是一种“疏密”“虚实”关系所产生的感觉。
我们通常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虚实”关系:一是执笔方法,所谓掌虚指实,掌虚,才能灵活运笔,指实,才能运笔有力;二是结构布局,通过满与空所体现的虚实变化,使得全篇充满生机;三是笔画枯湿、浓淡的变化而产生虚实效果。
董内直《书诀》云:“指欲实,掌欲虚。”当年王羲之从童年王献之背后去掣笔,不动,于是认为是儿当有出息。其实这只能说明幼年王献之已经做到了“指实”,而这样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掌虚”,方能运笔自如。否则,死死抓住笔杆,任何一个蛮汉都会,实则实矣,又有何用?
赵宦光《寒山帚谈》云:“骨力者,字法也;韵度者,笔法也。一取之实,一得之虚。”赵宦光认为骨力得自字法,韵度得自笔法,一实一虚。能否将字法与笔法如此截然分开,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只有虚实结合,才能既有骨力,又有韵度,这一点,是值得深思的。
在笔画线条中,也有虚实变化,提按顿挫,使转收放,或轻或重,或疾或徐,或圆笔或方笔,都会产生阴阳、黑白的丰富细微的效果,说到底,这也是书法的“虚实”。进入新时期后,书法家们对书法的“虚”和“实”进行了更为广阔的探求,超出了传统书法创作的习惯性思维,如有的作品,有意留下大量的空白,在空白处适当以印章压一下,产生特殊的视觉效果。有的现代书法创作,将整张纸都用浓墨覆盖,连落款、钤印的空间都几乎没有留下,那么,这样的书法是不是没有“白”、没有“虚”了呢?也是有的,书法家将“白”“虚”留到了作品之外,让观众自己去生发联想。
“虚”和“实”的最重要一环,归根到底在于作品之内、作品之外的关系。一幅书法作品的客观存在,外观呈现是“实”,是“作品之内”,这幅作品所散发出的神韵、气息是“虚”,是“作品之外”。一幅优秀的书法作品,不但要致力于“作品之内”,更要营造“作品之外”的韵味。当然,说“营造”,只是一种不很确切的表述而已,韵味不是靠“营造”出来的,而是得之于长期的学养积淀和技法训练,是书法家生命的外化。要做到这一点,还是记住并践行老子的六个字吧:“致虚极,守静笃。”让自己的书法生命虚灵到极点,没有一丝杂念与污染,空明一片,湛然朗朗,虚一浑厚,静而至静,专心问艺,全神修炼,以成正果。
清与浊:腹有诗书,激浊扬清
中国古典哲学非常讲究“气”,认为气是宇宙间万事万物之源。人的生命与气密切相关,精神状态与气密切相关,人所创造的艺术品也与气密切相关,而气有旺衰之别,清浊之分。我高中毕业后当农民,没有书看,到处借书,抄书。有一次意外地借到了一本《袁柳庄相书》,手自抄录,倒背如流,对功名富贵之相早已不甚了了,而人相之清浊,则影响颇深。大凡在应酬场合遇见人,先观其清浊如何,遇到官不小、钱不少,但浊气熏天的,赶紧敬而远之;虽然没有富贵可言,但清气怡人,谈吐不俗的,则乐于结为布衣之交。
自古诗文与书画,皆有“清”与“浊”之分。曹丕《典论·论文》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中国历代文论选》注:“清浊,意近于《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气有刚柔。’”刚近于清,柔近于浊。字亦有清浊与刚柔之分。有的字,开卷便觉清气拂拂而来;有的字,入眼便觉恶俗不堪。清浊之间,刚柔自分。
人之清浊与地位高低、职务无关。自古官场乃藏污纳垢之地,俗客云集之所,虽不乏清俊豪迈之士,但总体来说难脱一个浊字。字之清浊,同样与书家的身份无关,与是否获奖无关,与是否畅销无关。一旦评奖体系的把持者既浊且俗,能够入其“法眼”,有幸“获奖”的作品要不浊不俗,可能吗?而市场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场所,虽不能说凡是沾上了买卖就带有铜臭味,但带有一定的浊气也是在所难免的。
泾渭有清浊,人品有清浊,语音有清浊,天地有清浊,书法有清浊,只要有气存在,清浊便随之而来。浊不可怕,贵在激浊扬清,而切不可清浊混淆,同流合污。
赵宦光《寒山帚谈》云:“作字作绘,并有清浊雅俗之殊。出于笔头者清,出于笔根者浊。雅俗随分,端在于此,可以慎择!”赵宦光的前半句是对的,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有清浊雅俗之分。后半句有一定道理,但未免偏颇。书法固然以出于笔头为上,出于笔根无异于蛮汉犁地,那粗鲁的动作已经俗了几分,但是,出于笔头者也未必清。清和浊,关键在于书家本身的清浊。雅人固然未必能写出雅字,然俗汉写出清字,则更属天方夜谈。
苏轼《和董传留别》诗云:“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用到书法上,是恰到好处的,只有“腹有诗书”,书法之气才可能“自华”。熟悉整首诗的人恐怕不多,但“腹有诗书气自华”一句却是广为流传的,这句诗也确实写得好,写出了中国书画艺术的真谛,只有注重知识积累、学养提升、学问增长,才能升华人的精神境界,才可能创作出“气自华”的优秀作品。苏轼的这一句诗,可以作为“清”与“浊”的最好注脚。
“清”与“浊”也是鉴赏书画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看一件书画作品的真伪、好坏,首先看其整体气息,是清还是浊。笔墨可以模仿,乃至“逼真”,唯有气息、气韵是无法模仿的。就如同人,一些出演领袖人物的特型演员,哪怕样子有几分相似,举手投足和方言语气也模仿了不知多少遍,但一看便见其浅显,甚至拙劣,气质、气局远远达不到那个份上,这是通过短期努力所无法改变的,奈何奈何。
柔与刚:乾刚坤柔,刚柔相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柔刚”是与“阴阳”相对应的影响极为深远的哲学思想和美学概念。《周易》云:“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又云:“乾刚坤柔。”从而将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自然万物都归纳到“阴阳”“柔刚”的范畴之中。老子进一步提出了“刚柔相济”的理论体系,提出了“柔弱胜刚强”“以柔克刚”的哲学命题。
刚与柔,并非绝对的,更非对立的。百炼钢成绕指柔,此柔,乃至柔也,于是至刚。两千多年前的越王剑,深埋地下,埋时不慎被压弯,谁料出土后依然能够复原,能够伸屈自如,能够削铁如泥,非至柔,能够达到如此至刚的境地吗?可以至柔则至刚,至刚则至柔,两者是统一的。
书法艺术上合宇宙之道,下合人生之道,自然也在“阴阳”“柔刚”的统领之下。书法艺术所追求的“柔刚”,正是天地万物的柔刚的体现。轻风行云是柔的,书法有时似轻风行云;疾风暴雨是刚的,书法有时似疾风暴雨;山刚水柔,书法有时似高山流水;山有刚有柔,水有柔有刚,似山似水的书法也柔中有刚,刚中有柔。春风拂柳与秋风落叶,信马看花与铁马金戈,微醺花前与醉卧沙场,凡此各类景态,在书法中都有鲜明的呈现。
毛笔之毫是软的,写出的字却是刚的。见人写字,喜欢以硬毫笔、短毫笔写“硬字”,喜欢将笔揿至底部,似乎笔力千钧,其实大谬。中国书法的特点,恰恰在于“笔软而奇怪生焉”,恰恰因为是软毫,可以八面出锋,可以将全身精气神凝于毫端,可以化至柔为至刚,懂得此理者,方可以言书法。有的书法家喜欢用长锋羊毫写大字,写硬字,见功力,也见刚性。墨如水,也是柔的,写成书法,却能产生钢铸般的、岩石般的效果,极具刚性。宣纸也如此,是软的、轻的、柔的,却纸寿千年,不蛀不腐,呈现刚的一面。
老子的伟大在于,他发现了“刚”的最高境界是“柔”,因为柔能克刚,至柔至刚,柔比刚还刚。水与石孰柔孰刚?看似水柔石刚,日深月久,却水滴石穿,水终究比石厉害,故云“上善若水”,因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书法“至柔至刚”,恰恰和“水(墨汁)”结合在一起了。羊毫、狼毫至柔,水(墨汁)至柔,经过书法家之手,当书法家把思想感情、笔墨技巧都倾注于其中时,却能够石破天惊、天崩地裂、怒涛拍岸,产生“惊天地,泣鬼神”的效果。
细而言之,书法艺术的方方面面都有柔与刚的对应关系,笔墨纸张有柔刚之分,笔法、墨法、结体法、章法也有柔刚之别。行笔的整个过程,起与收,快与慢,中锋与侧锋,都可区分出柔与刚来。俗话说“力透纸背”,应该说的是刚,然而,要想达到这一效果,用力运笔肯定适得其反,而是要用内敛之气,缓慢行笔,将无形的气韵倾注于笔端,渗透到纸上。有的笔画,看似粗重有力,实则锋芒毕露,气息外泄,神散韵淡。有的笔画看似纤细柔弱,似悬针,似垂露,似银丝,却是刚的,有精神的。
清朝的沈宗骞提出了“刚德”“柔德”的概念。他列了“劈空而来,天惊石破”,“挟风雨雷霆之势,具神工鬼斧之奇”等一长串排比句,得出“此能尽笔之刚德者也”的结论,又列了“柔如绕指,软若兜罗”,“摇曳天风,具翔凤盘龙之势”,“恍惚无常,似惊蛇之入春草”等一长串排比句,得出“此能尽笔之柔德者也”的结论,并指出“二美能全,固称成德。”这应该是阐述书法艺术刚柔相济的妙文了。
我们还可从太极拳得到启发,太极拳以阴阳辩证理念为核心思想,是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传统拳术,达到了至柔至刚的境界。太极拳与书法极为相似,比如,太极“棚、捋、挤、推、按”和书法“横、竖、撇、捺、点”之间就有密切关系。两者都带有很强的技巧性,而技巧性的最高境界,则是看不出“技巧性”,大巧若拙,浑然天成。再如,动作和运气的关系问题。太极和书法的动作,都离不开运气。动作规范、娴熟、柔和,有助于气脉贯通,于身体则通体舒泰,于书法则气韵生动。运气的关键,在于静下心来,全神贯注。书法与太极的不同之处在于,书法还须再进一步,将这种“心手相应”的感觉传递到笔端毫尖,倾注于纸上,生发为墨迹。在重心的把握上同样如此,太极的每个动作转换,两条腿在移动时都十分自然地实现了全身重心的转移,每时每刻都保持重心的稳定,形体上不管展现什么动作,重心都是坚如磐石的。书法同样如此,可以奇崛狂野,可以疾风暴雨,可以长袖善舞,不管笔法如何变化,笔势如何奇险,字体的重心必须是稳固坚实的。重心稳固了,动作看似柔和,却绵中带刚,具有势不可当的力度。此外,太极有“欲左先右,欲上先下”之说,而书法则有“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之诀,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强调的是回锋、回势,一种循环往复的圆满,一种天衣无缝的和谐,以保持用笔、用拳的圆润、稳健、有力。从这一对比中,或许能对柔刚之道作出一个形象的说明,体味出太极和书法共通的美的奥秘。
中国古典书论中论述柔刚之道的妙语很多,如赵宦光云:“一于刚则不和,过此乖矣。一于柔则不振,过此糜矣。”诀云:“刚纵其柔,柔纵其刚。”沈宗骞云:“然其寓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所谓百炼刚,化作绕指柔,其积功累力而至者,安能一旦而得之耶。”诸家所论,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对老庄哲学的领悟与阐发。书法家应该多读读老庄,则柔刚相济之道不言而自明矣。
浓与淡:流雾屯云,浓淡相宜
“浓”与“淡”属于书法的墨法范畴,也属于书法风格的范畴。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古代书论中,与“浓”相对的概念,似乎并非“淡”,而是“纤”“轻”“薄”“浅”等。如“浓纤说”:梁武帝云“浓纤有方”。庾元威《论书》云“浓头纤尾,断腰顿足,一八相似,十小难分”。蔡邕《隶书势》云“纤波浓点,错落其间”。张怀瓘《书断》云“然割析张公之草,而浓纤折衷,乃愧其精熟”。“浓轻说”:欧阳率更云“萧侍中飞白,轻浓得中,如蝉翼掩素”。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赞》:“至若寻翰墨轻浓之势,穷点画分布之能,与日弥深,随见逾妙。”又云:“翻飞露白,乍轻乍浓。”张怀瓘《书断》云:“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浓之势。”“浓薄说”和“浓浅说”:窦臮《述书赋·语例字格》注“不伦”曰:“前浓后薄,半败半成。”张怀瓘《书断》云:“浅如流雾,浓若屯云。”
不过,应该说纤、轻、薄、浅,都含有“淡”的意思在,所以姑且还是按照现代词语组合习惯把“浓”和“淡”放在一起来欣赏。
墨分五色,是中国画最基本的技法,中国书画的精妙处,全在墨色变化之中。墨分五色指以水调节墨色多层次的浓淡干湿,语出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运墨而五色具。”何谓“五色”,说法不一,或指焦、浓、重、淡、清,或指浓、淡、干、湿、黑,也有加上“白”而合称“六彩”的。到底指哪几个,并不重要,只要知道实际上指的是墨色运用有着丰富的变化即可,而不管哪一种说法,其中都有“浓”和“淡”。这说明,“浓淡”的美学概念,在唐朝时已经提出并使用。
一般而言,浓墨显得庄重,淡墨显得清雅。从汉魏到晋唐,书法家们普遍对浓墨推崇备至,对淡墨则运用不多,人们普遍觉得淡墨难以体现书法的神采,无法凸显书法的气韵。孙过庭《书谱》所说“带燥方润,将浓遂枯”,所表达的便是浓墨所产生的特有效果。“文人画”“文人书法”兴起之后,书画家们开始对“淡墨”有了新的认识。也即从宋代“淡墨”普遍进入了书画家的审美视野,特别是在元明清,对淡墨的使用更是广泛地进入到创作领域,人们对淡墨赋予了新的内涵。
就中国画而言,通过墨色的浓淡,能有效解决山水画的透视关系,表达出通常所说高远、深远、平远“三远”的远近层次,也能表达花鸟画草木的荣枯、茂衰、疏密关系,还能处理好人物画的明暗关系,更能渲染出特殊的悠远、淡雅的神韵。就书法而言,用笔浓淡变化,能够体现书家的情感活动和精神气韵。墨汁的浓淡效果,肯定不如手磨之墨。古人用墨,大有讲究,不但用手磨之墨,且根据不同创作,对松烟、油烟亦有不同要求和使用方法。当然,古代也没有墨汁,墨汁的发明,给书画家带来了很大便利,却不利于墨色的发挥,很难做到墨分五色。现在不少书法家贪图方便,习惯于用墨汁,加上现在写大幅作品、巨幅作品较多,全部用手磨之墨也吃不消,哪怕用磨墨机也未必来得及,所以墨汁大行其道。墨汁虽然也可以通过加水、用笔蘸水来调节浓淡,但毕竟层次不多,装裱之后效果往往不理想。用墨汁写书法,写好后看似光亮,装裱后却反而变得灰淡,层次单一;手磨之墨汁,写好后似乎灰淡,装裱后却显得精神,层次丰富。
一般而言,写篆隶,最好用浓墨,写行草,则以淡墨为宜。明清二代科举考场盛极一时的“台阁体”“馆阁体”,以方正、光洁、乌黑、大小齐平为基本特征,自然以浓墨为主,而不适宜用淡墨。明之后以淡墨闻名的书家不少,明代董其昌擅长用淡墨,这与他天真散淡的美学追求是相统一的。清代王文治也喜欢用淡墨,潇疏秀逸,有“淡墨探花”“淡墨翰林”之誉,与其并称的刘墉则称“浓墨宰相”。王文治的书法早年从前辈笪重光入手,楷书习褚遂良,行草书则学《兰亭序》和《圣教序》,又学赵孟頫和董其昌,中年后改习张即之。他的字线条扁薄,点画妩媚匀净,结体飘逸婉柔,可明显地看出与笪重光、董其昌的传承关系。他喜欢用长锋狼毫,中年以后潜心禅理,这些都是他偏爱淡墨的由外及内的原因和手段。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云:“国朝刘石庵相国专讲魄力,正梦楼太守则专取风神,故世有‘浓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目。”钱泳也将他与刘墉、梁同书作比,认为王文治中年临摹张即之书迹,遂入轻佻一路,如同秋娘傅粉,骨格清纤,姿态自佳,而欠庄重。钱泳之论带有贬义,但对王文治的书风特色的譬喻还是精准的。乾隆南巡江南时,在杭州寺庙中见到王文治所书《钱塘僧寺碑》,大为赞赏,王文治的书法声望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广为流传。当时竟有“天下三梁(指梁同书、梁衍、梁国治),不及江南一王”之说。在现当代,“草圣”林散之更是擅长用淡墨的妙手,将水墨的濡化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林散之重视墨法,与他师承黄宾虹有着很大的因果关系。黄宾虹是国画大师,也是运用墨法的大师。他在吸收古人墨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七种墨法。他认为:“墨法七种,古人墨法妙于用水。水墨神化,仍在笔力。笔力有亏,墨无光彩。”这七种墨法分别是:浓墨法、淡墨法、破墨法、泼墨法、渍墨法、焦墨法、宿墨法。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浓墨法和淡墨法,其他数种,也无不与此有关。如破墨法,“画选淡墨,破以浓墨。亦有先用浓墨,以淡墨破之。如花卉勾筋,石坡加草,以浓破淡,今仍有之。浓以淡破,无取法者,失传久矣。”完全是一种浓墨、淡墨的交替使用。泼墨法也有浓有淡,而渍墨、焦墨、宿墨,则偏向于浓墨。“黑团团里墨团团,黑墨团中天地宽”,这是石涛的题画诗,也是黄宾虹作品的真实写照。特别是晚年,他的山水画一次次用宿墨濡写、叠加,厚重、浓黑得无可复加,是“浓墨法”的杰出代表。林散之的作品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再加上他得益于黄宾虹用水用墨,而在淡墨运用上别出心裁,又喜用长锋羊毫在生宣上挥写,故墨的层次丰富,极具鲜明的艺术特色,不仅不缺乏神采,反而增加了一种深远朦胧的意境。
浓墨运用的技巧,古人有“浓墨轻用”之说,要点在于提得住笔,沉得住气,笔笔到位,而无拘促之感。苏轼堪称用浓墨的典范,他的书法“无意于佳乃佳”,其笔墨有如蚕之吐丝,笔笔牵连,宇字相生,气势内敛而极具动势。其用墨非常“黑”,乃至于“乌黑”,如小孩之点睛。淡墨的使用方法,前人总结出三种:一是用清水将浓墨稀释冲淡后使用,二是笔毫先蘸少许浓墨,再多蘸清水后运笔,三是笔肚饱蘸清水后,笔锋蘸少许浓墨使用。实际使用时,可以根据各人的喜爱、习惯,灵活运用。
欧阳询曾云:“墨淡则伤神彩,绝浓则滞锋毫。”浓墨、淡墨的运用,与书写内容也大有关系。淡墨固然不如浓墨亮丽,但是,如果书写内容是那种戴望舒、徐志摩式的带有“淡淡的哀怨”的内容,偶尔用用淡墨,很可能别有一番韵味呢!浓墨固然滞毫锋,但有的书法家借用山水画家宿墨作画的办法,用极厚重的宿墨写字,效果相当不错。
如果在同一幅作品里浓淡枯湿适当交替使用,将书法当作水墨画来创作,又该是如何一番情景?水墨画家们作画,喜欢用书法入画,曰“写”;一些书家,特别是在创作现代书法时,喜欢用水墨画法用笔,且不论其短长,作为一种创作手法的探索,至少可以聊备一格。当下一些书法家在进行大字创作、现代书法创作时,唯恐浓墨不够浓,尝试以掺入乙烯、丙烯等化工材料,而有的书法家进行似书非书、似画非画的“水墨创作”时,又淡得不能再淡。这说明,当代书法家已经把书法的“浓”与“淡”的技法探索,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