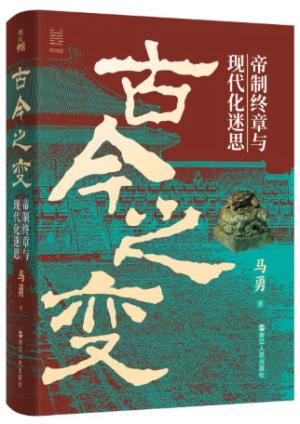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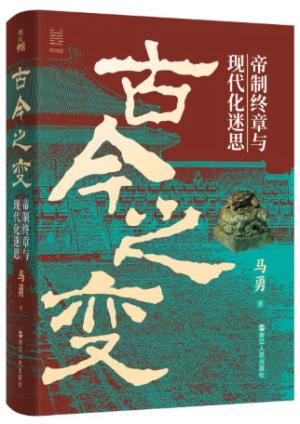
《
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
》
售價:HK$
107.8

《
存在的意义 11位心理治疗师的存在-人本之旅(孤独、意义、自由、敬畏、死亡交织在人生旅途中,推动我们
》
售價:HK$
93.5

《
达尔文的植物世界 跟随达尔文的试验与研究发现自然植物的奥秘 达尔文进化论植物篇
》
售價:HK$
165.0

《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引擎:中国创新的黄金时代2015-2025
》
售價:HK$
74.8

《
你永远有选择
》
售價:HK$
57.2

《
1848变革之年(理想,是“民族之春”,现实,是“血色夏日”,革命风暴席卷欧洲,旧时代的丧钟为新秩序
》
售價:HK$
85.8

《
拓客销售:可持续的营收增长
》
售價:HK$
75.9

《
骨与肉
》
售價:HK$
61.6
|
| 編輯推薦: |
★本书完美再现了那个纸醉金迷的“喧嚣的二十年代”,再现了盖茨比曾经徜徉流连的那个蓝调纽约城,同时却又在这块梦幻般的画布上构筑了一个精巧狡诈的悬疑故事,揭示了爱的谎言如何可以变成一场最危险的催眠游戏。
★本书将由福克斯探照灯电影公司改编为同名电影,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凯拉奈特利将担任主演。
|
| 內容簡介: |
1924年的纽约城——“爵士时代”那颗跳动的心脏。对于都市女性而言,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摩登世界。维多利亚时代的旧式道德禁忌被一扫而空,波波头、红唇与香烟、叛逆的地下酒吧成为了新女性们彰显自由的标志。但也有人对这个新世界感到陌生、抗拒,比如罗斯。作为一名在纽约城警局工作的打字员,循规蹈矩的罗斯依然在苦苦搜寻那个逝去年代的温情,搜寻着她在童年时代、在冰冷的孤儿院中未能得到的亲密友谊……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罗斯的梦想很快成真了。一个星期二的早晨,一个光彩照人的女孩儿走进了警局大门,成为了陪伴罗斯的“另一个打字员”。奇迹降临了:这个叫奥黛丽的摩登女郎与古板守旧的罗斯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密友。这是一位能够让所有女孩儿最疯狂的幻想成真的好闺蜜:罗斯搬进了她那间豪奢的酒店房间,与她分享堆满衣柜的高档时装,取之不尽的精致甜点,还有一次次在夜幕的掩护下闯入地下酒吧世界的探险之旅。搭乘着奥黛丽号快车,一度被时代远远抛在身后的罗斯一步登天,甚至连她那原本平淡无奇的相貌似乎都分得了一份好友的光彩,变得妩媚妖娆起来……
然而,罗斯不知道的是,自己并不是成为了凤凰的麻雀,而是被一步步诱进了一个金色的捕鸟器,而所有这一切流光溢彩的奢华与心心相印的姐妹情都只是一根根精致的带刺铁丝,直到整个故事的结局处才会砰然闭合…..
|
| 關於作者: |
|
苏珊娜兰德尔是美国莱斯大学美国现代文学博士生,《另一个打字员》是她的处女作,目前兰德尔正在创作第二部小说。
|
| 內容試閱:
|
他们说打字机让我们雌雄莫辨。
对这种设备报以一瞥,你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些自诩为女性美德与道德准则捍卫者的家伙,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拿一般的打字机来说,不管是安德伍德牌、老爷牌、雷明顿牌还是科罗娜牌,都面目严肃、分量十足、四四方方,从不拐弯抹角,没有半点无聊的曲线或是怪异的阴柔。更不用提它的钢铁支架带来的纯粹暴力了一种无情的力量击打在纸张上。无情。是的。宽恕从不是打字机的天职。
我想我自己对“宽恕”一词也所知无多,因为我的工作恰好和它的反面密不可分那就是“招供”。我并不负责逼供,那是警司的活儿,或是警督也可以干,但并不是我的职责。我的工作静默无声,除非你把用打字机转录速记纸上的文字时发出的噼啪声算在内。但即使如此,我也不是这噼啪声的始作俑者。归根结底,我只是一个女人,只有在离开侦讯室的时候才会被警司注意到,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会轻柔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庄严的声调对我说:“不好意思,罗丝,像你这样的淑女竟然要听到这样的事情。”他指的是强奸案、抢劫案……这些我们刚刚耳闻的疑犯招供。我们警局位于纽约曼哈顿下东区,辖区里像这样的案件可谓屡见不鲜。
我明白,警司对我说话时用上“淑女”这个词纯属客气。眼下正是1924年未完而1925年将至的时候,我的身份按时下的标准可能介于“淑女”与“女人”之间。这两者间的区别一部分源自受教育程度作为阿斯托利亚速记员女子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我或许可以忝列于“淑女”之中。但说到成长背景和生活条件,我只不过是一个每周入账15美元的孤儿,并不能自称“淑女”。而且受制于雇佣关系也是阻碍我成为“淑女”的一个因素。按照传统,“淑女”可以干点儿什么消遣,但并不受雇于谁。然而我为了上有片瓦下有三餐的生活折腰,只能称得上是一个“女人”,而非一名“淑女”。
当人们说起“打字机会让我们变得雌雄莫辨”时,他们很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这份打字员的工作会让女人离开自己的家庭,并非踏入制衣厂或是洗衣房,而是走进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这些之前见不到女人踪迹的地方。我们扔下围裙,穿上浆洗笔挺的衬衫和乏味单调的深蓝色裙子,变得不再那么有女人味儿了。他们害怕一旦我们长久地被速记机、油印机、加算器和气动邮件管这些技术性设备所包围,我们柔情似水的女人心就会不自觉地模仿着这些钢铁黄铜,变得刚硬顽固起来。
在我看来,掌握了打字这门技巧,的确能让女性步入那些原本男性化的工作场所,比如警察局。在这儿,打字员组成了女性少数派。事实上,也许有人听过或是的确见过曼哈顿的女警卫雇用这些奶奶级的老古董是为了解放男性警卫,使他们不必天天将多如羊群的妓女驱入警局,免得他们面临“举止不当”的虚假指控。但是我们警局的警司对使用女警卫并不赞成,也从不雇用她们。要不是警局打字工作太多他们实在忙不过来,可能压根儿连一个女人也不会雇用。实际上,打字机是我进入女性禁区的通行证。
打字并不是野兽般男性化的工作,请注意。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认为打字员的工作简简单单的听写艺术,指尖翻飞着在速记机键盘上敲出精巧断奏也许是我们现代社会所能提供的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工作之一。至于其他的?人们大可不必担心。一名好的打字员很清楚自己的位置: 作为一个女人,能拥有一份收入合理的工作,她已经很知足了。
无论怎样,如果打字真的是一份男子气概十足的工作,那你就会看见更多的男打字员,但事实上并没有多少。女打字员倒是随处可见,因此这份工作想必更为适合女性。到目前为止,我只见过一次男打字员,外形纤弱,看起来比我还不适合在警局工作。我第一眼看到他,就觉得他这份工作干不长。他有小鸟儿一般的体态,胡须整洁得似乎每天都有理发师修剪,还穿着打理得当的白色鞋罩他来上班的第二天,就有一个犯人往上面啐了一大口烟痰。我很遗憾地向大家宣布,这名男打字员当时就变得小脸儿煞白,起身去了盥洗室。在这次事故之后,他只多撑了一个礼拜。“白鞋罩……”警司边摇头边咂了咂嘴这通常是他对我信任的体现。“这儿就容不下什么白鞋罩。”他说。我明白,送走了这么一位“时尚先生”,他也许很高兴。
当然,我并没有提醒警司,咱们的警督也穿着白鞋罩。警督和警司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但似乎很久以前就结成了某种不稳定的同盟。我一向清楚不应该表露出对他们中间任何一位的好恶之情,以免打破他们共事时微妙的平衡。但如果我实话实说,我会告诉你,跟警司在一起我觉得舒服得多。警司要年长一些,而且对我的喜爱似乎略微超过了一名已婚男子应有的程度。不过我觉得这是一种父亲般的喜爱,而且他之所以成为一名警司,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充满了正义感的男人,并且打心眼里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维护我们这个伟大城市的良好治安。
此外,警司很喜欢把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以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为傲。上个月他刚扣了一个警员一周的薪水,就是因为这个警员给拘留所里的一个流浪儿塞了块火腿三明治。我想我明白为什么那个警员要这么做: 那个流浪儿实在太可怜了。他瘦得肋骨根根毕现,透过薄薄的衬衫看得清清楚楚,一双眼睛像闹鬼的弹珠,在深陷的眼窝里骨碌乱转。没有人当面指责警司铁石心肠,但是我相信他明白有些人心里是这么暗自嘀咕的。“给这样的人饭吃只会让别人觉得辛勤劳动、遵纪守法也没什么好处!我们可不能纵容这样的堕落念头!”警司提醒我们。
警司的职位不及警督高,但是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个子不高,却很有分量,极富威慑力。他的大部分重量都集中在腰部,堆成一个老爸式的将军肚,稳坐在制服长裤腰带上方,让人看着觉得很踏实。他的八字胡近年来染上了些岁月的灰白,被他打理成弯弯的形状。他还留着长长的连鬓胡子这式样有些过时,但他却毫不在意,一点儿也不想追求那些惊世骇俗的新造型。有一次我还听见他在读报的时候加以评论,说当代风尚简直是民族倒退的证明。
与之相反,警督一根胡须也不留,总是刮得干干净净,正符合当下的时尚潮流。他用发膏随意梳起的大背头也正是眼下流行的,而且似乎总有一两绺儿垂落下来,在一只眼睛前面颤啊颤的,惹得他不时伸出手来往后梳。他的前额上面有一道醒目的疤痕,从眉毛中间延伸到一只眼睛边上奇怪的是,这让他的五官反倒更有魅力了。他很年轻,可能只比我大一两岁,而且因为是警探,不是巡警,所以不用穿制服。他的穿着入时,但是气质奇特,总像是刚从床上滑下来,恰好跌进了这堆衣服里。他总是一副漫不经心的快活模样,就连鞋罩也从不曾像那个男打字员一般雪白干净。这并不是说警督不注意个人卫生,而只是说他的仪表不够齐整。
事实上,尽管警督看起来总是一副邋遢的样子,我却确信他有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他时常斜靠在桌边跟我讲话,我注意到他身上总散发出梨牌香皂的味道。有次我问他:“这个牌子的香皂难道不是女人用的吗?”他立刻双颊绯红,面露不悦,虽然我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之后大约有两个礼拜都故意躲着我。而在此之后,他身上再也闻不到梨牌香皂的味儿了。有天他又冲我的桌子俯过身来,没和我说话,只是默不作声地取走了一份打印稿。我却留意到他身上的香皂味儿变了,闻起来像是昂贵的雪茄与陈年皮革的混合物。
我不大乐意跟警督共事,而更喜欢和警司一起工作,其中一个原因是警督审讯的多数是命案。也就是说,一旦我跟他进了侦讯室,很有可能需要速记下来的就是一名凶杀疑犯的口供。警督对我的命令里听不出丝毫歉意,而警司的就有。事实上,有时我甚至能从警督的话音里听出一点挑衅的意味。而表面上看来,他自然总是爽快干练,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弱势性别,但我想,男人们都没有注意到,事实上我们女人需要面对同一份口供两次。头一次是用速记机听写下来,第二次则必须用打字机再次转换成正规的英文,因为警局里的男人们可看不懂速记符号。对他们而言,速记稿上的符号简直堪比象形文字。尽管我似乎应该心怀不满,但实际上我并不介意把这些口供打了又打,除了午餐或晚餐前回溯刀刺棍击的细节有些小小地倒胃口。你知道,问题在于,一旦这些嫌犯放弃了自我辩解,决心一股脑儿认罪,通常都会将犯罪带来的混乱后果描绘得淋漓尽致。作为一个具有道德感的人,我对这些可怕的细节自然谈不上欣赏。然而我更讨厌警督看出我的不适,并将其作为我脆弱的女性承受力的佐证。我向你保证,我的承受力在这方面可一点儿也不脆弱。
当然,我必须承认,和别人一起听这些口供会带来某种不那么直接的亲密感,但我绝不认为和警督共度这些时光是一种享受。他审讯的嫌犯通常对女人犯下了命案,而且在结束受害者性命之前还做了些其他的恶事。当我记录下对年轻女子施以暴行的疑犯口供时,屋子里的空气简直令人窒息。有时,我能觉察到,在罪犯陈述最为残暴的罪行部分时,警督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我。每到这种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像个科学实验品,或是时下大热的心理学研究实验品。我就那么坐着,打字,尽力无视他。
然而,和出于体谅替我担心的警司不同,警督似乎并不特别在意我听到的口供是否会亵渎我那颗理论上冰清玉洁的女人心。老实讲,我着实不明白他想从我脸上看出些什么。他很有可能在猜想我会不会突然昏过去,脸朝下瘫在速记机上。谁知道他说不定为此跟其他警员打了赌。但是我们已经进入了摩登时代,女人大有可为,无须时时费心履行昏倒的义务。我希望一身时尚气质的警督也不要再像只好奇的小狗偷瞟我的脸了,让我安安心心地好好工作吧。顺便提一句,我的活儿还是干得很好的: 用普通打字机每分钟能打一百六十字,要是用速记机,每分钟能打将近三百字。而且我对绝大部分听到并且转录的口供都保持着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就像一台打字机,我的工作就是精确地报告,制作官方、公正的报告,并最终用于法庭。我打出来的字,就是事实本身。
当然,我有时也得注意一些,不能被我的骄傲情绪冲昏头脑。有一次,我和警督一块儿从侦讯室里走出来的时候,我用比自己预期的大了那么一点点的声音对他说:“你知道,我可不是个傻瓜。”
“你说什么?”他停下了脚步,猛地转过身来,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那种看着科学实验品的表情又浮现在他的脸上。他朝我走近了一两步,像是要跟我偷偷商量什么,一缕雪茄混合着皮革的肥皂香味钻入了我的鼻子。我挺直了身体,轻咳了一声,再次镇定地表明了我的立场。
“我说我不傻。这样的工作可吓不倒我。从来不会。我不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你不用担心要替我拿个嗅盐一种由碳酸铵和香料配制而成的药品,给人闻后有恢复或刺激作用,用来减轻昏迷或头痛。瓶子什么的!”我加上这最后一句,只是虚张声势,警局里可不会备着嗅盐,而且时下似乎也没人带着嗅盐瓶子到处走了。但是我马上又后悔了。这么说显得太戏剧化,就像我刚才提到的,“歇斯底里”。
“贝克小姐……”警督终于对我开了口,但却欲言又止。他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最后,像被什么人猛掐了一把,他脱口而出:“我确信你能眼都不眨一下地录下‘开膛手杰克指1888年8月7日到11月9日间于伦敦东区的白教堂一带以残忍手法连续杀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凶手代称。’的口供。”我还没来得及反击,警督就一转身,大踏步地离去了。
我不知道他这么说算不算恭维。但是和警局的这帮警察一起工作,我对讽刺倒是略知一二。要我说,警督说不定背后正对我大加嘲笑呢。其实我对“开膛手杰克”也并不熟悉,只风闻他刀子用得好得出奇。
这个话题就这么结束了。我也再没跟警督提起过。警局的日子还是在或多或少可以预见的和谐中一天天过着。警司跟警督保持着不稳定的协作关系。警督和我的关系也总是客客气气,却不咸不淡。
这样的太平日子,却在另一个打字员到来的时候终结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