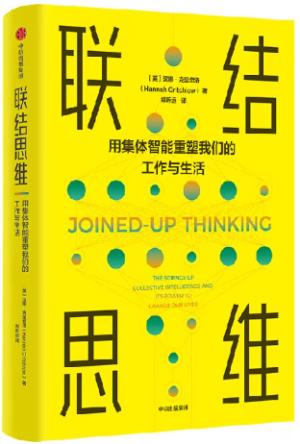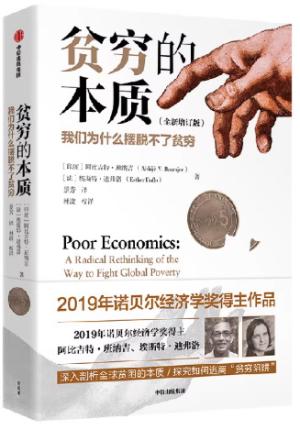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你永远有选择
》
售價:HK$
57.2

《
1848变革之年(理想,是“民族之春”,现实,是“血色夏日”,革命风暴席卷欧洲,旧时代的丧钟为新秩序
》
售價:HK$
85.8

《
拓客销售:可持续的营收增长
》
售價:HK$
75.9

《
骨与肉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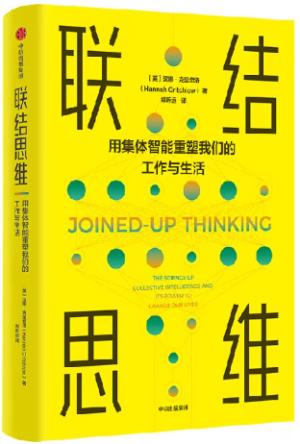
《
联结思维
》
售價:HK$
75.9

《
陶说 中国古代陶瓷经典
》
售價:HK$
12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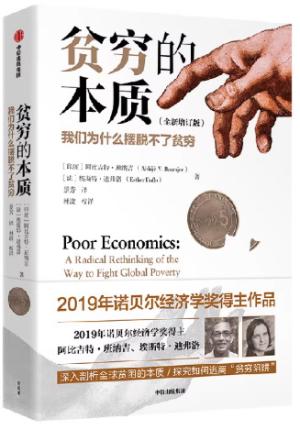
《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全新增订版)
》
售價:HK$
75.9

《
什么知识改变命运:知识类型及其获得与阶层流动机制的“中国经验”研究
》
售價:HK$
96.8
|
| 編輯推薦: |
迈克尔罗兰教授在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声名显著,他对西方人类学文明研究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并同中国学者一道在文明物质性等领域讨论互动,进行了一系列深入对话。
聚焦历史、物质性与遗产主题,契合我国当下已蔚然成风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推动对我国博物馆方向转型的理解。
扎实的人类学知识,丰富的援引资料,一窥英国人类学务实而又进取之风范。
|
| 內容簡介: |
|
本论文集共收录14篇讲演稿和1篇附录。讲演稿是罗兰教授于2006年至2014年间,在北京、成都、泉州、贵阳、大理等地参加会议、举办讲座、参与国家外国专家局项目的主要论文与讲稿的译稿;附录是对罗兰教授的学术专访。这些文章尽显罗兰教授多年来在长时段史的人类学、物质文化与博物馆研究等领域的研究心得。
|
| 關於作者: |
|
迈克尔罗兰,在1972年获得伦敦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后,至伦敦大学学院任人类学讲师,后于1992年成为物质文化研究教授,曾担任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主任。罗兰教授的研究突破了民族、国家与区域的视野局限,并注重对各种文明体系的比较研究工作。作为一位卓有建树的人类学家,罗兰教授的学术成果丰富,著有《考古学中的社会转型》《物质文化研究手册》等。
|
| 目錄:
|
自序
编译者说明
上编 历史、文明与人类学
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再到民族学)
文明与非洲的一体性
长时段过去和断裂
超越封闭文化: 中国境外的文明、区域和长时段的延续与断裂
文明作为对照的宇宙秩序:西非与中国
作为宇宙统治之比照的文明
新石器化:从非洲到欧亚以及更远之处
下编 物质性、遗产与博物馆
器物之用:物质性的人类学探究
献祭行为:对世界之间性的物质化
遗产、记忆与后殖民时代的博物馆
对遗产与记忆的再思考
重新定义博物馆中的物品:中国遗产的井喷
中国的新博物馆时代到来了吗?
新型民族志博物馆:数字化遗产技术、社区参与及文化还原
附录 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迈克尔罗兰专访
|
| 內容試閱:
|
从民族学到物质文化(再到民族学)
导论
1923年,
英国社会人类学奠基人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撰写了一篇在当时被认为划时代的文章,他认为,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区别,类似历史与科学的区别。德英美三国的民族学,以历史化(historicizing)或意象化(ideographic)的方式研究文化多样性。新的社会人类学,则是一门对社会体系进行共时性、比较性、一般性研究的自然科学。
众所周知,涂尔干的社会学让社会人类学家脱离进化论和传播论的人类文化起源说,并拒绝原始遗存说和历史猜测。与任何奠基故事相仿,今天的人可能觉得那场分裂很严重。可是,研究野蛮他者的民族学,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迅速消失尤其在东欧。民族学尽管不符合人类学的社会学化进程,但它在某些方面仍继续发展。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德国的某些院系,民族学仍是一门研究民俗和农民遗存的学科。即使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它也并未中断,且延续至今,研究日常生活、国民身份、民俗(Volkskunde),并转向流行文化a 研究。在美国,博厄斯派的人类学,从传播论、历史具体主义转向了文化的心理学综合。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实证主义的支持下,美国人类学经弗里德(Morton Fried)、斯图瓦德(Julian Steward)和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之手,演变为独领风骚的新进化论。
但是在战后欧洲,人类学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向,非历史化和民族志化消解了多数方法,民族学就是其中之一,以至于今天很多人类学家听说民族学还是一个独立学科,都会感到意外。今天的民族学,恰恰是拉德克利夫-布朗这样的人类学家眼中的民族学。它通过博物馆和人造物的收集,而不是民族志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多样性。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曾令人信服地指出,社会人类学的兴起使物的研究衰落,其结果就是,物不得不被放在社会语境中理解。她强调说,新几内亚高原的哈根人,是用人造物创造语境的,人的存在并非理解意义的前提条件。同理,原始艺术的研究之所以在20 世纪60 年代变成了艺术人类学,就是为了突出田野工作的重要性,为了突出在社会与文化语境中观察物品的重要性,而将处理博物馆藏品的技能与理解藏品的技能分开。宾尼(Christopher Pinney)曾提出所谓的金斯博格问题(Ginzburg
problem)在视觉分析中,历史学家解读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的意象。
民族学研究作为民族一体性资源之一的民间文化,并因此在欧洲某些地方得以保留,这背后显然存在有趣的历史。研究民众生活的学者,受命收集和保存那些日常的、被忽视的物品,如烤铲、锄头、挤奶凳。从农业工具、农场建筑,到家庭陈设,他们不知疲倦地为一切物件创造科学术语。他们相信,抢救正在消失的农民文化的任务十分紧迫:在废弃的谷仓崩塌之前,要抓紧测量;在最后一块公用地被圈占之前,要抓紧研究村落;在阁楼和棚屋的物品被遗忘之前,要赶紧收藏。他们插手每一个领域,尤其是与农民社会有关的物质文化。对于旧的人文学科如艺术、历史、文学的同行来说,这种雄心很容易被视为可笑的或微不足道的。但是,对于印度部落人群和中国、前苏联少数民族研究来说,则未必如此。民族学对于19世纪印度种姓的种族化,或前苏联的民族发生学(ethnogenesis)一直有贡献。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社会人类学的核心地带,民族学已经被分解成一个个最小单位,要么被社会学化,要么被排挤到博物馆研究领域。在博物馆研究中,1870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第一个博物馆时代)收集的大量民族志物质文化藏品,已经丧失了传播论或进化论的框架,物质文化和技术的研究于是发生了一场描述转向。所以,物质文化和历时性研究淡出人类学,并不一定是民族学受到了整体的学术批评,而是因为民族学作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消失了。
物质性怎么了?
在下面的讲座中,我将回归并重建民族学对大规模时空转型和长时段历史变迁的兴趣。但是,我的讨论将以物质文化为题。物质文化是民族学事业的另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是对人造物的表象特征进行博物馆收藏、分类和研究的工作。
众所周知,虽然对博物馆藏品的类型学研究与新兴的社会人类学互不相干,但社会人类学并未完全忽视技术和物质文化,前提是要用田野工作的三棱镜改造一番,使技术和物质获得语境,如拉德克利夫-布朗对安达曼岛人的观察,或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对珊瑚园圃及其魔法的观察。但这意味着,要理解物品世界的物质性,就必须知道它们的社会语境,即人如何言说物品。因此,像哈登(Alfred Haddon)等人关于太平洋地区的鱼钩
或者旋架独木舟的研究,只好躺在图书馆里无人问津。民族学成果(传播论者眼中的人造物的时空形态变异)无非是臆测历史,对于理解社会如何整合这样的功能主义问题没有贡献。
当前物质文化研究在人类学和更大范围的复兴,并没有承诺要重新研究宏大的时空变异。例如,米勒(Daniel Miller)在一本研究物质性的专著的导论中,这样定位物质文化研究的主旨:理解物的世界如何制造人,以及人制作了什么a。他将物品化(objectification)的研究与布迪厄的著作联系起来,批评社会人类学将物质世界简化为社会的解释。他强调,社会区隔(socialdistinction)实际是对物质做选择的后果。他对消费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遵循这一观点,且不无偏见地反对理性行动者的算计说(拉图尔〔BrunoLatour〕,卡龙〔Michel Callon〕等)。他着力理解物质世界如何通过从无到有,实现某些特定的理想。许多物质文化研究关心群体如何理解自身并通过盗用汽车、时装、家具等货物成为自身。该观点认为:如果货物不存在,身份就不能实现年轻并非拥有时装、音乐或生活方式的先决条件,而是它们的后果。而且,人也可以失去物质性贫困,即失去自我,恰好是这样的例子。拉图尔提出偶像冲突(iconoclash)的概念,形容一种混杂的反应:既沉溺于意象,又渴望破坏意象。实际上,米勒的观点并不完善,因为在逻辑上,他从物质性移向文化性,但文化性却由人化的语境来定义,即穿一件印度纱丽或买一杯特立尼达饮品之所以使身份成为现实,取决于附着在物上的、布迪厄式的传递和惯习。拉图尔的出发点较为偏激:因为没有自然,所以就不可能有文化,只有混杂或自然加文化nature-cultures,人和非人纠合在一起。因此,大气中的臭氧空洞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文化的,而是两者纠合的产物。提姆英格尔德(Tim Ingold)批评米勒没有注意到物品在技术上的物质性。米勒毕竟认为,物品的意义和形式要从人们对物品的态度理解,就是说,焦点仍在文化而不在物质性。提姆英格尔德在一篇《制造文化与编织世界》的文章中,宣称他对物质性的研究取得了突破。他将通常的秩序颠倒过来,将制作视为熟练操作的产物。一件物品成为现实,体现的是有节奏的制作过程,例如编一个篮子或者造一口锅。这个过程的特点,在于将想法变成现实,并将之带入惯习或日常行动之中。我猜,我们更接近哈登和他的鱼钩了。当然,严肃地研究物品,让我们可以重新利用博物馆藏品,让藏品虚拟地回归田野工作的语境,并推进人造物的物质性研究,而不再仅仅做文本或口述形式的视觉验证。吉尔(Alfred Gell)将人类学的艺术争论从文化决定论的边缘拯救回来。他以20世纪80年代在纽约展出的赞德人(Zande)猎网所引起的争议为例,将艺术理解为思想的对象。猎网用打结的绳子编成,绳结和绳索承载了复杂的观念。此处的观念,类似邓肯IsadoraDuncan 的说法:如果我能告诉你它是什么意思,我就不会把它跳成舞了。库奇勒(Susanne Kuechler)说,绳结不仅激发了一系列个人思想和情绪,还构成了太平洋作为文化区的特征。她研究了绳结的类型与结绳的本体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理解南太平洋的身体政治及其各种表述。她研究太平洋地区的物品,一种是用辫形绳索捆扎的物品,另一种是用特殊的打结方式捆扎的物品。结果发现,捆扎动作与酋长继承有关。她认为捆扎的物质性与知识的技术有关。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技术的转型。新爱尔兰的马朗根雕塑(Malanggan sculpture)木框上的绳结或者夏威夷斗篷和物品上的过度捆扎,与当年哈登笔下的鱼钩有直接的关系在太平洋地区,人们极为重视鱼钩系在鱼线上的方式,它大大超出了捕鱼本身的需要。
过去的文化区观念和当下的商品观念,在这里形成一个矛盾。前者认为,世界可以根据某种延续性和实质性特征分成区域,无需顾及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后者认为,商品从一个文化进入另一个文化,会越来越失去其物质性。就这个问题,宾尼提出,可以存在不同的汽车文化。这里又是一个循环论证:汽车文化仅仅是不同文化中的汽车文化。
物品看似叙述的焦点,仅仅成为搭建不同文化(乃至于人)的方式。作为物的社会生活的叙事,物品再次肯定了它们穿梭于其中的人的能动性。
后来,他遵循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观察,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悖论,物品越是客观,主体就越主观地凸显出来,我们所讲的有关世界的知识就越发变成关于人的主张,越变成人类学。物品作为非人领域的诞生,与人类作为人的诞生是同步的。
仅仅强调客体(物品)凌驾于主体,换言之,修正涂尔干式社会学对人类学的影响,只能继续陷入主体-客体的悖论,继续让物品和意象附属于我们已经熟识的文化和历史,我们希望摆脱这个悖论。
我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混杂的复合体中,追踪在实际上将物品和人联系起来的通道和网络。如果文化和物质性不能分开,人与物品是它们互动的产物,那么文化将物品人化的观念,或者物品和技术制作人的观念,都将消解到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即这些不同的潜力如何传递或如何继承。在后面两讲中,我将更细致地追究这些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