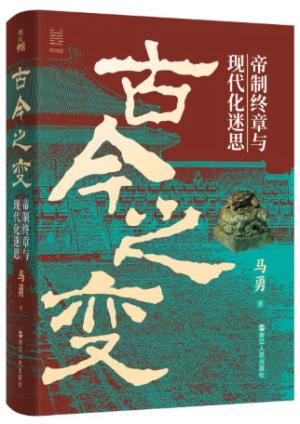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中老年人学AI: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精彩
》
售價:HK$
98.8

《
不想成为妈妈那样的母亲
》
售價:HK$
49.5

《
龙头股交易指南(上)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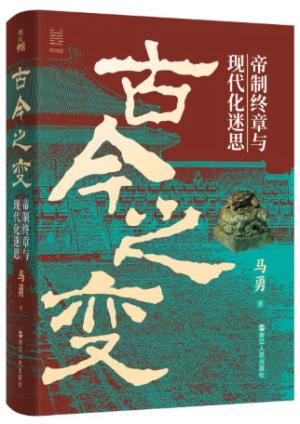
《
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
》
售價:HK$
107.8

《
存在的意义 11位心理治疗师的存在-人本之旅(孤独、意义、自由、敬畏、死亡交织在人生旅途中,推动我们
》
售價:HK$
93.5

《
达尔文的植物世界 跟随达尔文的试验与研究发现自然植物的奥秘 达尔文进化论植物篇
》
售價:HK$
165.0

《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引擎:中国创新的黄金时代2015-2025
》
售價:HK$
74.8

《
你永远有选择
》
售價:HK$
57.2
|
| 編輯推薦: |
作者赵絪幼年时随父母颠沛流离,后来又在时代的动荡中载沉载浮。她记录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山东大学校园里的恬静岁月,教授们的风趣盎然和学者风范跃然纸上;又记录了随后政治风暴中的艰难困苦,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们或达观或正直或隐忍或悲凉的图景。在平实又活泼的字里行间,往事如历历在目,令人不禁掩卷沉思。
《孤灯下的记忆》书中记载的教授们弦歌不辍,其门生也是名家辈出,如赵俪生关门弟子秦晖、王瑶弟子钱理群、张政烺弟子李零。而通过作者的文字,我们有幸一窥那一代皇皇大家,仿佛他们音容尚在。
|
| 內容簡介: |
《孤灯下的记忆》作者赵絪,是讲中国通史可比肩钱穆的历史学家赵俪生的女儿,她在书中鲜活地记录了一批父辈学者的独特风采和多舛命运。例如赵俪生与王瑶一生既是对手又是老友,不断较劲又彼此珍惜;赵俪生与其天才般的挚友童书业,两人之间一场无言的泣别竟成永诀;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明镇夫妇,一个天真无邪,一个优雅端庄;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女士朴实大方,举止得体,影响她的后人亦是谦和朴素,平易亲切。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者还记录了自己家庭中几经磨难,但每个成员皆能坦然应对的往事;记录了一批知识青年的群像。她的书写,为一个时代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标本;她的文字朴实、从容,却又让人意犹未尽。
|
| 關於作者: |
|
赵絪,1946年生于陕西蔡家坡,成长并定居于甘肃兰州。其父是著名历史学家赵俪生。文字曾发表在多家报刊上,受到广泛关注;同时是一名书画家。
|
| 目錄:
|
代 序 01
第一辑 思亲
告别209室
写在父亲赵俪生先生的祭日里 003
在苦难中磨砺 009
我与我的父母 029
我的母亲高昭一 076
扉页上留下的痕迹 092
被遗漏了的一段师承 101
迟交的作业 104
忆亡人 109
寻踪祖父母 121
二大爷 128
第二辑 忆旧
王瑶与父亲 147
孔祥瑛女士和她的后代 159
平凡中见精彩
大羽老伯印象 165
幼年印象中的童书业先生 169
张政烺先生二三事 175
一位不该忘记的长者
记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 180
一件拓片的来历 192
偶逢遇罗克
一个已经模糊了的印象 198
为张珏女士送行 202
刘 宝 206
记砾石居主人 218
笑对人生
朱开发去世三周年祭 226
运尸记 241
第三辑 谈艺
何鄂印象 249
序,就得这样写 258
指墨间的情趣
小议张兴武先生指画 261
我与《老照片》 266
贺《开卷》 269
书 信
有感于即将消失的一种文体 271
婚姻手记(小说) 276
后 记 338
|
| 內容試閱:
|
代 序
文乔幼梅
《孤灯下的记忆》作者赵絪女士是已故著名史学家赵俪生先生之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赵先生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执教时我有幸承沐教泽,故我与作者一直以师姐妹相称,彼此比较熟悉。师妹以自己和父母的亲身经历为素材,记述了两代知识分子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半个多世纪所经历的反右、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冲击、涤荡和社会地位的升降沉浮。由于是同时代人,又有相似的经历,读来尤感亲切。
当年沦为狗崽的师妹只读到初中毕业便辍学在家,不久又赶上了上山下乡运动,被迫去了甘肃河西农场劳动,到恢复高考时,她已结婚生子、人到中年,无法圆自己的大学梦了。而她的四个兄弟姐妹则先后得到了深造,所以师妹经常自嘲是扫盲班出身。先师心疼此女未能得到正规教育,又感其有一定的文学、绘画天赋,于是便为师妹开了小灶,亲自指点她读一些传统典籍和国画技艺,在先师的耳提面命下,师妹不仅得以浏览中外名著,而且笔耕不辍,每有习作画稿即呈交老父批改。先师是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学者,在山东大学和兰州大学均是最受学生拥戴的优秀教师,曾培养出多位高水平的学者。师妹得到乃父的亲自调教,安能不成俊才?尤其在甘肃水利水电学校退休之后回到了父母身边,终日陪伴、侍奉已届耄耋之年的二位老人达十几年之久。父女二人一位传授,一位聆听,亲切互动。他们两代读同样的书,交流不同的见解,既排遣了先师垂暮之年的寂寥,也为师妹退休后的生涯奠定了基础,本世纪初先师和师母先后去世,师妹独守孤灯,往事历历,难舍亲情,遂寄情翰墨,集成此书。
师妹以饱满的热情颂扬了先师及其同窗好友如文学家王瑶先生、孔祥瑛女士,史学家张政烺先生、童书业先生,文物考古学家王献唐先生以及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等前辈学者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诚友谊,崇尚自由、不敷衍、不苟且、刚毅守正的高尚品格,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在被打成右派或遭受不公正对待后,他们尽管无处辩白,生活窘迫,心境悲凉,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桎梏,却依然不灰心,不绝望,锲而不舍地著书立说、培养学生,执着顽强地继绝学、铸新知,传承、弘扬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他们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师妹以独特的视角记述了河西农场劳动者们的美丽心灵。在那饥饿的年代,他们每天高强度劳动十几个小时,粮食定量不够吃,几乎每个知青都被逼当过小偷,即使这样,有的农场工人和知青还将自己的饭票送给更加困难的同伴。一位年龄最小的知青经常把从农场地窖里偷来的洋芋送给拖儿带女的贫困户,把烤熟的洋芋留给年长的知青好友。如此宽厚仁爱、克己助人的美德在那饥饿的年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师妹还记述了几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奇特的婚史:他们有的有成就,有的平庸,婚姻上都遭遇坎坷。其中一位四次结婚,四次被迫离婚,还因此坐了十几年的大牢,最终妻离子散,孑然一身。而造成这场人生悲剧的根源正是当时盛行的政治干预婚姻,剥夺人权、戕害人性的极左思潮。
师妹叙人叙事清新简洁,文风朴实犀利,诙谐老辣。她不发空论,不打禅语,更不堆砌流行金句,很接地气。在她笔下,不论是生气勃勃的知青还是满腹经纶的学者,个个活灵活现,跃然纸上。这样一部有思想深度的高品位优秀作品,的确令人掩卷难忘。
王瑶与父亲
王瑶伯伯是父亲清华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两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了密切的关注。这说明透着骨子的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如今父亲也故去了,我回忆起和王伯伯有限的几次见面,还有父亲生前对王瑶伯伯的描述,以及社会上总是把他们拴在一起来评议,使我对这两位老同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发现他们尽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不论在性格、作为、思辨、语言表达方面都有很多相近之处,我愿意把对他们的一点感性认识记录下来,这样也能从侧面提供一些对两位学人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谢泳先生曾撰文把周一良、王瑶、赵俪生三人归入一个类别来评点,并将这三个人和在美国成为世界级大家的杨联陞、何炳棣相比较。作为旁观者,客观地说,这两组学者没有什么可比性,更何况前三者也绝不属于同一类型的学者呢!倒是王瑶和父亲,不管他两人怎样地相互攻讦,他们的风格、思维方式却比较类同,而且他们把他们思辨的方法、看问题的视角顽强地传承了下去,以至于他们的后学源源不断、精英辈出,这也说明这两个并非一流的学人,却带出了许多一流的学生。
周一良与王瑶和父亲是不属于一个类型的学者,周伯伯是世家子弟,受了系统的、完整的东西方教育,一直非常体面,循规蹈矩地做人、做学问,为人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不张扬,不激愤,一派大家风范,是传统学人的楷模。这种温良的个性,在巨大反常的压力下,和众人一样,只能屈从。所以他晚年写的《毕竟是书生》,道出他这一辈子的委屈和无奈,其公子也在多篇文章中为其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进行疏解和辩诬。这让我们深深理解和同情,有如此身世、如此学问,守身如玉的学者却遭此百口莫辩的尴尬局面。我家这一代和周家后人也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
而王瑶和父亲在学人群中属于另类。两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表现也绝对地张扬、绝对地尖刻、绝对地调皮。他们总是看到人家不愿让看到的那一面,非要提人家捂住不让提的东西。这是一对绝不讨人喜的学人,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不用其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高潮时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多少有点二杆子,使他就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二十余年。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演出了这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三个女儿,以大姐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我们不走时,他也就不以为然地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而未加制止,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背负了一生对王瑶伯伯的歉意。
我们渐渐长大,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饱读各类文学著作的同时,也去读读王伯伯有关文学史的理论文章,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加之又是父亲少小同窗好友,我们和王伯伯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兰州大学来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的言语致歉的含义,同时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曹禺戏剧的大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是高兴。大家团聚一起,热烈讨论,叙旧事、谈学问,也谈时下局势,真是神采飞扬、妙语连连、其乐融融。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当年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没有发生相互攻击的一幕。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这句话,就是那次聚会时,扔俏皮话时扔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了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遇,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遇,当然两位老同学之间的物质生活可以说有天壤之别。这也是王瑶伯伯一摆谱,父亲就跳高的一个缘故。王伯伯家殷实、富裕,一九六六年家中已有电视机,这只有在相当层次的人家才能见到,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王伯伯喜骑单车,三个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辆,这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亲好得多。我和周家公子、王家姐妹同游了颐和园、碧云寺,照片至今夹在父亲的影集中,当时王伯伯从四清点上打来电话,让伯母盛情款待。在王宅的那一餐饭吃得两家工资待遇差不多的周公子多年后提起,也觉得对接待我们这样的晚辈来讲,有点奢侈了。为此周公子还和他父亲探讨:你们都差不多,人家咋那有钱?这一问还引来周伯伯一顿科学家不如文人的感慨。没几天,文革即起,我匆忙返回兰州,哪知这一别竟是二十几年呢?
再次进京已是一九九三年了,二十七年历经了太多的沧桑,北大镜春园的旧居中,只有杜琇伯母一人留守,我们的王伯伯走了已近五个年头。伯母待我犹如家人,在共叙往事之时,我为父亲对王伯伯失礼之处向伯母致以歉意,伯母制止了我:你不要再说了,在你父亲和王伯伯之间的事上,不光是你父亲做得不对。也就是说,王伯伯在处理老同学关系上也多有不合适的地方。这让我看到,极难驾驭、很不好侍候的两位学人,之所以还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庭,与两位含辛茹苦、百般宽容的女性有着极大的关系。王伯伯去世后,父亲应邀写了《宛在的音容》,母亲亲自把场、定调子:不准写一个字的不是!理由就是人都去了,不要再刻薄了。而在家中表现得更加专制的王伯伯,这一辈子也是给王伯母带来了不少烦恼和哀怨。王伯伯去世后,父亲调来了灵堂送别的录像,当看到王伯母扑向灵前跪送的场面,老泪纵横,冲着母亲说:看见了没有?将来我走的时节,你也得这样送!结果招来众儿女一致声讨:得了吧,将来你得像这个样地送俺妈,俺妈是你老大姐。王伯母是王伯伯的学生,她这是在执弟子仪!可见这两位不省心的学人,硬是让两个厚德、守信、有毅力、有耐心的女性给陪下来了,所以说,他们的学术成就中凝聚着两个默默无闻的女性的宽容与照料,否则他们的后果绝不比储安平好多少。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就没消停过。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但在嘴上从来不认账、不服输。父亲在《宛在的音容》中生动地形容了大学时代的王瑶伯伯,并写道:当他露出快要发脾气的时候,同时却又流露出一股孩童般的真纯。这个境界很美丽、很高乘。有时我会想,父亲是不是想刺激出他那美丽、高乘的境界,故意挑衅呢?这当然是我一个做晚辈的善良企盼罢了。父亲在文章中也表示:假如我是个女同学,我一定爱上这个人。父亲看人的眼力很准,他能这样说,那我们的王伯伯一定是个魅力十足的男子汉了。王伯伯虽也不断给父亲闹难堪,但在母亲和我们面前却不讲父亲的不好,总是提当年清华园里的赵甡是如何地漂亮、怎样地聪明,王瑶伯伯的常用笔名为昭琛,明眼人一看就知这是当年赵甡名字的谐音,这说明他也是欣赏、喜欢父亲的。可就是不能见面,因为只要碰到一起,就是一个不服一个。比如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居然大学肄业三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定为三级教授。本来就不舒服了,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了的师兄,摆出了一副 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哥们儿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可是山大的三级。就是到老,暗中较劲也没减势,王伯母毕恭毕敬寄上《王瑶文集》七大本,父亲放置案头,对母亲讲:将来我的文集出来,绝不比王瑶兄差!《赵俪生文集》刊印出来后,父亲击案长叹:可惜王瑶老哥看不到了!
就是这样一对不是冤家不聚头的老同学,他们一同听课,一同吃饭,一同买书,一同游行,相互批驳又相互感染。王瑶伯伯是有政治抱负的,因投身革命遇阻而求其次。父亲是关注政治的,因崇尚自由而远离政治。抗战时,两人在乾县窑洞分析形势,相约都入儒林传,果然两人沿着不同的途径走上了治学、育人的道路。后来王瑶伯伯成为北大校园学院派气息浓厚的大教授,而父亲成为边远地区屡遭厄运,被学界放逐边缘的一朵寒葩。他们都努力了,都在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的境况下,苦苦经营着自己的那点玩意,虽未成世界级大家,也确属锲而不舍。都执着、勤奋地做了一辈子学问,留下了让后人众说纷纭的话题。
正因为关心政治,注重民生,这两位学人在解放后选就的研究项目都是非常时尚、贴近政治和颇具开拓性的。王伯伯选了现代文学史的课题,而父亲则选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让别人会有一种赶时髦的看法。如果他们唯唯听命,按上边的调子来调整自己的学术路子,他们会是很能出风头的人物,可这两个自视很高,很有头脑,同时也很自信的学人,偏要独立思考,于是这一对有着敏锐气质的老同学就不断地试探禁区,虽不敢明目张胆,却也在允许的范围里顽强地表达了在这两个敏感领域中,他们独到的研究心得。这一点点可怜的自己的东西或许为今日之学人所不屑、所指责,可谁能想象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精神压力和物质贫乏的状态下写就的?父亲没有奢望文章生前就能见天日,每篇文章后均署名篱槿堂遗稿,如此寂寥无望的前景、悲凉的心境,还在苦苦坚守自己的一点信念,这是那些世界一流学者们所曾经历和承受过的么?
每个时代的学人都留下了他们辛勤的劳作,也留下了那个时代他们自己的风骨和人格,当然也留下了他们深深的反思和无限的遗憾。他们超脱不了现实给他们划定的范围,他们从童年就打下了坚实的传统文化的基础,到少年时受五四新文化的感召步入新文艺领域,青年时代在民族危亡的关口,放弃学业,投笔从戎。解放后,为信念与追求满腔热情扎入科研、教学领域,又历经反右文革这样举世震惊的大运动,而他们往往又被推上祭坛,成为接受打击的对象。可以说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他们一一阅尽,饱尝了那个时代所有的苦难,可他们依然没有灰心,没有绝望,锲而不舍地用最原始的方法默默地耕耘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有些后学们抛开这恶劣的客观条件,还在振振有词地品头论足,这里没有做对,那里没有搞好,没有达到他们原本应该达到的水准。试问:把你换成他们,你能保证做得像你说的那样完美吗?
诚然,王瑶和父亲绝非完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代学人、一位教师而已,但他们尽了一代学人的责任,他们把他们的思辨能力、认识方法顽强地传承下去,启迪他们的后学沿着这种思维方式更深一步探究他们未能完成、来不及涉猎的学术领地,在教学这个舞台上,这对师兄弟也堪称各领风骚数十年了。
就教学而言,在数量上父亲比王瑶差了许多。因王伯伯从解放到文革前后均没有被剥夺上课的权利,可以说一辈子都站在讲坛上,可谓桃李满天下了。父亲的教学生涯则始终随着政治时局的时紧时松而时断时续。但两人留给学生们的印象都是恢宏大气、不死板、不教条、非常地生动。就这样,老同学在教学的这一块领地上,也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
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乡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多亏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纵观天下,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许多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撇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这种后学不断的王瑶现象不值得人们研究么?这就是王瑶先生的不朽业绩。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他的一副钢口。可内中所付出的劳动也只有家人知晓罢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真像铆足了劲唱了一出《挑滑车》,就这样豁出命地干,才赢得了众口一致美不胜收的嘉誉。从五十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八十年代关门弟子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们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们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而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只不过他们只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着逗着玩的色彩,骨子中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教书教得怎样,不然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有几分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甚至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是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王瑶伯伯走得突然,让人猝不及防,父亲走得平缓安详,是名副其实的寿终正寝。我相信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见了面,也还要比上一番、斗上一阵、损上几句,谁让他们是当年清华园中好斗的少小好友呢?
他们走了,但他们那诙谐、幽默、尖刻、一语中的的生动形象深深印在了曾一睹他们风采的人心中。王瑶为绚烂多彩、百花齐放的文学领域平添了几分理智和深邃,而父亲又为枯燥、陈旧、寂寥的史学园地带来了生动和活力。这是多么好的一对老同学,多精彩的两个学人。他们既不是钻进故纸堆的不问时事乡愿式的老学究,也不是浪荡社会、追逐虚名的肤浅过客,他们既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地做了一辈子的学问,教了一辈子的书,也痛痛快快地张扬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展示了一把自己的才华。应该是够本儿了,应该是去而无憾了。
随着王瑶、父亲这一代学人的离去,意味着那个时代、那种文风的渐渐消失,因为他们毕竟是手工操作的最后一代学人。在当下随着电脑的普及、信息量的加大,人们的视野被大大地拓宽了。时下的学人已不屑于进图书馆、钻故纸堆、爬格子式的劳作了,著作等身在时下学人群也不过小菜一碟了,那种坐拥书城、苦苦思索,一天伏案十数小时着力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已成为历史上一道宁静、寂寥、清雅的风景。父辈们曾品头论足地点评着各类历史人物,而今他们不可免地也成为历史,让下一辈的学人们去评来点去了。在清理他们的遗产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尽力了,甚至尽了一个超出常人所能达到的能量。所以,他们的那些坏脾气,人格上的某种变异和扭曲,甚至在人生途中有意或无意出现的偏颇和失误,这本是人生途中的正常现象,任何人都不可能活得那样尽善尽美,何况父亲又是这样一个性情中人。但他确实活得堂堂正正,无愧于人生,无愧于学界,无愧于那坎坷人生带给他的重重苦难。
父亲可以坦荡而去了,作为女儿,只能遥祝老爹一路走好!
二○○八年元月十六日
于父亲逝世七七后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