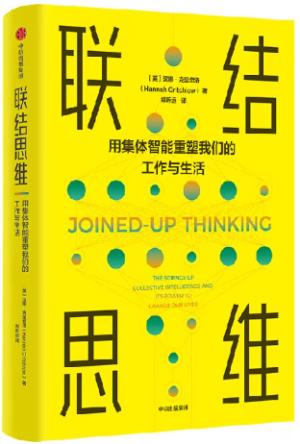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达尔文的植物世界 跟随达尔文的试验与研究发现自然植物的奥秘 达尔文进化论植物篇
》
售價:HK$
165.0

《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引擎:中国创新的黄金时代2015-2025
》
售價:HK$
74.8

《
你永远有选择
》
售價:HK$
57.2

《
1848变革之年(理想,是“民族之春”,现实,是“血色夏日”,革命风暴席卷欧洲,旧时代的丧钟为新秩序
》
售價:HK$
85.8

《
拓客销售:可持续的营收增长
》
售價:HK$
75.9

《
骨与肉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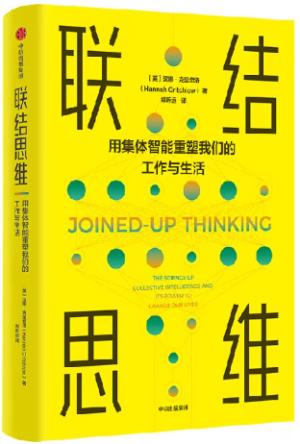
《
联结思维
》
售價:HK$
75.9

《
陶说 中国古代陶瓷经典
》
售價:HK$
129.8
|
| 編輯推薦: |
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尼刻奖、布克国际奖等多项大奖获得者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小说集直接译自波兰语原著
北京外国语大学专业波兰语翻译,保证译文准确性,贴切传达和呈现原作的语言风格和文字魅力;
完全根据原著编排,直观展现托卡尔丘克作品原貌。
三个富有超现实色彩的故事,为世界片隅中的冥想者观察家造物主量身打造:
《衣柜》旧衣柜里的异域能量场,吸引一对夫妇住进其中不愿出来。
《房号》突出展现托卡尔丘克第四人称叙事魅力,以客房服务员的视角捕捉客房中痕迹勾画的秘密。
《神降》带有卡夫卡小说韵味;程序密码构建的半边宇宙中,创世之神却常常陷入失望
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
特别收录:托卡尔丘克在她策划并组织举办的引号国际文学节上接受的专访
本次访谈的六个月后,瑞典学院宣布授予托卡尔丘克201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提炼日常中的诗意,书写日常经验之外的神秘世界
平平无奇的夫妇,默默无闻的客房服务员,酒店里的匆匆过客,深居简出的程序员将目光投入普通人的内心,以丰盈的想象力将离开的人带回现场;
打开神秘柜门,发掘平凡角落里
|
| 內容簡介: |
《衣柜》是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集,收录三部作品。其中,《衣柜》讲述一对夫妇被一只能量坑般神秘的旧衣柜吸引,最终住进里面不愿出来的故事;《房号》的叙述人是身为客房服务员的我,故事中,我游走于首都饭店的不同房间,循着蛛丝马迹捕捉客人留下的气息;《神降》则有关一位宛如创世之神的编程天才,他不断用程序构筑新世界,却又对人类屡屡失望在这些富有超现实色彩的故事里,托卡尔丘克以她独特的第四人称叙事,探寻着日常经验之外的隐秘世界。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本书直接译自波兰语原著,并特别收录托卡尔丘克在她策划并组织举办的引号国际文学节上接受的文学访谈。
|
| 關於作者: |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Olga Tokarczuk)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19年授予),当代欧洲重要作家、波兰国宝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为: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呈现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托卡尔丘克也是历史上第15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
托卡尔丘克生于1962 年,毕业于华沙大学心理学系,1989年凭借诗集《镜子里的城市》登上文坛。代表作有长篇小说《E.E.》(1995)、《太古和其他的时间》1996、《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1998)、《最后的故事》(2004)、《世界坟墓中的安娜尹》(2006)、《云游》(2007)、《犁过亡者的尸骨》(2009)、《雅各布之书》(2014);小说集《衣柜》(1997)、《鼓声齐鸣》(2001)、《怪诞故事集》(2018);散文《玩偶与珍珠》(2001)等。
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神话、宗教故事等元素来观照波兰的历史与人类生活。除诺贝尔文学奖外,她曾凭借《云游》和《雅各布之书》两次荣获波兰权威文学大奖尼刻奖,六次获得尼刻奖提名;2010年荣获波兰文化杰出贡献银质奖章;2015年荣获德国-波兰国际友谊桥奖;2018年《云游》荣获布克国际奖;2019年《雅各布之书》荣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奖,同年《犁过亡者的尸骨》入围布克国际奖短名单,该小说改编的电影《糜骨之壤》曾获201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亚佛雷德鲍尔奖。
|
| 目錄:
|
衣柜 001
房号 009
神降 053
附录 065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辞 067
温柔的讲述者
在瑞典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讲 071
一切都说明,文学将变得越来越小众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访谈 107
免费在线读衣柜(部分节选)
我们把家搬到这里的时候,买了一只颜色很深的旧衣柜,价格还没有把它从二手商店运回家的运费高。两扇柜门上有植物形状的装饰,第三扇柜门是玻璃的,我们开着租来的车把衣柜运回来的时候,玻璃上折射出整座城市。运输过程中需要用绳子绑住柜子,以防柜门在中途打开。我拿着一圈绳子站在衣柜旁边时,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荒唐。它会和我们的其他家具很搭。R先生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抚摸着这只木质衣柜,仿佛抚摸着一头刚被新农场买来的奶牛。
最初,我们决定把这只衣柜放在走廊上,用来隔开我们的卧室和其他空间。我将松节油注射到几乎看不见的孔中,它是可以帮助衣柜抵抗时间腐蚀的可靠疫苗。夜里,安放在新位置的衣柜嘎吱作响,垂死的木蛀虫发出悲痛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收拾新房子一处旧公寓。我在地板的缝隙中找到一把手柄上刻有纳粹标志的叉子,木壁板后面是一张旧报纸的残留部分,只能识别出上面的一个词: 无产者。为了挂窗帘,R先生把窗户开得很大,房间里充满了矿工管乐队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晚上。衣柜出现在我们梦中的第一晚,我们都没能睡很久,R先生的手不安地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梦。从此之后,我们经常做一样的梦,梦里一片寂静,万物都像商店展示柜上的装饰物一样悬挂着,我们在这片寂静中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早晨醒来时,我们不必向对方讲述梦的内容一个字就足够了。从这时起,我们不再告诉对方自己做了什么梦。有一天,我们发现公寓里已经没什么需要收拾的地方了,所有东西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干净又整洁。我一边在壁炉旁烤背取暖,一边观察餐巾,上面的螺纹图案是不规则的,有人用针在完整的布料上勾了许多孔,通过这些孔我看到了衣柜,回想起了那个梦,梦中的那一片寂静正是来自衣柜。我和衣柜背向而立,我是脆弱、忙碌、短暂的那一个,而衣柜只是它自己,它完美地成为它自己。我用手指拧了一下衣柜的门把手,衣柜就在我面前打开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连衣裙的影子,还有R先生的两套旧西装所有东西在黑暗中都是一种颜色。在衣柜里,我的女性特质和R先生的男性特质并无区别,一个物体光滑或粗糙,椭圆形或有棱角,远或近,陌生或熟悉,也变得无关紧要。衣柜里有其他地方的气味,时间对我而言也很陌生,天哪,但那里又存在着熟悉、亲切、不足以用言语描述的东西(我们用文字去命名一个事物时不能对它过于熟悉)。柜门内侧的镜子反射出我的身影,只有一片漆黑,和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几乎没有区别,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在此时并无差异,我的身影出现在衣柜的镜眼里,现在我只需抬起腿就走到了衣柜里面。坐在装了毛线的塑料袋上,封闭空间里,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逐渐增强。
衣柜(部分节选)
我们把家搬到这里的时候,买了一只颜色很深的旧衣柜,价格还没有把它从二手商店运回家的运费高。两扇柜门上有植物形状的装饰,第三扇柜门是玻璃的,我们开着租来的车把衣柜运回来的时候,玻璃上折射出整座城市。运输过程中需要用绳子绑住柜子,以防柜门在中途打开。我拿着一圈绳子站在衣柜旁边时,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荒唐。它会和我们的其他家具很搭。R先生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抚摸着这只木质衣柜,仿佛抚摸着一头刚被新农场买来的奶牛。
最初,我们决定把这只衣柜放在走廊上,用来隔开我们的卧室和其他空间。我将松节油注射到几乎看不见的孔中,它是可以帮助衣柜抵抗时间腐蚀的可靠疫苗。夜里,安放在新位置的衣柜嘎吱作响,垂死的木蛀虫发出悲痛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收拾新房子一处旧公寓。我在地板的缝隙中找到一把手柄上刻有纳粹标志的叉子,木壁板后面是一张旧报纸的残留部分,只能识别出上面的一个词: 无产者。为了挂窗帘,R先生把窗户开得很大,房间里充满了矿工管乐队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晚上。衣柜出现在我们梦中的第一晚,我们都没能睡很久,R先生的手不安地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梦。从此之后,我们经常做一样的梦,梦里一片寂静,万物都像商店展示柜上的装饰物一样悬挂着,我们在这片寂静中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早晨醒来时,我们不必向对方讲述梦的内容一个字就足够了。从这时起,我们不再告诉对方自己做了什么梦。有一天,我们发现公寓里已经没什么需要收拾的地方了,所有东西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干净又整洁。我一边在壁炉旁烤背取暖,一边观察餐巾,上面的螺纹图案是不规则的,有人用针在完整的布料上勾了许多孔,通过这些孔我看到了衣柜,回想起了那个梦,梦中的那一片寂静正是来自衣柜。我和衣柜背向而立,我是脆弱、忙碌、短暂的那一个,而衣柜只是它自己,它完美地成为它自己。我用手指拧了一下衣柜的门把手,衣柜就在我面前打开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连衣裙的影子,还有R先生的两套旧西装所有东西在黑暗中都是一种颜色。在衣柜里,我的女性特质和R先生的男性特质并无区别,一个物体光滑或粗糙,椭圆形或有棱角,远或近,陌生或熟悉,也变得无关紧要。衣柜里有其他地方的气味,时间对我而言也很陌生,天哪,但那里又存在着熟悉、亲切、不足以用言语描述的东西(我们用文字去命名一个事物时不能对它过于熟悉)。柜门内侧的镜子反射出我的身影,只有一片漆黑,和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几乎没有区别,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在此时并无差异,我的身影出现在衣柜的镜眼里,现在我只需抬起腿就走到了衣柜里面。坐在装了毛线的塑料袋上,封闭空间里,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逐渐增强。
房号(部分节选)
在酒店
首都饭店吸引来的就只有有钱人。穿着制服的门童,跑腿的伙计,操着西班牙口音、穿着燕尾服的服务员都是为了他们而存在;四面装着玻璃的静音电梯是为了他们,每天被矮小的南斯拉夫女孩擦拭两次的、不能沾染上任何指纹的铜制门把手是为了他们,只有当他们电梯幽闭恐惧症发作的时候才会使用的铺满地毯的楼梯是为了他们,宽大的沙发、厚重结实的被褥、在床上享用的早餐、空调、比雪还白的手巾、香皂、芬芳的洗发水、橡木坐便器、最新的杂志是为了他们;上帝为他们创造了管理脏内衣的安吉洛和提供特殊服务的扎帕塔,在走廊里穿行的穿着粉白相间制服的客房服务员也是为了他们,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可能关于我说得太多,当我正在走廊尽头的小隔间里换上格子围裙的时候,有关我的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毕竟我脱下了自己的颜色、我的安全气味、我最喜欢的耳环、我夸张的妆容和高跟鞋。我也卸下了我的外地口音、我奇怪的名字、诙谐幽默、鱼尾纹、对这里极品菜肴的喜爱、对琐事的记忆我光裸地站在粉白相间的制服里,就好像突然之间站在了海水的白沫里。而从这一刻开始
整个二层都是我的
每个周末,我八点钟来,不需要赶时间,因为八点钟所有有钱人都在睡觉。酒店将他们纳入怀抱,安稳地摇晃,就好像自己是世界中央一枚巨大的贝壳,而他们则是珍贵的珍珠。远处某个地方汽车醒了过来,地铁则引得小草尖微微颤动。而冰冷的阴影仍旧覆盖着酒店的小花园。
我从花园一侧的门进来,一下子就闻到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它混合了清洁剂、洗过的内衣和因承受不住来来往往的人而流汗不止的墙壁散发出的气味。电梯长宽都是半米停在我面前做好了服务的准备。我按下了四楼的按钮,去我的上司朗小姐原文为英语。那里听指令。当电梯升到二层和三层之间的时候,我脸上总会闪过类似恐慌的表情,我怕电梯停下,怕自己永远留在这里,就像细菌一样,被困在首都饭店的身体里。而酒店醒来以后,就开始慢条斯理地将我消化,撬开我的思想,将我身上还残留的东西一并吸收,在我无声地消失之前,将我变成它自己的养分。但是电梯仁慈地将我放了出来。
朗小姐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眼镜架在她的鼻尖上。所有客房服务员中的女王、八个楼层的女主席、上百个床单枕套的服务员、地毯和电梯的女管家,以及扫帚和吸尘器的女侍从官,就应该打扮成这样。她越过镜片看向我,然后拿出专属于我的卡片,上面的空格和空栏里是整个二层的检查结果,每个房间的情况。朗小姐从不注意酒店里的客人,可能他们对于更高级的工作人员来说更重要,尽管很难想象有谁能比朗小姐更加重要,更加尊贵。
于她而言,酒店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构,我们必须精心呵护的鲜活的存在,虽然它一动不动。当然,人们或匆匆,或缓缓地在酒店里流动,将它的床铺捂热,从它铜制的乳头吸水喝。但是他们只是过客,总会离开,而我们和酒店则留在原地。所以朗小姐向我描述房间的时候,总当它们是被临幸的地方本处波兰语原文亦可做灵异之地解释。永远都用被动语态:被占用的被弄脏的被留下的暂时被解放几天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还会不满地看着我俗气的衣服和脸上残留的、匆忙化的妆。而我已经手拿写着朗小姐漂亮的,有点像维多利亚时期书法的笔迹的卡片顺着走廊走了,一边放松自己,一边还要思考策略。
然后我便不自觉地从后勤区走到了为客人准备的地方。我是通过味道认出来的我必须抬起头才能将其区分。有些时候我能区分: 有的房间闻起来像男士阿玛尼或者拉格斐,又或者像浓郁典雅的宝诗龙。我是通过在时尚网站购买的便宜试用装认得这些气味的,我知道那些小分装瓶长什么样。还有粉饼、抗皱霜、丝绸、鳄鱼皮,洒了一床的金巴利,给温温柔柔的棕发女孩抽的随想曲牌香烟。这就是二层独有的气味,但还不是所有的味道应该只是第二层独特气味的前调。在我赶去自己储物间的路上,我就会像认出老朋友一样认出它。而在储物间里总会发生
转变
我穿着粉白相间的制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看走廊了。我不寻找气味,铜制的门把手上的倒影不再吸引人,我也不再聆听自己的脚步声。现在面对走廊的视角里,吸引我的是门上编了号的长方形牌子。这八个长方形牌子,每个后面都是一个房间被滥用的四角空间,每隔几天就会给别人使用。其中四个房间的窗户面朝街道,街上总是站着一个留着络腮胡、穿着苏格兰裙的男人在弹班杜拉琴。我怀疑他不是苏格兰人。他太有激情了。在他旁边放着顶帽子,里面还有一枚吸引同类的硬币。
剩下的四个窗户面朝花园的房间采光就不是很好,总是浸没在阴影中。这八个房间已经全部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尽管我还没有见到它们。我的眼睛能看到的就只有门把手,其中有几个上面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我挺高兴,因为不管是打扰别人还是打扰他们的房间,对我来说都没有好处,我更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搅我坐拥二层的美梦。有时牌子上会显示请即打扫,这个标志让我进入了准备状态。还有第三类信息: 无信息。这让我像打了激素一样,有点不安,开启我沉睡到这个时候的客房服务员的智慧。有时,当这样的门后面过于安静,我就必须将耳朵贴上去,仔细听,甚至还会从钥匙孔往里面看。这样总好过拿着一手毛巾突然出现在房间里,撞上慌乱遮住裸体的客人,或者更糟,看见客人深陷难以挣脱的梦,就好像马上要消失一样。
|
| 內容試閱:
|
衣柜(部分节选)
我们把家搬到这里的时候,买了一只颜色很深的旧衣柜,价格还没有把它从二手商店运回家的运费高。两扇柜门上有植物形状的装饰,第三扇柜门是玻璃的,我们开着租来的车把衣柜运回来的时候,玻璃上折射出整座城市。运输过程中需要用绳子绑住柜子,以防柜门在中途打开。我拿着一圈绳子站在衣柜旁边时,次感受到了自己的荒唐。“它会和我们的其他家具很搭。”R先生一边说,一边温柔地抚摸着这只木质衣柜,仿佛抚摸着一头刚被新农场买来的奶牛。
初,我们决定把这只衣柜放在走廊上,用来隔开我们的卧室和其他空间。我将松节油注射到几乎看不见的孔中,它是可以帮助衣柜抵抗时间腐蚀的可靠“疫苗”。夜里,安放在新位置的衣柜嘎吱作响,垂死的木蛀虫发出悲痛的声音。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收拾新房子——一处旧公寓。我在地板的缝隙中找到一把手柄上刻有纳粹标志的叉子,木壁板后面是一张旧报纸的残留部分,只能识别出上面的一个词: 无产者。为了挂窗帘,R先生把窗户开得很大,房间里充满了矿工管乐队的喧闹声,一直持续到晚上。衣柜出现在我们梦中的晚,我们都没能睡很久,R先生的手不安地在我肚子上摸来摸去,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梦。从此之后,我们经常做一样的梦,梦里一片寂静,万物都像商店展示柜上的装饰物一样悬挂着,我们在这片寂静中都很快乐,因为我们并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早晨醒来时,我们不必向对方讲述梦的内容——一个字就足够了。从这时起,我们不再告诉对方自己做了什么梦。有一天,我们发现公寓里已经没什么需要收拾的地方了,所有东西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干净又整洁。我一边在壁炉旁烤背取暖,一边观察餐巾,上面的螺纹图案是不规则的,有人用针在完整的布料上勾了许多孔,通过这些孔我看到了衣柜,回想起了那个梦,梦中的那一片寂静正是来自衣柜。我和衣柜背向而立,我是脆弱、忙碌、短暂的那一个,而衣柜只是它自己,它完美地成为它自己。我用手指拧了一下衣柜的门把手,衣柜就在我面前打开了,我看到了自己的连衣裙的影子,还有R先生的两套旧西装——所有东西在黑暗中都是一种颜色。在衣柜里,我的女性特质和R先生的男性特质并无区别,一个物体光滑或粗糙,椭圆形或有棱角,远或近,陌生或熟悉,也变得无关紧要。衣柜里有其他地方的气味,时间对我而言也很陌生,天哪,但那里又存在着熟悉、亲切、不足以用言语描述的东西(我们用文字去命名一个事物时不能对它过于熟悉)。柜门内侧的镜子反射出我的身影,只有一片漆黑,和挂在衣架上的连衣裙几乎没有区别,有生命的物体和无生命的物体在此时并无差异,我的身影出现在衣柜的“镜眼”里,现在我只需抬起腿就走到了衣柜里面。坐在装了毛线的塑料袋上,封闭空间里,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逐渐增强。
房号(部分节选)
在酒店
首都饭店吸引来的就只有有钱人。穿着制服的门童,跑腿的伙计,操着西班牙口音、穿着燕尾服的服务员都是为了他们而存在;四面装着玻璃的静音电梯是为了他们,每天被矮小的南斯拉夫女孩擦拭两次的、不能沾染上任何指纹的铜制门把手是为了他们,只有当他们电梯幽闭恐惧症发作的时候才会使用的铺满地毯的楼梯是为了他们,宽大的沙发、厚重结实的被褥、在床上享用的早餐、空调、比雪还白的手巾、香皂、芬芳的洗发水、橡木坐便器、的杂志是为了他们;上帝为他们创造了管理脏内衣的安吉洛和提供特殊服务的扎帕塔,在走廊里穿行的穿着粉白相间制服的客房服务员也是为了他们,而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但可能关于“我”说得太多,当我正在走廊尽头的小隔间里换上格子围裙的时候,有关我的事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毕竟我脱下了自己的颜色、我的安全气味、我喜欢的耳环、我夸张的妆容和高跟鞋。我也卸下了我的外地口音、我奇怪的名字、诙谐幽默、鱼尾纹、对这里菜肴的喜爱、对琐事的记忆——我光裸地站在粉白相间的制服里,就好像突然之间站在了海水的白沫里。而从这一刻开始——
整个二层都是我的
每个周末,我八点钟来,不需要赶时间,因为八点钟所有有钱人都在睡觉。酒店将他们纳入怀抱,安稳地摇晃,就好像自己是世界中央一枚巨大的贝壳,而他们则是珍贵的珍珠。远处某个地方汽车醒了过来,地铁则引得小草尖微微颤动。而冰冷的阴影仍旧覆盖着酒店的小花园。
我从花园一侧的门进来,一下子就闻到了那股奇怪的味道,它混合了清洁剂、洗过的内衣和因承受不住来来往往的人而流汗不止的墙壁散发出的气味。电梯——长宽都是半米——停在我面前做好了服务的准备。我按下了四楼的按钮,去我的上司朗小姐原文为英语。那里听指令。当电梯升到二层和三层之间的时候,我脸上总会闪过类似恐慌的表情,我怕电梯停下,怕自己永远留在这里,就像细菌一样,被困在首都饭店的身体里。而酒店醒来以后,就开始慢条斯理地将我消化,撬开我的思想,将我身上还残留的东西一并吸收,在我无声地消失之前,将我变成它自己的养分。但是电梯仁慈地将我放了出来。
朗小姐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眼镜架在她的鼻尖上。所有客房服务员中的女王、八个楼层的女主席、上百个床单枕套的服务员、地毯和电梯的女管家,以及扫帚和吸尘器的女侍从官,就应该打扮成这样。她越过镜片看向我,然后拿出专属于我的卡片,上面的空格和空栏里是整个二层的检查结果,每个房间的情况。朗小姐从不注意酒店里的客人,可能他们对于更高级的工作人员来说更重要,尽管很难想象有谁能比朗小姐更加重要,更加尊贵。
于她而言,酒店就是一个完美的结构,我们必须精心呵护的鲜活的存在,虽然它一动不动。当然,人们或匆匆,或缓缓地在酒店里流动,将它的床铺捂热,从它铜制的乳头吸水喝。但是他们只是过客,总会离开,而我们和酒店则留在原地。所以朗小姐向我描述房间的时候,总当它们是“被临幸的地方”本处波兰语原文亦可做“灵异之地”解释。——永远都用被动语态:“被占用的”“被弄脏的”“被留下的”“暂时被解放几天的”。她一边说着,一边还会不满地看着我俗气的衣服和脸上残留的、匆忙化的妆。而我已经手拿写着朗小姐漂亮的,有点像维多利亚时期书法的笔迹的卡片顺着走廊走了,一边放松自己,一边还要思考策略。
然后我便不自觉地从后勤区走到了为客人准备的地方。我是通过味道认出来的——我必须抬起头才能将其区分。有些时候我能区分: 有的房间闻起来像男士阿玛尼或者拉格斐,又或者像浓郁典雅的宝诗龙。我是通过在“时尚”网站购买的便宜试用装认得这些气味的,我知道那些小分装瓶长什么样。还有粉饼、抗皱霜、丝绸、鳄鱼皮,洒了一床的金巴利,给温温柔柔的棕发女孩抽的“随想曲”牌香烟。这就是二层独有的气味,但还不是所有的味道——应该只是第二层独特气味的前调。在我赶去自己储物间的路上,我就会像认出老朋友一样认出它。而在储物间里总会发生——
转变
我穿着粉白相间的制服,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看走廊了。我不寻找气味,铜制的门把手上的倒影不再吸引人,我也不再聆听自己的脚步声。现在面对走廊的视角里,吸引我的是门上编了号的长方形牌子。这八个长方形牌子,每个后面都是一个房间——被滥用的四角空间,每隔几天就会给别人使用。其中四个房间的窗户面朝街道,街上总是站着一个留着络腮胡、穿着苏格兰裙的男人在弹班杜拉琴。我怀疑他不是苏格兰人。他太有激情了。在他旁边放着顶帽子,里面还有一枚吸引同类的硬币。
剩下的四个窗户面朝花园的房间采光就不是很好,总是浸没在阴影中。这八个房间已经全部印在了我的脑海中,尽管我还没有见到它们。我的眼睛能看到的就只有门把手,其中有几个上面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我挺高兴,因为不管是打扰别人还是打扰他们的房间,对我来说都没有好处,我更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搅我坐拥二层的美梦。有时牌子上会显示“请即打扫”,这个标志让我进入了准备状态。还有第三类信息: 无信息。这让我像打了激素一样,有点不安,开启我沉睡到这个时候的客房服务员的智慧。有时,当这样的门后面过于安静,我就必须将耳朵贴上去,仔细听,甚至还会从钥匙孔往里面看。这样总好过拿着一手毛巾突然出现在房间里,撞上慌乱遮住裸体的客人,或者更糟,看见客人深陷难以挣脱的梦,就好像马上要消失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