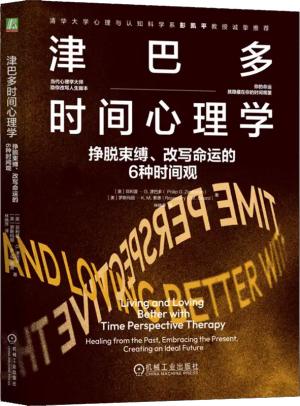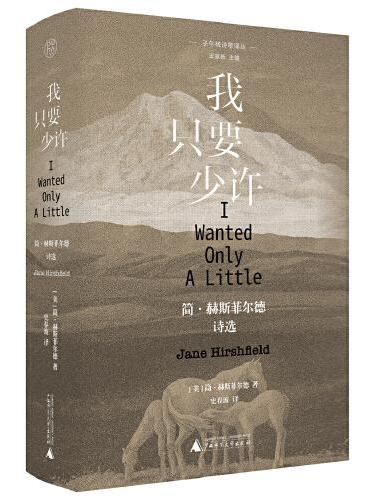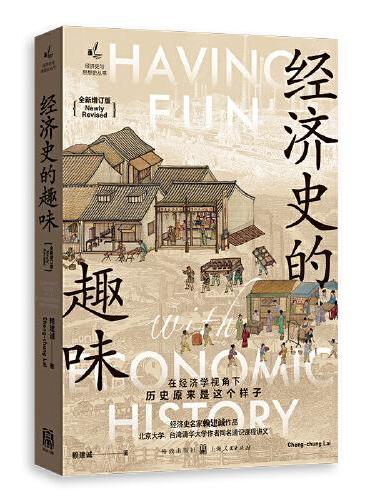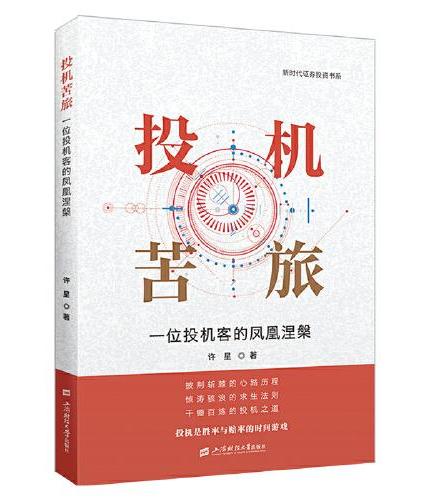新書推薦:

《
8秒按压告别疼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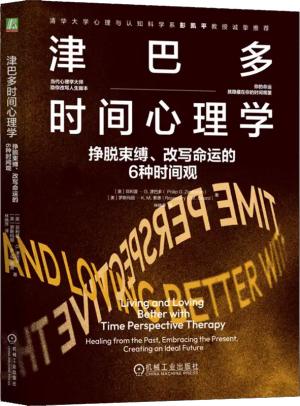
《
津巴多时间心理学:挣脱束缚、改写命运的6种时间观
》
售價:HK$
77.3

《
大英博物馆东南亚简史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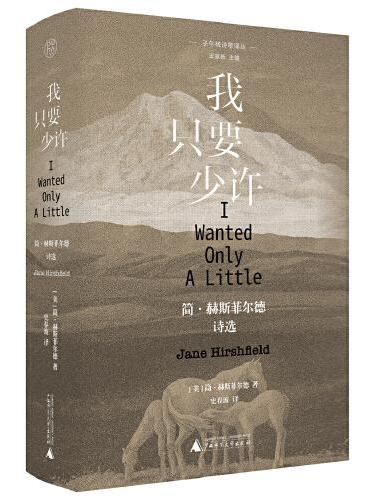
《
纯粹·我只要少许
》
售價:HK$
8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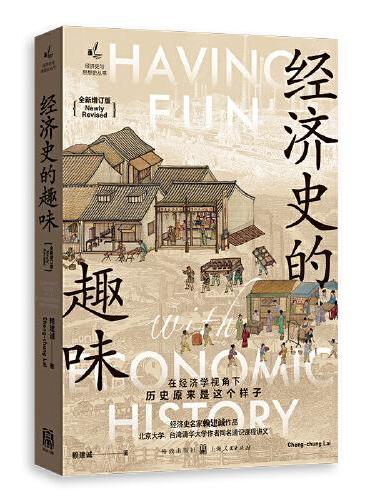
《
经济史的趣味(全新增订版)(经济史与思想史丛书)
》
售價:HK$
84.0

《
中国古代鬼神录
》
售價:HK$
19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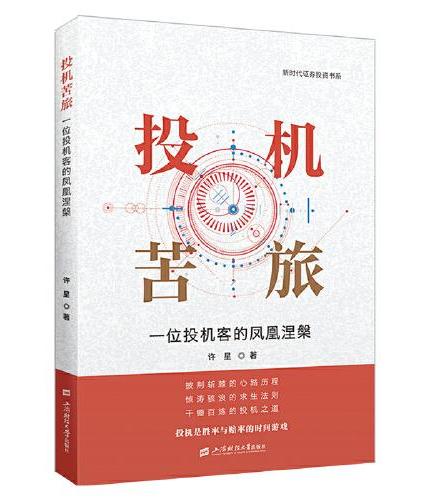
《
投机苦旅:一位投机客的凤凰涅槃
》
售價:HK$
88.5

《
重返马赛渔场:社会规范与私人治理的局限
》
售價:HK$
69.4
|
| 編輯推薦: |
郁达夫小说奖、《作家》金短篇小说奖获得者雷默积淀四年力作
一部劝人向善的小说
一部敬畏生命的小说
一部悟道的小说
|
| 內容簡介: |
|
《大樟树下烹鲤鱼》一书收录了雷默近四年的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视野宽广,主题多变,涉及生死、童年、饥饿、寻找,甚至还有科幻,小说在一个切面上展开,进入人物隐秘复杂的内心世界。如《祖先与小丑》《飘雪的冬天》等小说对生命的流转,在生生不息的繁衍过程中体会得到与失去,以探求普通人的人生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苍蝇馆子》《著名病人》《大樟树下烹鲤鱼》等小说把视角对准了美食,对食物的迷恋和审美上,体会到世事的苍茫,而寻找的过程又回归了生命的本源。本书是对雷默近年小说创作的一次高质量的精选,代表了他的创作成果,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
| 關於作者: |
|
雷默:1979年10月生于浙江诸暨,现居宁波。在《收获》《人民文学》《花城》《作家》《江南》《十月》《当代》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小说月报》等选载,并入选多种年选,部分作品被译成英、俄、日文。出版有小说集《气味》《追火车的人》等。
|
| 目錄:
|
免费在线读祖先与小丑
父亲得了食道癌,生命倒计时的时候,他还在惦记着吃的。他说最好过年的时候能杀一头猪,猪尾巴做成酱肉,切成小段,放饭锅里蒸,会唆哦冒油。事实上,膨胀的肿瘤让他 咽口水都非常困难。我很难过,如此热衷于吃的人偏偏生这 样的病!
也是在那个月,母亲偷偷跟我说,你爸活不到过年了,应该为他准备后事了。我去喊了村里的木匠,让他为我父亲打口棺材。木匠是我远房表亲,平日里看不出是个木匠,大部分时间他都扛着锄头游走于路上,慢吞吞的像只乌龟。他问我,娘舅怎么了?我说快不行了,大概就这几天。他停下了手里的活,带上工具就来了我家。
楼下伐木的声音传到了楼上,父亲就知道是在给他打棺材。他问我用的是什么材料,我说浸池塘里的几段木头都捞起来了。父亲又问,那段阴干的檀木呢?我说也用了。父亲 迟疑了阵,陷入了沉默中。我知道他是心疼那段木材,当初找到这棵碗口粗的檀树时,他欣喜不已,说留到以后可以 派大用场,那时候他绝没想到是为自己打棺材用的。我说, 一段木头而已,用就用了。父亲没有再吭声。
我猜没有那口棺材,父亲可能早几天就走了,他一直在等那口棺材。村里也有这样的老人,奄奄一息,挨着挨着又挺过难关,活过来了,等棺材打好,又用不上了。所以木匠的活干得不紧不慢,他还时不时地去探望一下我父亲,在床头跟我父亲聊一会儿天,告诉他,棺材打好还需要一段日子。他看多了弥留之际的老人,知道哪些老人还能挺一挺,如果真不行,他也会加快进度,绝不会发生人过世了,棺材还没打 好的情况。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木匠都会言之凿凿地留下一句话: 娘舅一时走不了,你们放心。十天后,他给棺材上完漆,收拾着工具要走了,我真有点舍不得他。我说,你空的时候多来看看他。他笑嘻嘻地答应了。事实上,后来他再也没来过。
楼下安静了,父亲的胃口突然好了起来,他喝下了满满 一碗粥。陈小秋在床边高兴得像个孩子,她说,爸爸要好起来了。那时候,父亲脸色红润,精神也好像回来了。喝完粥, 他让我给他捶背,我触到他的后背,发现他瘦得吓人。那仿佛是一具空壳,我特别留心力道,生怕下手重了会捶疼他。
捶了一小会儿,他示意我停下,我从他后背伸出脖子去看他, 发现他脸上的光泽变淡了。
父亲指了指床边的橱柜,让我去拿上面的种子。我竟然 不知道橱柜上还放着种子,那些种子都用旧报纸包着,包得很规整,形状和大小都差不多,握在手中像个面包,打开后, 种子光鲜亮丽,一颗颗都饱满而圆润。父亲语气低沉,不容商量,他说,你仔仔细细,用手捋一遍!我不明白,他为什么 让我这么做,他说那都是他留下的种子,活人的手不摸一摸, 他担心来年发不了芽。祖先与小丑
父亲得了食道癌,生命倒计时的时候,他还在惦记着吃的。他说最好过年的时候能杀一头猪,猪尾巴做成酱肉,切成小段,放饭锅里蒸,会唆哦冒油。事实上,膨胀的肿瘤让他 咽口水都非常困难。我很难过,如此热衷于吃的人偏偏生这 样的病!
也是在那个月,母亲偷偷跟我说,你爸活不到过年了,应该为他准备后事了。我去喊了村里的木匠,让他为我父亲打口棺材。木匠是我远房表亲,平日里看不出是个木匠,大部分时间他都扛着锄头游走于路上,慢吞吞的像只乌龟。他问我,娘舅怎么了?我说快不行了,大概就这几天。他停下了手里的活,带上工具就来了我家。
楼下伐木的声音传到了楼上,父亲就知道是在给他打棺材。他问我用的是什么材料,我说浸池塘里的几段木头都捞起来了。父亲又问,那段阴干的檀木呢?我说也用了。父亲 迟疑了阵,陷入了沉默中。我知道他是心疼那段木材,当初找到这棵碗口粗的檀树时,他欣喜不已,说留到以后可以 派大用场,那时候他绝没想到是为自己打棺材用的。我说, 一段木头而已,用就用了。父亲没有再吭声。
我猜没有那口棺材,父亲可能早几天就走了,他一直在等那口棺材。村里也有这样的老人,奄奄一息,挨着挨着又挺过难关,活过来了,等棺材打好,又用不上了。所以木匠的活干得不紧不慢,他还时不时地去探望一下我父亲,在床头跟我父亲聊一会儿天,告诉他,棺材打好还需要一段日子。他看多了弥留之际的老人,知道哪些老人还能挺一挺,如果真不行,他也会加快进度,绝不会发生人过世了,棺材还没打 好的情况。
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木匠都会言之凿凿地留下一句话: 娘舅一时走不了,你们放心。十天后,他给棺材上完漆,收拾着工具要走了,我真有点舍不得他。我说,你空的时候多来看看他。他笑嘻嘻地答应了。事实上,后来他再也没来过。
楼下安静了,父亲的胃口突然好了起来,他喝下了满满 一碗粥。陈小秋在床边高兴得像个孩子,她说,爸爸要好起来了。那时候,父亲脸色红润,精神也好像回来了。喝完粥, 他让我给他捶背,我触到他的后背,发现他瘦得吓人。那仿佛是一具空壳,我特别留心力道,生怕下手重了会捶疼他。
捶了一小会儿,他示意我停下,我从他后背伸出脖子去看他, 发现他脸上的光泽变淡了。
父亲指了指床边的橱柜,让我去拿上面的种子。我竟然 不知道橱柜上还放着种子,那些种子都用旧报纸包着,包得很规整,形状和大小都差不多,握在手中像个面包,打开后, 种子光鲜亮丽,一颗颗都饱满而圆润。父亲语气低沉,不容商量,他说,你仔仔细细,用手捋一遍!我不明白,他为什么 让我这么做,他说那都是他留下的种子,活人的手不摸一摸, 他担心来年发不了芽。
那时候,我挺沮丧的,母亲却出奇地顺从,她跟我说,你都答应了去,不要让你爸不痛快。我只好都依着做,捋完种 子,我又重新用旧报纸包好,每一包都包得小心翼翼,仿佛那是我父亲全部的心血。
父亲的精神彻底委顿下来,他躺在床上跟我们说,你们去休息一下,晚上可能会没得睡。我激灵了一下,母亲却凑到他的跟前,问他大概什么时候走。父亲犹豫了一下,指了 指窗外的夕阳。我转过头去看,通红的落日如同老人的一声 叹息,正缓缓地往西边隐退下去。
他眼睛中的光变得微弱,仿佛隔着一层轻薄的雾气,一 直看着我和陈小秋,我想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认出我们了。 我喊了他一声,他微微地点了点头,陈小秋哭了起来,我看到父亲脸上的愁容像波纹一样扩散了开去,他的脸色变得恬淡而安详。
晚上,婶子、堂哥他们都来了,床前站满了人,我恍惚间明白过来,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原来,送终跟送一个出远门的人情形是差不多的。大家都站着,伸长了脖子,依依不舍地看着他。父亲躺在床上,只剩下出气的声音,声音很 大,仿佛在干一件重活,看上去十分吃力。
母亲跟我说,你去抱抱你爸,送他一程。众人都上来帮忙,把躺着的父亲上身抬了起来。我盘着腿坐到了父亲的背后,感觉像抱着一个大孩子。那一瞬间,我感觉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最早的童年记忆发生了偏移。我清楚地记起小时候父亲抱着睡得朦朦胧胧的我往楼梯上走,我的两条小腿露在外面,时值隆冬,小腿肚那里凉丝丝的,木楼梯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音。之前,我一直以为最早的记忆是在五岁的时候我手上拿着一块南瓜饼,在堂哥家的黄狗面前晃了 晃,被它一口叼走了,我哇哇大哭起来,那动静是如此之大, 以至于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忆犹新。
我恍惚出神的时候,周围的哭声响了起来,所有的女人都开始号啕大哭,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母亲凑上前来跟我小 声叮嘱,要忍一忍,千万别把眼泪滴到父亲脸上,不然他会走得不安心的。我应了下来。那时候,母亲在父亲的身边不停地讲宽慰的话,意思让他放心地走,家里她会照顾好的,再过 些年,等孩子大了,她就下去陪他。这个过程很漫长,母亲一直絮絮叨叨地讲着,我好几次想把父亲放下来,因为我的腿坐麻了,但我也不想放下还未彻底咽气的父亲,我知道这一 放下,就永远地放下了。盘着的双腿由麻木变成针扎般的刺痛,这让我尴尬不已,我起不了身,又不能跟人讲述我的感受,就这样一直抱着父亲,直到他的身体开始慢慢变凉。
堂哥率先看到了我的六神无主,他把我从床上扶了下 来,我险些跌倒在地,他以为我是伤心过度,我低声跟他说, 腿坐麻了。他赶紧挪了一条凳子,让我坐下。片刻之后,我的脚恢复了知觉,悲伤的情绪如同轻柔的潮水,一寸寸地淹 上来,淹没到脖子那里,我几乎难以呼吸。这一晚,我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精神处于游离的状态,很多人叫我,我都没听到。
第二天清晨,堂哥变成了最忙碌的人,我看着他进进出出,理着千头万绪的杂事,恍然间有点心疼他。我也跟了出去,发现家里来了很多人,哭声如同号角,一响,四面八方的人都赶过来了。堂哥问我,请哪里的道士?我蒙在那里,不 知道该如何回答。堂哥说,算了,还是我去请吧。说着,他匆匆忙忙地往外赶,走不了几步,又停下来吩咐租赁碗筷的人。我看到堂哥手里拿着一本污垢很厚的小笔记本,还有一支鹅毛圆珠笔。他麻利地记着账,那些字又粗又大,笔迹还挺难看。他记账的时候,特别专注,蓬松的头发会微微地颤抖。
那时候,我感到很丢脸,一个人站在门外,不停地有人过来安慰我,我却记不清到底是哪些人,脑袋中突然浮现出傻子马勒的样子,哪里有热闹他就往哪里凑。很奇怪,在闹哄哄的人群中竟然没见到他的身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