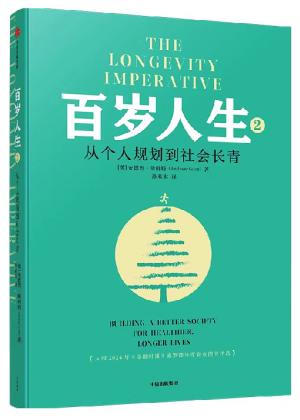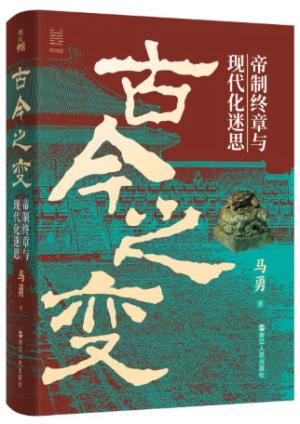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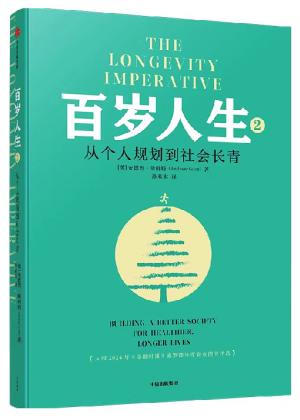
《
百岁人生②:从个人规划到社会长青
》
售價:HK$
74.8

《
超级肠道
》
售價:HK$
97.9

《
中老年人学AI:人工智能让生活更精彩
》
售價:HK$
98.8

《
不想成为妈妈那样的母亲
》
售價:HK$
49.5

《
龙头股交易指南(上)
》
售價:HK$
5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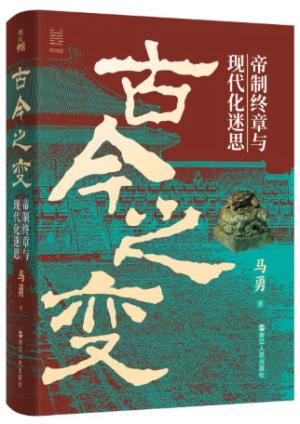
《
古今之变: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
》
售價:HK$
107.8

《
存在的意义 11位心理治疗师的存在-人本之旅(孤独、意义、自由、敬畏、死亡交织在人生旅途中,推动我们
》
售價:HK$
93.5

《
达尔文的植物世界 跟随达尔文的试验与研究发现自然植物的奥秘 达尔文进化论植物篇
》
售價:HK$
165.0
|
| 編輯推薦: |
1、矿工诗人陈年喜shou部非虚构故事集。作者应邀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巡回演讲。《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媒体重磅报道。
2、重振《诗经》的民间叙事传统,挖掘中国人悲怆又炽烈的生存力。震得人头皮发麻。
3、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陈年喜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天赋好,语言好,靠一种天性。
4、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张慧瑜:《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见证了他二十多年流离西北、西南的颠沛生活,既是一本从秦岭腹地到昆仑山脉的天地之书,也是亿万新工人从劳动中萃取的生命之书。
5、随书附赠陈年喜ZUI新诗集《炸药与诗歌》。
6、如果《平凡的世界》有后续,大概就会这么写。《平凡的世界》结尾,主人公孙少平又回到了大牙湾煤矿,读者说:如果孙少平的故事还有续篇,命运大概也会像陈年喜一样悲怆吧!
7、你买1本书,我捐1块钱。本书与专注尘肺病救助的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合作,你每买一本书,我们捐1块钱,给尘肺病患者子女提供助学金。
8、本书带你辗转中国边荒,遍见奇异风情。一路穿过长江、黄河、叶尔羌河,踏遍新疆的萨尔托海,内蒙的戈壁滩,大兴安岭的茫茫雪山……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矿工诗人陈年喜SHOU部非虚构故事集。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为巷道爆破工,陈年喜深潜于大地5000米深处,用炸药和风镐轰开山体,凿出金、银、铜、铁、镍。
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是王二、德成、小渣子等同样低微的命运。后来有的人在爆炸中跑成一蓬血雾,有的被气浪削成了两半,只有他相对幸运,只留下颈椎错位,尘肺病,还有一只失聪的右耳。
翻开《活着就是冲天一喊》,这些悲怆炽烈的生命逐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艰辛的劳绩,无常的生死,每一个故事,都像陈年喜在矿山深处敲下的石头一般坚硬,炫黑。
铁骨深情的爆破工陈年喜,在深山矿洞中抒发着“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人民日报》
在矿山,陈年喜的灵感像泉水一样涌上心头,只要把笔放在炸药箱上,一行行字就流淌出来。
——《智族GQ》
在克拉玛依矿上,床垫很薄,大家把空炸药箱垫在底下睡觉。诗句来的时候,陈年喜就掀开褥子,把它们写在炸药箱上。走的时候卷起铺盖,下面是满满一床的诗。
——《南方周末》
|
| 關於作者: |
陈年喜,矿工诗人。
《活着就是冲天一喊》是其SHOU部非虚构故事集。
他的作品重振了《诗经》的民间叙事传统,以苍凉细腻的笔触,呈现了中国人悲怆又炽烈的生命力。
茅盾文学奖评委张莉评论说,陈年喜的散文和那些名家放在一起毫不逊色。“天赋好,语言好,靠一种天性。”
|
| 目錄:
|
代序:一个矿工诗人的下半场 / I
炸药与诗歌
确诊尘肺病后的日子 / 002
从疆南到甘南 / 014
我的朋友哈拉汗 / 025
小渣子 / 046
德成 / 057
萨尔托海 / 062
在玲珑 / 070
铁厂沟的饺子 / 082
水桶席地而坐 / 086
乡关何处
父子书 / 097
父亲和摩托车 / 102
母亲 / 106
扶杖的父亲 / 110
父亲的桃树 / 114
岳父 / 119
司命树 / 126
病中一年记 / 133
理发 / 141
我的春节回乡路 / 145
赶路的人,命里落满风雪
媒事 / 157
洞穴三十年 / 168
填埋垃圾的人 / 180
断链的种菇户 / 191
关山难越上班路 / 195
无处胎检 / 199
我的精神家园
生活,真相,书写 / 204
香椿 / 211
挖苕记 / 214
生活有味是清欢 / 219
慵懒 / 222
年 / 227
代后记: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 232
|
| 內容試閱:
|
老鸹岔这地方的天亮得特别早。也不奇怪,山那么高,峰那么绝,和天离得那么近,突兀的一道屏障,空无遮拦,不早亮都不行。
这时候,远远地向山下望去,陈村镇隐隐约约,高的楼,矮的屋,庄稼与树木,分不大清楚,朦朦胧胧一片。分得清的,是时不时的公鸡打鸣声。鸡鸣如一把新刀,从鞘里缓缓拔出来,在风里划一道弧线,那道弧亮而弯,像一支射偏了的箭,又“唰”地落了地。鸡鸣十里,老天安排公鸡报晓是有道理的。狗叫也是听得到的,却远没有鸡鸣明亮、入心。像一盆少油寡盐的炖白菜。
巷道已掘进到了八百米,还不见一丝矿脉的影子,按那发黄的牛皮纸图纸资料,已经过线了,老板有些着急了。昨晚的生产会开到凌晨一点,也没个结果,后不得不做出的结果是向北六十度急转。这是我的主意,其实这也不是我的主意,是王二的主意,我替他说出来而已。他对我私下说出的理由是,你听北面炮声每天那么急,一天至少三茬儿炮,显然是见着矿脉了,抢着圈矿呢。我也说,是见脉了。我没有对他说出来的一句话是,见鬼了,岩里头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
因为急转,2.6米的钎杆直接用不上了,要打套钎。我喊小渣子把两根1米的短钎杆带上,他答应一声听见了,就去换工作装了。我递一根烟给王二:你要北转,转不出矿咋办?他说不怕,转不出矿能转出活儿也行,收麦还早呢。
王二到底是哪儿的人,我也不大清楚,也用不着清楚,能搭伙就行,也确实,这老小子不错,能吃苦,脾气好,技术也好。这座山的石头硬得要死,掘进面没有十个掏心孔拿不下来。我俩每人抱一台钻机,掏心孔差不多都是他完成的。他每天几乎九十度弓着腰,机器在怀抱里又跳又叫,嘴巴上叼一根烟,目不斜视。一弓就是四五个小时,孔距毫厘不差。麻黑麻黑的段面岩石上,规整有序的钻孔如一朵好看的素绘梅花。
小渣子是四川巴中人,那地方,和陕西隔着一道岭。他十七岁,原先是出渣的,嫌出渣苦,人也机灵,偶然碰到一块下班时,就替我们背着工具包,到宿舍抢着打洗脸水。我和王二就收下他做助手了。个班下来,我说,二,小子行,给他开三千,王二说三千五,我说为啥多五百,他说他值多得五百,我想半天,说行。小渣子跟随我们从三百米掘进到八百米,快五个月了。今天,他穿了一套崭新军训迷彩服,领标都在,只是有些肥大,这是他一个月前下山买的,一直没舍得穿过。
我问小渣子带了几颗钻头,他比画八颗。王二点点头,够了。我说今天活儿麻烦,渣子,你把空气压缩机调到八个。他麻利地奔去空压机房。
王二说,这小子机灵,下个月教他手艺。我说你别害人家,挣俩钱还是让他回去读书。王二把扳手一扔,屁,读书能咋的,能挣过咱手艺?说话间,气流就到了。风管像蛇一样跳起来,管头喷出一股白雾,气流吹得石头乱飞,我一把抓了起来,它愤怒得在空中乱舞。
我说今天我来打掏心,再不练练手艺就荒了。王二抓起钻机,先让小渣子开了边眼。按说急转,是要先剥邦的,就是在拐弯处形成一个宽大些的空间,不至于架子车因角度太急而进出困难,但任务紧,为了省事,就免了这套手脚,反正将来车子拐角不够,可以再补。
王二的机器消声罩吐出的气流直冲我的脸,冰碴儿打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只得把帽檐压低。两台机器吐出的雾气让工作面伸手莫辨,我只有把头灯调到亮,还是看不清钎杆和标杆的间距,在风压的巨大作用下,钎杆甩出一团弧光,如戏台上的飞舞银枪。这样很危险,弄不好就会窜孔,前功尽弃。
打到第六个孔时。还是窜孔了,钻头突破了两孔间的隔阂,拐了个弯窜到了另一个孔里。这种情况非常麻烦,边孔和辅助已经完成大半,重新布陶心孔将牵一发而动全身。我收了钻机的腿,扛住机头往外拔,钻机震得我头疼欲裂,钎卡一跳一跳地要脱落,钻杆只是空转,纹丝不动。王二说,把空压机停了,出去拿把洋镐来。小渣子停了机器,出去了。我说恐怕不管用,孔里全是石末子,钻头已经卡死了。王二说管用,递给我一根点着的烟。
小渣子把去了柄的镐反套在窜孔的钎杆疙瘩上,又插上一根钎杆去使劲别着,让镐孔的边沿部分死死地卡住钎疙瘩,王二抡起大锤在镐上向外猛砸,这就形成了巨大的向外拉力。这是我们惯用的方法,非常实用。王二抡着大锤一气儿砸了二百下,汗珠四溅,小渣子被震得龇牙咧嘴,窜孔的钎杆依然纹丝不动,仿佛从岩石里长出来的一棵甘蔗。
王二大概也长不了我几岁,甚至并不长,就是个头比我高好多,接近一米九。这身高干巷道,真是活受罪,也不知道他的手艺是从哪儿开始学的,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爆破也是一个江湖,他在这个江湖上有些声名。传奇的一个故事是,他在塔什库尔干时,一人独战五个来抢炸药库的坏人。坏人抢炸药库干什么,长什么样,谁都不知道,但坏人有多坏,大家看了王二大腿上的疤都知道了。据说当时一把英吉沙刀刺进了他的大腿。故事原多无考,但刀是真的,刀无槽,银柄,铁波银浪,纹饰美过所有工笔雕版画。王二老是用它下班了削苹果,有时也削厨房的大白萝卜解渴,我用它偷偷削过脚指甲,真的是削甲如泥。
老鸹岔是秦岭南坡河南灵宝段的一个山岔子,距华山不远。那天我从老家陕西来矿山,车过华山不久就看到它了。外窄里阔,像一把打开的扇子,一些扇条的接着天际,云蒸雾绕。每条扇肋上都有不等的矿洞,白花花的矿渣流出好远,像一排排鼻孔涕泪长流,远远望去,却也好看。
我那天到的时候王二已提前到了三个月,他和他的两个伙伴三个月里掘进了三百米巷道,两个伙伴受不了石头的硬,骂骂咧咧地走了。那天王二劈头就问我,你怕不怕石头硬?我说我是石头它老子,不怕。其实我也怕,不怕是假的,我不怕,两只手的虎口怕。
我又从王二手里接过大锤,小渣子显然有些吃不消了,我每扬一下锤,他就“哎哟”一声,那川腔还带着童声的哎哟和大锤碰撞铁镐的声音搅在一起,有一丝说不出的涩苦味。那应该是若干年后一个成人才该有的味道。
我扔了锤,对王二说,不行了,崩了它。王二扔了烟头,也说,崩了它。崩了它,就是在被窜的孔里填上少量的炸药,利用炸药爆炸形成的后坐力,把钎杆拽出来。好处是省力,坏处是一根钎杆报废,这是万不得已的招数。
记得我初到矿山时,一律使用的是TNT炸药,那玩意儿爆炸性大,毒性也大。初开始,我还是架子车工,就是把爆破下来的矿石或毛石用架子车拉出去。滚滚烟尘里,和伙伴们装车、拉车,一趟又一趟,空气又热又呛,常常有人晕倒,倒下了,没倒的人就找来冷水在他头上整桶地泼。泼不醒,就装上架子车拉出洞口,扔在渣坡上让风吹,待一排渣清理完,晕倒的人也醒过来了,喝一大碗白糖水,躺下睡好几天,嘴里不住地骂,狗日的太毒了,太毒了。也有永远没醒过来的,也不知道疼不疼,一声不吭就走了。
小渣子从铁皮箱子里取来了一包炸药、一根雷管和一米导火索。他现在也是材料管理员的角色,腰上挂一串钥匙。只是他还不够资格,材料签收单上用不着他签字,也不用他负责。王二有些不高兴,用小刀割下一段扔向小渣子:一半就够了,真是败家子儿。我低头看了看笔直的巷道,一眼可以看到洞口那拱形的亮光。光并不灿烂,有些弱,洞口对面山坡上,有要开未开的桃花数树。旁边别的树叶子已经显绿了。显然,我们已经耽误了很久,我有些内疚起来,虽然这也是常常碰到的情况。
据经验判断,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已经到了山体的中部,如果直线掘进,再有八百米山体就可以打穿了。现在石头的质地、硬度、含水度也证明了这一点,越是山梁下面,石头硬度越高,同时承受的挤压力也更大,见机变形。否则也不至于钎杆被卡得这么死。
王二一下子填进去了四管炸药,他是担心少了拿不下来。现在矿山普遍使用的是硝铵炸药,它产生的毒气相对小一些,威力却一点儿没有减弱。我再次看看笔直的巷道,隐隐有些担心,它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该有多大?沿着枪管一样的巷道,它的杀伤力将延伸到多远?在若干年后使用导气雷管之前,干爆破的我们一直在和导火索的燃烧速度练速度,和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比赛跑。赢了,继续干,输了,就回家了。这家,有时在陕西、四川,有时在河北、山东,有时在很遥远的地方。那地方从来都没去过。
王二嗜酒,刀头舔血的人,没有几个不喜欢酒的。我初到的当夜,王二为我接风,三斤猪头肉、二瓶西凤和一包花生米,我俩一下子干到半夜。他用大杯,我用小杯,有点儿欺负他,他也不在意。东一句西一句地交流里,我知道他的历史大致如此:五岁死爹,十岁娘嫁,有一个妹妹已经嫁人,夫妻关系不好,三天两头闹离婚。他喝到脸色发红,我也耳根发热时,他脱下皮袄,用筷子敲打桌沿,给我来了一段:
一见娇儿泪满腮,
点点珠泪洒下来。
沙滩会一场败,
只杀得杨家好不悲哀。
儿大哥长枪来刺坏,
你二哥他短剑下命赴阴台,
儿三哥马踏如泥块,
我的儿你失落番邦
一十五年载不曾回来,
……
是京剧《四郎探母》。王二嗓音发沙,但音准不错。到悲怆处,突然拔高调门,低处时,似要断绝,越发显出杨门的忠烈和不幸。王二已显秃顶,只有胡子茂盛,一百瓦的白炽灯照耀着他发红的脸,荒山野水粗硬的风,早已削尽了他青春的颜色。他眼里有些悲戚。我知道他已经走了,去到了另一个地方,那地方遍地狼烟,他正横刀跃马力挽山河,而江山破碎,残阳如血……
我突然无由地想起了另一个人,曲从口来:
三更里英台怨爹娘,
只怨爹娘无主张,
不该将奴许配马家郎。
梁兄待我恩义广,
我待梁兄空一场。
……
那一天,小渣子还没有来,或者说,我们还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会在颇长的时间里,成为我们的一部分。那夜空空的帐篷只有我和王二,杯盘狼藉,后我们都吐了一地,猪头肉的腥味,让大家多日都不愿进门。
小渣子接了电话,是工程部打来的,问怎么回事,半天不听炮响?他有些生气,把电话筒一扔,电话听筒像一只荡秋千的猴子,不停地荡来荡去,在石壁上碰了几下,终于停了下来。
一切妥当。王二割导火索用的小刀却怎么也找不到了,他掏出打火机,点了十几下也没点着导火索头。我为他打着灯,看见他握打火机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这一刻,谁都紧张,谁都怕,不管你干了多少年,点燃过多少导火索。只有初入道的人才会没有恐惧感,那是还不知道怕。
有一年,在克拉玛依的萨尔托海,那是一口竖井,三中段巷道已经打到六百米深,矿很富,矿茬有两米厚,每天提上来的矿石有百十吨,选厂日夜加班也忙不过来。工人常常可以碰到颗粒金,大块的有赤豆大小,金灿烂的,纯度很高,拿到金店,直接能加工成饰品。百十米长的采区,有近二十个溜矿斗,溜矿斗很陡,一开闸“哗”的一下就是一矿车,这一车推走,另一辆马上顶上。矿槽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堵,大块的矿石挤在一堆,都要下来,谁也不让谁。工人就用炸药包炸,用一根木棍,包一个炸药包,顶上去,点着,轰的一声,矿石就下来了。后来矿上有了规定,除了爆破工,别的人不能碰炸药,矿部就让爆破工下井值班。那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节,中午干活儿,下午放假,吃月饼和红烧肉。差几车不够八十车,八个出矿工,不好分账,就让一个姓李的下去顶炸药包。他用打火机点导火索,点了几十下,也没点燃,打火机受不了,不发火了,就打电话上来让放一个打火机下去。打火机才放到井口吊斗上,下面轰的一声。
上面的人下去一看,没见到人,只见汹涌的矿石已把通道堵死了,三班人日夜不停,扒通了巷道,见一个人完完好好地在里头坐着。他是缺氧死的。当时我在另一个矿口,离得不远,经常在一块儿打三带,总赢他的钱。老板赔了十万也不知道为什么炸药包会自爆,其实我懂得,不是自爆,而是导火索内燃了,看着没有起火,其实内部已经燃烧。这是一种次品产品。有经验的人在不能确定导火索燃没燃时,会用手捏一捏,如果某截发热,那就是已经内燃了,得快跑。那是个假货遍地的年月,好多人命送在这类假货上,让你防不胜防。
王二是死在我手上的,也是死在他自己手上,我不该不小心窜了孔,他不该把导火索弄得太短。但死,这是迟早的事儿儿,谁也没有办法的事。
我醒过来时,右耳再也听不见了,从此世上的许多话语,别人只能靠手来说出,我靠眼睛来听。
一米长的钎杆,从王二的后背穿过前胸,没有一滴血。在处理他的后事时,人们怎么也拔不下来,像原本从身体上长出的一只细手。小渣子说,师傅一辈子都在玩这个,是他舍不得,让他带着走吧。就带着去了火化厂。
小渣子一直没有挣到钱,也就没有机会回去复读,他一直还待在老鸹岔,我第二年再返故地时,他已成了一名正式爆破工,嘴唇上一层薄毛,手下带了两个徒弟。原来的矿洞一直打到一千多米,七拐八弯,把山体打成了迷宫,一直没有见矿。老板倾家荡产,在陈村镇上开了一家小饭馆。被欠了工钱的,可以吃饭不要钱。这是小渣子告诉我的。我们在另一个矿口再次结伙,他仍喊我“师傅”。
老鸹岔像一把打开的扇子,扇子的一头常年被云雾罩着,谁也没到过那些的地方。据说某个山顶有一座庙,叫狐仙顶,住着狐仙,狐仙有时会下山到陈村镇上购买些脂粉和鸡鱼,只是谁也没有见过。倒是漫山遍野,生长着许多香椿树,得到炸药残末的滋养,有说不出的肥嫩。工人们常常把芽头掰下来,炸面饼吃。为了保存,有时候会满满地窝一罐浆水菜,一直吃到来年花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