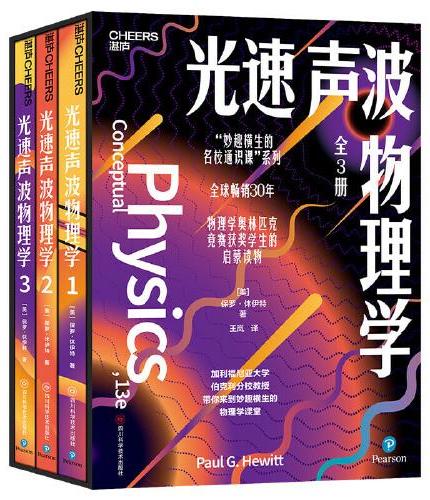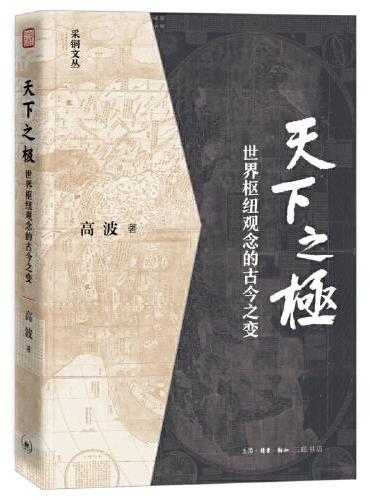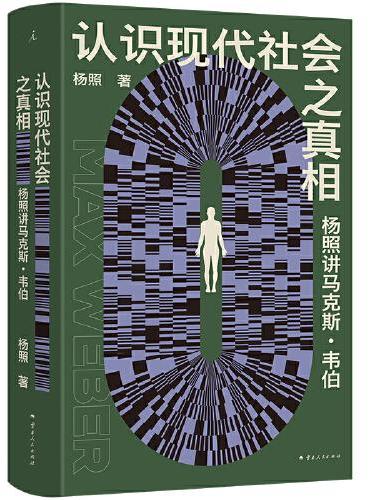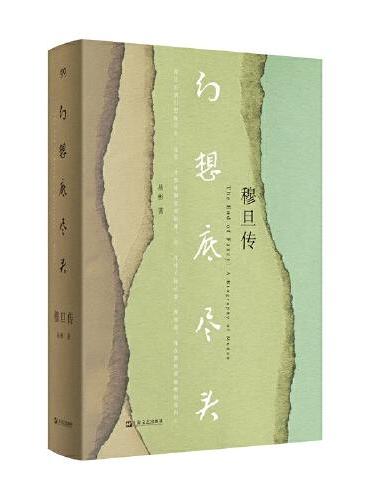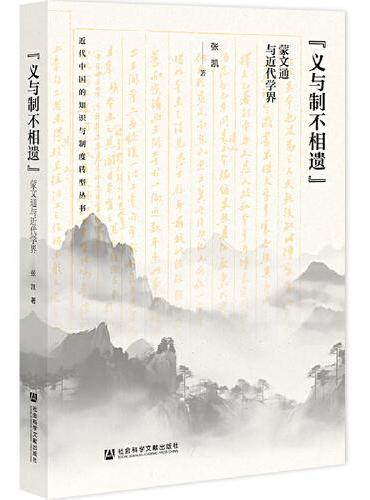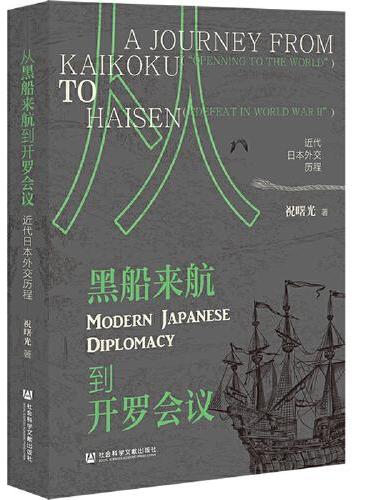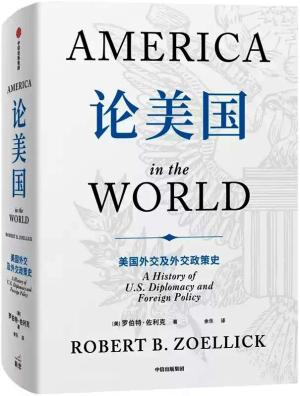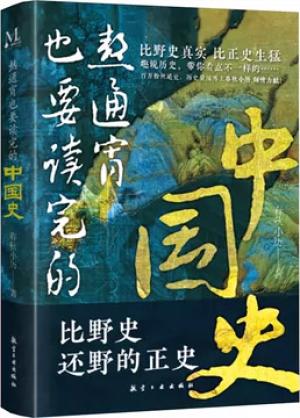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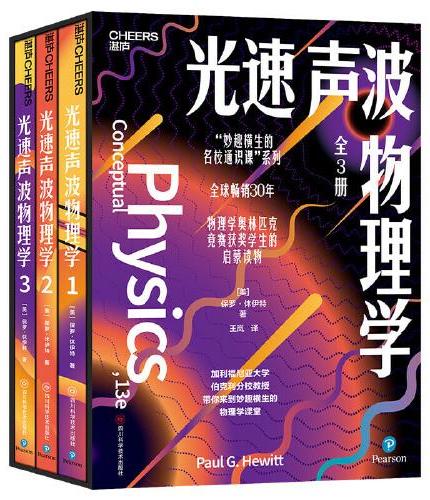
《
光速声波物理学. 1、2、3
》
售價:HK$
4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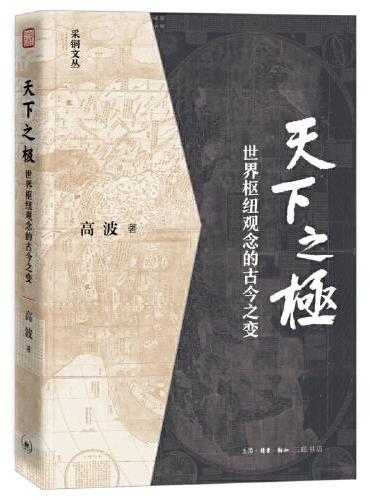
《
天下之极:世界枢纽观念的古今之变
》
售價:HK$
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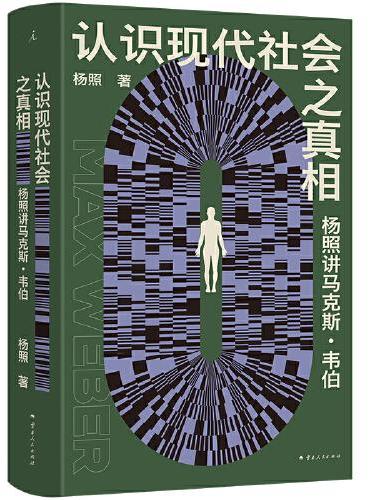
《
认识现代社会之真相:杨照讲马克斯·韦伯
》
售價:HK$
9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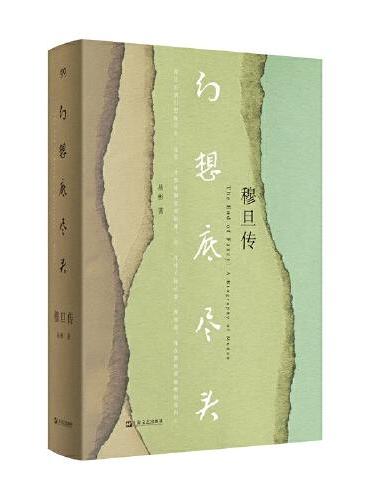
《
幻想底尽头:穆旦传(《穆旦年谱》编撰者历时二十余年心血之作,基于《穆旦评传》精心修订,文献翔实可靠,完整讲述了一位中国诗人与翻译家并不平顺的一生。)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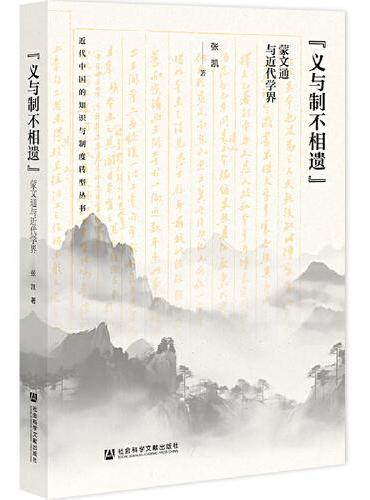
《
“义与制不相遗”:蒙文通与近代学界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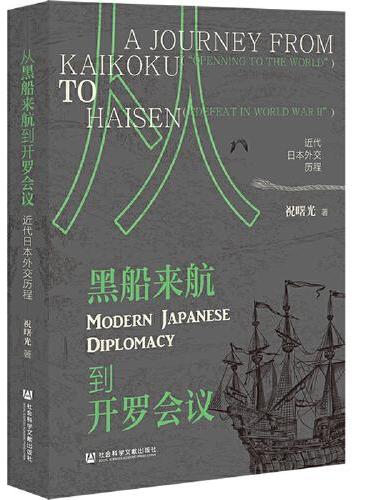
《
从黑船来航到开罗会议:近代日本外交历程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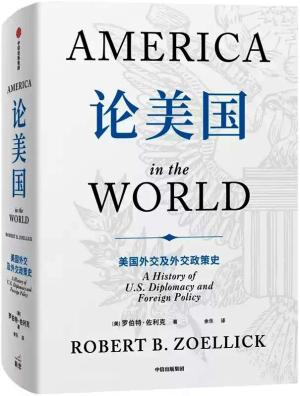
《
论美国(附赠解读手册)
》
售價:HK$
14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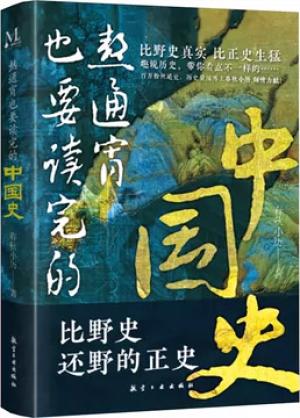
《
熬通宵也要读完的中国史
》
售價:HK$
74.8
|
| 編輯推薦: |
《芝加哥书评》2018年“自然写作奖”
《科学星期五》2018年“科学书籍”
Buzzfeed 2018年“书籍”
2019年环境记者协会“蕾切尔?卡森环境图书奖”
入围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院和工程通信奖”
《寻找金丝雀树》将科学与信仰完美结合,探索边疆与文明、荒野与社会之间的断层,诉说人类与自然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北美金柏无形的价值无可取代,森林给了人以身份,以“联系”替代“资源”才能使自然和人类重新成为彼此的一部分。
|
| 內容簡介: |
早年间,矿工将金丝雀带到矿井中来判断井中是否有一氧化碳泄漏。因此,现代人用“金丝雀”指代环境中的指示性物种。
在阿拉斯加,濒临死亡的北美金柏便是当地人的“金丝雀树”。为了找出这一金丝雀树所揭示的环境变化,奥克斯和她的团队在阿拉斯加偏远的沿海进行了艰苦的实地考察——书中用积极的文字重现了科学考察的真实场景;此外,她还采访了当地人,以探讨北美金柏对当地的经济、生活、精神各领域的深刻意义,及当它灭绝时森林和居民会如何应对一系列的变化。
奥克斯深信,应对环境变化造成的生态影响,科学研究要和当地人的行动联系在一起,并“在绝望中保持乐观”。
|
| 關於作者: |
劳伦?E.奥克斯,一名生态学家、作家和教育家。她是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气候适应项目的环境保护科学家,斯坦福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的兼职教授。劳伦教授关于科学故事讲述技巧以及大学科学传播课程。她于2015年获得斯坦福大学埃米特环境与资源跨学科项目博士学位,2004年获得布朗大学环境研究与视觉艺术学士学位。她的森林相关研究已经被《大西洋月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科学美国人》《科学星期五》《赫芬顿邮报》《户外杂志》《史密森尼》和其他媒体报道过。她曾为《纽约时报》和《国家地理》的“开放探索者”撰稿,并联合制作了《红色黄金》和《阿拉斯加黄金》两部环境题材纪录片。
译者简介:
李可欣,同济大学风景园林硕士,四川德阳人。
|
| 目錄:
|
序
部分 慢燃
引子
章 魂灵与墓场
第二章 伫立
第三章 气候变化中的森林与恐惧
第四章 解谜
第五章 倒数
第二部分 鸟歌
第六章 欣欣向荣
第七章 为人垂涎
第八章 分隔与归属
第九章 饱和点
第三部分 明日
第十章 度量与无量
第十一章 的机会
第十二章 哨兵
后记
致谢
注释
延伸阅读
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探寻自然的秩序,重建我们与万物的联系
关注自然,便是关注我们地球和人类自身的未来。所以当 “绿水青山”成为这个时代的强音,建设生态文明成为国家的主旋律时,我们更需要从思想层面建立对自然的认知,进而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未来发展的进路。这便是“自然文库”存在的意义。
具体而言,自然文库关注历史上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与方式,注重现实中环境与世界观的相互作用,此外,亦会抛开宏大的叙事,将个人纳入到生命网络中去讲述自然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仰望星空、俯首大地的意义,进而让我们的心灵得以安放,让忙碌的城市生活变得生动而鲜明。只有“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内化为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就自然展开的思辨就会越深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就会越光明。
部分 慢 燃
发现未注意之美的办法之一是自问:
“如果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会怎样?
如果这是我再不得见的会怎样?”
——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引子
2015 年 3 月 4 号,斯坦福大学。我面前坐着一百多号人,有同事、 朋友和家人。我的博士答辩:成为持证科学家—扔掉“女士”“小姐”(或者某天:“太太”),换上“博士”—路上的后一道坎。我以为通过答辩将令我如释重负,能给我更大的自由感来开启我的科学事业,而结果却并非如此。
在我们今日对气候变化真实而可度量的理解出现前许多年,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便提出“生态学教育带来的一大后果是人仿佛在一个充满创伤的世界中孑然求生”。然而今日的新闻将这一后果带给了更广的受众——它以一系列大标题描绘出一幅骇人的未来图景:“异常气候遍袭世界”“格陵兰岛在短短4年之间冰量骤减一万亿吨”“大洋变暖超乎人之所见”“我们正死于气候变化”。 如果知道我们当前的气候轨迹、接受这一事实,我想不论科学家还是普通市民都会困惑:我们能做些什么?在这一骇人的末日 感中,我们要怎样更好地活着?
花费六年时间研究气候变化的影响——对森林跟依森林而存的人——在我个人意味着什么,我先前并未考虑太多。我从未想过加入这一小小的竞争圈子意味着什么——这圈子由活在这一创伤世界中、受过高度训练的科学家组成——以及寻到前路需要付出些什么。
一切都始自我2010年时的那个问题:在北美金柏死后,森林将如何发展?——当时的我以为解答会很简单。较之一些同事所计划的预测气候变化跟旱情(这些是我认为科学上难的选题,就其对人类的潜在影响而言也是黑暗的),我其实认为自己的问题相当乐观。 我想了解在失丧跟变迁间有些什么物种还能生长繁荣,我们所形成的环境有什么样的生命能耐受,以及如何跟为何。这一问题始自一片与世隔绝的海岸,继而展开于遍布阿拉斯加东南的众群落。乘艇或步行,我花费数月去到散布于数英里长的崎岖海岸线上的一处处森林,循着 我的求索,来到猎人、博物学家和当地织工的离网的家,来到曾负责清伐这处美国的国家森林原生林的守林人的小屋。我指望记录影响,但也是在为一个看似难解的问题寻找解答。
博士生涯开始前,我从未料到自己会沉迷于单单一种针叶树,更不用说这一种还长在亚历山大群岛。事实上,我一直认为将数年时 间单单投注于一种物种的科学家们相当古怪(可能因此我早已命中 注定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请别误会,北美金柏(Callitropsis nootkatensis)将会是你沉迷某一树种的绝佳选择。
北美金柏形态壮美,体形巨大,与其他柏科植物——比如西内华达山脉(Sierras)的巨杉(sequoia)跟智利沿海山脉参天的山达木 (alerce)——有亲缘关系。然而零星分布于诸斑块跟小区域中的北美金柏却在数百甚至数千年间未受太平洋西北岸变化的影响。原因无人确知。每棵树的年轮中都记录着丰年跟灾年。北美金柏的树心记载了一段漫长的生命事件历史,人眼虽然可见,但唯有科学能解。
1879年,博物学家约翰·缪尔(John Muir)从加利福尼亚前往阿拉斯加,其时他在日记中为北美金柏作了速写,称其“羽毛般的”枝干“分成美丽的浅绿色小枝”。在数千年间,当地人用树皮纺织,用木材制作图腾柱和艇桨,与此树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今天,北美金柏仍是太平洋西北岸经济价值的树种之一。
北美金柏迷人、优美且有益人类,但其成为我研究中心的原因,却在于这一历经沧海而存活于今的树种正在大片地死亡。
已知早的死亡斑块报告来自一位名叫查尔斯·谢尔顿(Charles Sheldon)的猎人,他于1909年在沼泽地区注意到了死亡斑块。到20世纪末,科学家观察到高比率的树木死亡引起了阿拉斯加人的关注。在我开始博士研究之时,由保罗·埃农博士领导的一组研究人 员刚刚发现了导致北美金柏死亡的罪魁祸首:气候变化。
靠近两极的地方变暖的速度更快。20世纪中期开始,阿拉斯加 的升温幅度达到了全球平均的两倍。气候变暖同其全部后果一道, 已经成为阿拉斯加人的切身经验—现实、当下。故而我追求的并非为北美金柏而研究北美金柏,对于生态过程跟种族进化的单纯好奇心于我尚不足够,我不想止步于发现。同多数环境科学家一样,我想要解决问题。我想着,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在全球接踵而至,阿拉斯加人如何应对变化的环境、应对失去这种壮美的树,说不定能令我望到自己的未来——望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长期以来,变化的景观令我着迷且关注。年少时我便喜欢用相机镜头定格人与自然间的复杂关系。14岁那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祖父的柯达雷汀娜相机,一件20世纪50年代的古董。我家后院一棵老枫树的照片填满了我初的相册。照片记录着树身上因修剪留下的伤 痕:一次次地,树形由此慢慢被重塑。后来,拿着父亲的35毫米奥林巴斯,我拍下割裂田地的道路、花园中修剪整齐的灌木、裸露方形土壤上栽着瘦弱树木的城市人行道。我着迷于人们如何改变自然世界, 我的整个二十多岁都为其所引领,从一处被改变的环境到另一处。
在罗德岛,我追溯过街道造成的水污染;在美国西部,我目睹了为油气开发所改变的群落和沙漠景观;在阿拉斯加西南原始流域,我直面过采矿业的发展;在智利温带森林,我遭遇过公路建设。我曾是环保倡导者、纪录片制作者和政策研究者。但为了学习如何更精确地、 系统地评价环境变化的后果,我决定成为一名科学家。现在看来,出乎意料地攫住了我这个年轻科学家的那棵柏树,大约在当年后院那棵枫树身上便早有预兆。
北上阿拉斯加时,我内心的问题在于绝望和希望。是否我们都该承认战败、举手投降?有没有谁能做些什么真正带来改变?什么能带来改变?随着对气候变化认识的增长,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也在日增。世界变暖的图景似乎压倒一切、庞大而超乎我们的控制。气温预测描绘着一个在未来数十年间慢慢变红的星球。科学家们今日所展示的图表、数字、复杂模型还有统计,差不多都异口同声:“已经太迟了。”即便我们停止一切排放、在我们创造的生活节奏中来个急停,仍然太迟了。灾难的轨迹仍将沿着巨浪般的弧线推进,直到击中我们。
但从2010年到2015年——通向我在斯坦福答辩的那些年——我却活在谨慎的希望中。我研究当北美金柏死后森林群落内其他植物会何去何从,以及阿拉斯加人如何适应当地环境的变化。在外岸,我见到许多死树,但即便在受到回枯影响的森林中,我也找到了幸存者。 是什么令这些特定的北美金柏存活下来,又是什么令别的树种取而代之?数据和观察为我提供了一些答案,其余事实则只能从熟知森林的人们那里获知。
我的研究是生态与社会科学的糅合。同人交谈的重要性对我而言不亚于测量植物跟记录温度数据。当然,跟所有同事一样,我提出假设并借由系统方法寻找答案,但作为一个人,生存于面对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各样威胁的世界中,我也以出于个人的恐惧感跟无助感的方式 求索着。关于此,我到现在为止还没太谈到。科学家的训练要求我们不偏不倚且精确,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掺入个人因素。这与研究过程的全部错综复杂一道被藏在黑匣子中。
在科学意义上,我确实有所发现。通过对崎岖外岸沿线的数千植物进行测量,我发现森林正在复兴。通过对珍视这种树的阿拉斯加人进行深入采访,我发现这一人类社群正在与形成中的环境建立新关系。答辩当天,我展示了一系列表格跟图表,详细表现人们如何以种种方式回应树的死亡、应对变化。人们找到了北美金柏的替代品,发展出利用死树的途径。面对挫败,他们在寻找机会,尝试恢复与创新。
我的研究已经在一本科学期刊上得到发表,更多论文也行将付梓。但还缺少些什么。在精心提炼简洁、科学的语言时,人性的要素被我剥除尽净。
“测量2064株成年树与882株幼苗。”短短一句话、两个数,省略了我长达数月的个人经历—在这些死树间我如何生存跟感受, 如何倾听与呼吸。当1500页采访记录被提炼成一张简洁的表,一个伐木工如何满怀欣赏地以生满老茧的手拂过纹理细致的木材,以及当 一个阿拉斯加人讲述一棵壮美的北美金柏时整个房间是如何地安静都被我略而不提。从格雷格·史翠夫勒(Greg Streveler)这样的博物学家、泰瑞·洛夫加(Teri Rofkar)这样的特林吉特土著或者韦斯·泰勒(Wes Tyler)这样的伐木工那儿听来的故事——在失去一种曾为自己所用、所珍视、所爱的树种的同时,这些人找到了从形成的环境中获益的方法也被我删减。
当被要求描述北美金柏时,人们会用这样一些词打破令人肃然起敬的沉默:气味甜美、罕见、美丽、迷人、令人屏息、强健、刚毅、 性感、神秘、智慧。一个特林吉特土著曾向我解释与自然建立紧密关系——那种多数人只会同另一个人建立的关系——如何令人获得应对 变化的能力。科学中没有这类细节的容身之处,我只得将她传神达意 的话翻成数据点。在分析中我忠实于她所分享的,在解读中我保持客观,但研究过程掩埋了本质。
我在答辩前对 PhD“答辩”所知甚少。这一过程因体制跟国家而有所不同,但大体要旨是一致的:年轻科学家公开展示自己的研究,应对常规提问,接着进入与前辈科学家的一对一问答环节,由后者判断研究的价值。完成这全套环节过后,我在答辩室外的走廊独自踱步, 等待审议决定。
当委员会请我回答辩室并次称我为奥克斯博士时,我惊讶于自己并未感到解脱。是,我感到释怀,但并非我所预料的解脱。相反,有一种噬心的紧迫感:有更多需要我做的。有些事情还未解决—有 些更个人的而非科学的事情。
为在高层科学家中间获得一席之地,我曾加倍努力,但我同样需要让自己的工作走出专业的回音室。尽管已经为自己的研究写下的233页成果即将签名、盖章并提交,然而我知道为现在这本书我还会写出同等的页数。结束答辩后不久,我回到办公室,带着一箱日记和纸, 开始将数年的笔记数字化,让被掩埋的本质复活,为我自己寻找解答:今日,靠着我所学到的,如何能在这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得好?
这里记下的便是当时未得讲述的故事。
本书的主题是名为北美金柏的一种树,我在其魅力之中的所感,以及我如何为其所激励而开始探索那些在变化中生长繁荣的人跟植物。书中记录着我追踪北美金柏之死的努力:不仅仅为了揭示那些原始森林的未来,也是为了将适用于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们的经验教训 分享出去。本书的主题是寻获信仰,不是宗教意义上的,而是针对全球问题在地方层面寻求解决方案的某种力量,这种力量令我能喜乐地活着,并在仿佛暗昧的时期着眼于重要的事。我们若能开始着眼于地方图景、着眼于我们每日依靠自然而活的种种方式,解答便浮现出 来。在阿拉斯加,我见到了这一切。
我祖父的老柯达躺在一个塑料储存盒中,已经多年未用,而我带到外岸拍摄古木的相机同它毫无相似之处。大量电子文件跟缩略图取代了胶卷和相簿。我依然关注树和景观变化,但同样地,我也有所改变。在整个人生当中,我们形成叙事,又进行改写,以理解所发生的; 我们处理经验;我们随着生活的展开而阐释自己的世界观并再度阐释。 我相信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这一美好而艰难的过程。故而,虽然本书的叙事脱胎于我所做的研究,但其后数年的写作和报告也同样属于这趟旅程。我如何解释研究开始时我所得知的(和我所不知道的)跟 自那以后又添加的细节,都为我今日的科学家身份所影响。我个人曾如何应对工作中出现的挑战,以及我从自己的众多访谈对象那里学到的,则引导我选择在此处呈现的至为尖锐的事件和交谈。
作 家、 环 保 主 义 者 和 历 史 学 家 华 莱 士· 斯 蒂 格 纳(Wallace Stegner)曾经写道:“如果艺术是生活的副产品,而我相信如此,那么我想要自己的努力尽可能贴近土地跟人类经验——而我所了解的一片土地就是我所居的那一片,我所能确定的一份人类经验 就是我自己的那一份。”往返于加州和亚历山大群岛的这些年间,科研上,我尽可能密切地关注这一变化的世界;而情感上,我关注经验所引发的斗争。我在个人生活中遭遇失去又找到前行之路,这一过程令我发现了科学之事与个人之事的相似之处。
科学事实依赖假设,像砖一样一块垒在另一块上面。但我在群岛 学到的却基于一种混合,其中半是科学,半是进行这项工作的行动,也即在切身经验中尽力抵达下一个层面的理解。我们所感受跟获知的个人真实是短暂易逝的,因为我们从自己的人生中构建叙事景观,一遍一遍又一遍。这便是此刻的我,在一个某些人会认为注定将变得不 宜居住的世界中,寻找着抵达明天的路。这是一个驱散我个人恐惧的故事:恐惧在于一个变暖的世界在我有生之年中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出乎意料地成为乐观主义者的故事:在正死去的森林这一背景下、 在悲观主义已是惯常的一个专业中。
一些细节
这是一部非虚构作品。人物、地点和事件都是真实的,我在斯坦福大学期间于阿拉斯加西南开展的研究令我与他们结缘。人名均未改动,只是在保罗·埃农博士之后出现的每位保罗都得到了一个绰号。保罗·埃农博士就是那位将气候变化与死树联系起来的领头科学家。 有些人的绰号是在我们合作期间形成的,比如保罗·“P 鱼”·费舍尔(Paul “P-Fisch” Fischer)。另外一些保罗的绰号则仅仅是我写作此书时单方面发明的。森林病理学家保罗·埃农博士,野外技师保罗·费舍尔,森林生态学家保罗·阿拉巴克(Alaback)博士,植 物生理学家保罗·史嘉柏(Schaberg)博士,猎熊向导保罗·约翰逊 (Johnson)——在一片鲜为人知的森林中竟有这么多保罗,这几率能有多大呢?如果我管他们都叫保罗,你肯定会在一片突发的混乱之中停止阅读的。
我以年轻科学家的身份见过跟合作过的人当中,许多可能从没想过我会写出什么学术论文以外的东西,或者他们的名字连同我们的专业经验一道,会得以出版。我尽我所能地对人物、事件做了精确的呈现,基于数千页的野外笔记、记录、研究论文、邮件记录、信件和日 记,其中有我自己的,也有各位野外技师的分享。科学家们经常会提前告知我研究结果,远远早于终发表。同样地,有时我会描述他们的研究,忠于事件发生的先后而早于终发表。有些交谈我重构自笔记和记忆,继而像记者会做的那样进行核实。有可能时,我重访当时在场的人,协调不同视角,尽力实现精确的谈话复述和事件描述。
我为博士研究所采访的45位阿拉斯加人同意参与这项科学研究,他们清楚对自己的观点的报告将是匿名的、以数据点跟摘录的形式,以及某天,可能会以书的形式得到发表—届时他们的个人特征将得到全面呈现而能够辨识。我感谢他们的信任和殷勤,也感谢他们提供 这扇望向他们生活的窗。他们中有些人为我敞开了办公室,另一些为我敞开了自己家的门,令我在远地荒村得以容身。他们中有些我耐心等候数日方得一见,另一些则与我共度多日。
出于长度考虑,有时为着内容更清晰,我在直接引用谈话记录和转写时对其进行了编辑。鉴于每次正式访谈的可观长度,为着叙述而对谈话进行简缩是难以避免的。
这些访谈是在斯坦福大学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完全认可下进行的。由该委员会负责的审查程序旨在保护各项研究中涉及人员的权利和福利。IRB的用词是“人类研究对象”,但我从没把采访过的任何人当成研究对象。我接触每一个人时,都半是作为科学家,半是作为关切的市民——在旅居中且寻求着智慧的建议,向着可能刚好针对一个邪恶的问题找到了解决之道的某人。我是否—不论在他们的话还是我的研究中——找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终极解决方案?并没有。但是我确实找到了些什么—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目标,并令我们 每个人在当下更加有目的地生活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