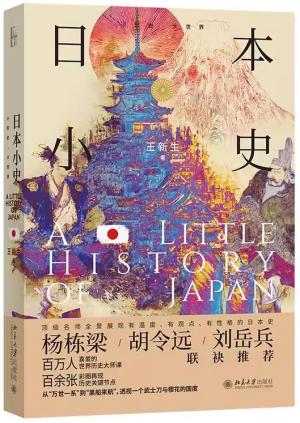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俄国在中亚 地缘政治原典级著作
》
售價:HK$
107.8

《
索恩丛书·汉娜·阿伦特:20世纪思想家
》
售價:HK$
75.9

《
“节”与“殉”——八旗制度下的妇女生活与婚姻 中华学术·有道
》
售價:HK$
83.6

《
城市群高铁网络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与规划应对
》
售價:HK$
108.9

《
古代教坊与文学艺术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全两册)
》
售價:HK$
38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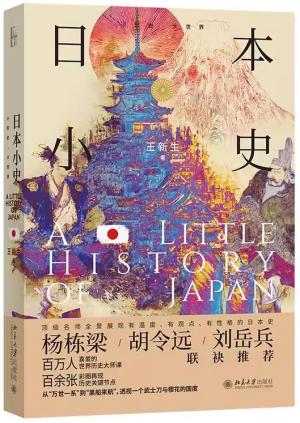
《
(小历史大世界)日本小史
》
售價:HK$
86.9

《
慢慢变成大人 一部颠覆传统教育观的权威指南 驳斥传统育儿观念,直击教育核心 直面儿童成长中的深层议题
》
售價:HK$
75.9

《
口腔临床病例精粹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旧荒诞的遗址,新喜剧的未来
谭越森短篇小说集
寓言 讽刺 幻想 玩笑 荒诞 黑色 喜剧 现实 科幻 超现实
何谓幽默和讽刺?真正的幽默是绝望之后的幽默,真正的讽刺是生死无谓的讽刺。讽刺小说,就是抽干沼泽地的艺术。
——谭越森
|
| 內容簡介: |
《收藏家》是谭越森短篇小说集,这部作品以其一贯的冒险精神,体现了辽阔的叛逆和展示综合文体的能力。他的小说是世俗的,也是反诗性的:《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是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反乌托邦小说;《坏种老头》以俏皮的语言、玩笑的戏谑,记录了一个特定时空的悲惨往事;《少年》则通过辛辣的讽刺,摧毁了精神的乌托邦和虚假的诗意的居处。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在普遍流行苦咖啡文学的时下,《收藏家》提供了另一种文学视域,一种新的可能性。无论是文本的开拓性,还是小说风格的多样化,从戏谑到讽刺,从严峻到荒诞,从现实世界到软科幻,他的语言幽默、幽冷、幽暗,犹如在穿越层层迷阵中寻找真实的审美向度。
|
| 關於作者: |
|
谭越森,男,七十年代出生。他的小说介于贝克特与卡夫卡之间,小说先锋特征被喻为“旧荒诞的遗址与新喜剧的未来”。
|
| 目錄:
|
目 录
诗人与丧尸 1
雪一样不存在的城市 35
鳃盖 72
幽冥 81
背负沉睡的人 107
坏种老头 112
保姆 131
一生吃苦有什么用 136
偷小孩的老妇人 140
阵雨 149
劫匪 159
怒火攻心 203
少年 214
春播大战 256
死手怪谈 262
恐怖包子故事 292
提线娃娃 297
猴子和异乡人 304
汽车公墓 309
|
| 內容試閱:
|
序
我们的时代如此之丰富,反而让小说家的笔调不知所措;我们的时代如此之单调,更加让小说家的笔调不知所措。福柯说:“人终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在这个时代,人没有被抹去,但被遮蔽;人没有被抹去,但被击成碎片。长篇小说越来越难以表达这个碎片化和被技术遮蔽的时代,不仅显得力不从心,而且往往昨是今非。由此,我越来越倾向于具有捕捉和截取能力的短篇小说艺术。
一个小说家,就是对同时代的人性碎片的收藏(本书书名由来),也是对历史的缺憾的补充。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世上所有的事情,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灵魂图景。
小说的常态是写梦,非常态才是写现实。如果一部号称现实主义的作品没有让你产生眩晕感和觉醒,那么这部小说仍然在写梦——我没有指非虚构作品。从梦中醒来,推开房门,是继续走向梦,还是走向我们感知到的世界,通常谓之真实的
世界?
是尼采的真实?塞利纳的真实?卡夫卡的真实?布尔加科夫的真实?海德格尔的真实?汉娜·阿伦特说,如果人们不知道一个时代的整个政治光谱,不能区分不同国家的基本状况,不同的发展阶段、传统、生产类型和等级、技术、心智等等,那么,他们也就不知道如何在这领域中行事和表态。人们只会将世界打得粉碎,以至于到后只剩下—件事——纯粹的
黑。① 还是哈维尔的“活在真实中的真实”?文学的真实?哲学的真实?人心的真实?什么是真实?鲁迅抵达过部分的真实,王小波也抵达过部分的真实。什么是文学的真实?就是如在梦中被人指出你在梦中时的那种悚然而惊的真实。
非虚构并不能够表达真实。况且虚构的真实,能抵达一部分就可以了。虚妄全部的真实往往是失败的。
小说,体现了辽阔的叛逆和展示综合文体的能力。小说是世俗的,也是反世俗的。它没有价值,因为基于自由这一永恒和至上的铁律,它不能制定价值,只能谦卑——谦卑是它了不起的存在根本。它是器,如同我们无法挣脱的生物本能,困于肉身的体制;它是道,可以建造精神的乌托邦和实现诗意的居处。它有原则,自由和审美严肃的判别;它没有原则,因它不可控,它是超越性的存在。任何束缚自由的工具,它必然加以嘲讽和唾弃;而对于一切美好事物的追寻,则证实了它的力量。它能体现文学的精神——捍卫人性自由,以及对世俗永不停息的冒犯。
小说家介于诗人和哲学家之间,他永远无法自信,他只能怀疑和谦让。偶尔,他还要充当诗人、戏剧家、散文家或时评写手,他必须牢牢与时代保持一种紧张关系,即他需要确立自身所处的位置,同时担负他身处的时代所有的苦与无常。
小说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对作者来说,一旦完成了它,它会寻找一个属于自身轨道的世界。而对读者来说,它会继续在不同的人心中形成它的力量,它的世界。佛家说,十界互具。一部小说,它同样具有如此的规模和无限的心性。
小说总会体现一种“失控”感。在我们的历史长河中,在我们的美学经历中,在我们所了解的政治哲学,以及我们身处的世俗社会(即赖以轮回之基点),小说以它的方式,或嘲讽或怜悯,或预见或回溯,或摧毁或建构等力量介入,来为我们的庸常生活、我们的政治生存提供不同的答案,告诉我们:我们本可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或:历史不是这样的,政治也非如此。我们无非囿于各自的偏见中。事实上,转识成智方可让你获得通行世界的钥匙。
小说,只有打破习常的世俗之见,让你“失控”,你才能真正触碰到“真实”。
这些足够了吗?并没有。这只是一种显性的世界,还有更多的世界(比如隐性的世界)存在。我们所说的因与果,即生成或灭坏构成的秩序。六因迥异,果实各有不同,呈现方式亦为分别。
对小说家来说,一部小说完结得恰到好处,是一种创作的惰性和意志的匮乏,因为杰出的小说往往是绝地求生,穷尽它的可能性。那些说当代文学某某作品可以传世,皆为虚妄之言。一个小说家,只有在确立自己所处的历史、政治的位置,他才会真正了解自身写作的所有问题。一个作家的错误在于把虚妄当成实在,把实在当成虚妄。
小说,从来不是才子的事业。
……可是他
必须挣脱出少年气盛的才分
而学会朴实和笨拙,学会做大家
都以为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
因为要达到他的的愿望,
他就得变成了绝顶的厌烦,得遭受
俗气的病痛,像爱情;得在公道场
公道,在龌龊堆里也龌龊个够;
而在他自己脆弱的一身中,他必须
尽可能隐受人类所有的委屈。①
小说家,就是在人群中全然不值得一顾的一种人,包括忍耐和隐受。
汽车公墓
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不能如愿,一是如愿。
——萧伯纳
一
我站在荒漠,朝着黄沙堆撒了一泡尿。滋起沙土冒了一小阵蒸汽,辽阔的地平线晃动着,扭动着,生气勃勃,我分明感受到自己的尿气里有种畜生的味道,这让我十分振奋。不远处,一座座汽车垒起来的庞大公墓群隐隐约约地现身,当我每走一步,就能得到一座公墓群的轮廊,更加让我兴奋不已。这里是全球集中的污人居住地。高智民称居住在这里的人为污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一个异端分子,被驱逐者,现在正在投靠污人,也谈不上是投靠,因为我很明白,我与他们并无不同之处,本来就是一回事儿的人。我在到达之前,已经做好了决裂之选,生死无凭,只能听天由命罢。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我一无所有,除了怀里揣了本破书——《庄子》外,双手空空,一个人走了这么多天,浑身发臭。我闻到前方一股恶心腐臭,仿佛与我身上的气味暗暗押韵。那气味还夹杂着一些莫名的像是工业塑料燃烧的气味,呛人鼻息。
“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天色浑浊不堪,像股陈尿,泛着污黄色,我念着庄子这句话,是因为就要见到老张了。
一辆载着七八个人的绿色吉普车驰了过来。从车上跳下一个身材中等的中年男人,胡子拉碴,穿着土黄色的迷彩服。他一见到我,露出满嘴黑牙。不错,他就是老张,我们污人反抗军首领。我没有想到,他能来亲自迎接我这个流浪汉,心里十分激动。
——一切都是他们逼的,把我们赶到死人地。没有能源,没有网络,什么都没有,除了死人,那些废烂汽车上的尸骨,我们和他们的亲人皆葬于此。老张说道。
——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对抗他们的暴政。那些高智民,随意改变基因从而变得强大又冷血的一群畜生。
——他们胸膛里装的一定不是人心,一定不是的。如果是,他们为何不把我们当成人看?哪怕当一点点的人看也好。
我一边听着老张说话,一边看着车窗外。那些一堆接着一堆的汽车墓群,锈迹斑驳,品牌不同,车身颜色各异,一个接着一个折叠或焊接而垒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或造型怪诞,或中规中矩。那些以前载过很早的人,驰骋过这个独立星球任何一个地方的车辆,如今全然沉寂,全都变成了废品,变成了一个个骨灰盒,装着死人尸骸(完整的或不完整的、几个或一个、混杂一起的、拼凑在一起的人体骨骼)的棺材,结构恢宏的体系。墓群有高三十米或五十米,也有高过百米的。我看不到尽头,这幅庞大的景象,简直无与伦比。但我能感受到那里面的死灵像活物,有种说不出来的恐怖气息,就像进了死神的领地。绝望或者别的,或者没有别的。
——他们胸膛里装的一定不是人心,一定不是的。如果是,他们为何不把我们当成人看?哪怕当一点点的人看也好。老张重复着这句话。我看到他的脸色如同排便困难时憋出的痛苦可怜相,而目光散乱,又像个孩子。
车的速度缓慢下来,墓群越来越密集。有街道了,许多人站在街旁在看着我们。看来,我们这辆车可能是公墓里为数不多的能行驶的车辆——我没有看到其他能动的。汽车绕来绕去,像在黑沉沉的大都市中穿梭过。偶尔能看到灯光,但很少,还有零散的小火堆,以及玩耍的小孩子们。车接近他们时,他们大喊:“老张,老张来了。”公墓中的建筑物大部分场域是黑魆魆的,高大的黑,以及尸臭味。到处散发着阵阵浓郁的尸臭,像是排泄物。人死了,也许就是一种排泄。
更为庞大的建筑群,应该是汽车墓群耸立眼前。我抬头望上去,一堆漆黑入云。一百米高?两百米高?老张看着我歪着脖子,笑眯眯地说,在我们汽车公墓里,这是的,足有五百米高,没人数得过来是由多少辆汽车垒起来的。“是不是?”老张问他左边的一个“战士”,那个战士连忙点点头,回复道:“我小时候就在这里数,一直数,数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超一号到底是由多少辆车垒起来的。”
没有能源,没有网络,确切地说,没有高智民那种通天达地、高度发达的粒子网络。老张究竟靠什么来反抗高智民,并且坚持这么多年?而且环境是如此糟糕,空气中充满着尸臭,一呼一吸都是恶心的死尸味道。连睡梦都是如此?我心里充满着疑惑。
阴道炎的味道?龟头囊肿的味道?扔掉的烂裤头?口臭?臭鸡蛋?我能感觉到我的颅骨在飞翔。
甚至是一个小人。我会突然忘掉它,然后走着走着就发现身后有它在追随,猛地一转身,就看到它。
从作战部走了出来,超一号地下洞穴里,我在一个士兵的带领下,穿越一个挨着一个的洞穴,继续往里走。气味并不因为在地层下会有所减弱,而且越发地怪异。我只要深深地吸上一口恶臭的空气,便明显能听到自己的肠胃发出狂暴的咆哮。一阵之后,我的胃默默地收缩,食物混合着胃酸在冲向喉管——造反!我屏住呼吸(实则自欺欺人而已),狂按住嘴巴,对造反的胃进行宣教、镇压,镇压、宣教。
编号一三八的洞口传来一团混杂的声音:打酣声、哭喊声、叫骂声、小孩笑声,以及妇人的低泣声。士兵对着已经脸色煞白的我说:“谭先生,到了。”我忍不住转身问士兵:“为何老张对我这么个流浪汉待遇这么好?”我是指他居然亲自迎接我。
——以前不是这样的。现在很少有人会往我们这边来的,简直是稀罕事物。再说,我们这边尸臭从早到晚,无所不在,吃的、住的、喝的、聊天瞎扯、睡觉做梦,还有啪啪,无时无刻不让那该死的臭味熏来熏去。人被熏傻了,人人一副傻逼模样。需要新的人来冲冲这晦气,铺天盖地的晦气。
——重要的,我们相信,刚来的人肯定比我们聪明。至于以后……士兵突然间露出神秘的奸笑。
——嘿嘿,都会成一个傻样。
他得意地说完,沉浸在对自己的言语出色表达的欣赏中,一会儿又沮丧地说:
——谭先生,你看我现在这模样,傻不傻?
我和士兵一起绕过地下竖七横八睡的人,靠洞穴里头,有微暗的光。士兵说,到了。
躺在黑污污的棉被上,洞穴从地到顶有五米高,是家庭或者单个人,用各种布(塑料布、棉布以及像布的材料)相互之间隔开。人声回旋在其间,我注意到离我有十多米的地方,好几个人在盯着我看。我从背包里取出烟叶,卷了一根,吸了起来。这样的举动引起一阵哗然,几个人走了过来。
我出了冷汗。
“这是一场发着恶臭的噩梦啊。”
二
一切要从“上帝重塑人类计划”开始。
我的童年,我的噩梦。
我见到过于丑恶的东西,太多的丑恶。这个独立的星球,再也没有任何生物像人类那样丑恶了,萦绕我整个人生。我多么想自己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终其一生该多好啊!
上帝没有死,而且上帝很民主。据说,一天上帝良心发现,决定问问人类,他创造的这些智能生物对自己还满意吗?得知上帝居然放下身段来问,注定是“尘归尘,土归土”的卑贱的人类一时惊喜若狂,自此潘多拉魔盒算是打开了。人的问题就是太容易坏掉了,脆弱不堪,完全是上帝造的劣等货。作为地球高等智能生物,肉身强壮不及大象,奔跑不及虎狼,生殖器不及……鼻涕虫,那小小东西,生殖器可达身长几十倍,一次交配时间长可达数天呢。干吗要造那么多东西?先把自身打造好,就不用费脑子制造工具来弥补自身不足。
人类觉得,上帝应该把造人的能力归还过来。这么多年一直受到上帝的独裁,简直就是毒咒。而上帝也正有此想——把自由归还给人类,自己不再多管闲事,有时间多泡泡妞什么的。反正浩渺的宇宙中不止他一个。
一时间,人类疯狂起来了。“上帝重塑人类计划”正式展开,各国陷入了混乱时期,基因改造就像太阳能一样普及众生。人人都尝试改造自己的基因。有利的,当然是那些有钱人,社会上有头有脸,买得起奢侈品就能买得起基因改造技术,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改的人,直到把自己改造得完全不是人样为止。
我们的街道,突然变得丰富而怪异起来,平时那些有钱人,即人生赢家们,以瞠目结舌的模样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正走在街道上,不时就从眼前掠过一个长着大翅膀的胖子腾空而起,在离地五十米的高处得意地大笑,引起一群人仰视。人群中喊道:高董事,你太厉害了。不一会儿,一个长着八条腿的怪物掠面而过,人们还未看清是谁,只听到“你们猜啊猜”的声音。一个庞大的大甲虫横行无忌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说没有任何东西能让他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于是就有人拿棍棒、刀具,在大甲虫身上乱打乱砍,只听到像碰到了钢铁一般的闷响,而大甲虫毫发无损。
还有些怪物浑身发光,像个巨大的手电筒,直立地行走。
越来越多的富人变成了怪物。这些怪物从一开始的好玩,到后来越来越变得暴力。
它们白天食人,晚上宣淫。
我父亲不再上班,留在家里,把家里的门窗全部钉死,周围的邻居也是如此。不被攻击只能算是侥幸,许多人都被怪物们生吞活剥了。政府下达命令,授权军队对怪物们进行猎杀。街道上到处都是怪异的死尸——曾经的富翁,有钱人的尸体。
一些怪物逃向汽车公墓。
这是“上帝重塑人类计划”阶段的人类悲惨的下场。
政府将那些有钱人的公司资产、家产全部回收,基因改造由政府垄断,继续出台了“上帝重塑人类计划”。
这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历史啊。
他们自认为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人类的问题,至少他们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我既能生男人,也能生女人,还能生下我自己。
他们没有通过上帝,或者说他们就是上帝,重新塑造了他们自己。
三
诺娜是个活泼的女孩。她一口鲍牙,牙齿黑黄,靠近我坐着,她爷爷抽着我递给的烟,不断地夸着烟品质如何好,他满嘴的牙齿稀稀拉拉的已经没几颗。
——谭老师,能不能把你的手机让俺们瞧瞧?诺娜的爷爷问道。
我把背包里的手机掏给他,已经没电了。没电有两个原因,一是我自离开那座虚拟城市后,没找到能充电的地方;二是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联系的人。
老头拿着我的手机看来看去,长叹了一声,眼角滴下了一颗浑浊的老泪。
——与我们一样哪,都是普通手机,而不是智机。
——老张是好人,但他不是大圣。但老张很有骨气,虽说早就知道能反抗个啥,但人总得有点精神,对吧?
诺娜的爷爷颤声说道。周围几个人连连点头。毫无疑问,诺娜的爷爷是这里的精神领袖。我不得不对他表示敬意,又掏了一根香烟递给我们的精神领袖。
这里没有书,没有智机,没有文明。
——我们生活在这个烂死人世界,还有没有天理?
我无言以对,也知道他们这么说无非是自言自语。
过会儿,老头脸上突然散发出自信的红光,说道:我们虽说脑残,但我们是人,他们不是人。我们有同情心,而他们呢?除了智商高,有什么了不起的。
一阵咯咯的笑随即而起,老头有气无力地笑着,双肩抖动,像要抖掉肩膀上什么东西似的。笑了一会儿,咯咯的笑变成粗声的喘息,他双手捂着胸,大喊救命,脸呈死灰色。过了一会儿,他脸色转白,好起来了。他完全被自己笑虚脱了。
诺娜的爷爷在几个人搀扶下,回到布栏处。诺娜还在。
——你看他们多漂亮,一个比一个完美,一个赛一个天仙。
她带着那种发痴的少女心对我说。
——我们丑死了。难怪他们叫我们是污人。
我只能重复她爷爷的话——我们是人,有同情心。而他们全然丧尽同情心,他们不是人。
我看着诺娜,微笑着。
是啊,他们精益求精,有机械的冷,是一种完美的艺术。他们的眼里没有怜悯,就不是人类。
他们俨然解决了因贪婪而丑陋的这个人类自古以来的定律,他们贪婪而美丽。这才是糟糕之处。
我想起他们说的话:你们活着,在于我们仁慈。
自从政府垄断基因改造技术,继续推行“上帝重塑人类计划”,如我等普通人很快明白:谁掌握计划,谁就能拥有重塑自我的特权。于是拥有特权的人越来越完美,越来越聪明,他们的思维和身体都趋向“神”的境界。而没有特权的我们,即普通大众开始引起了惊慌,真正发自内心的恐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