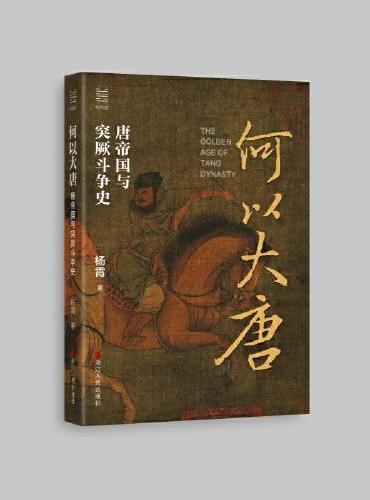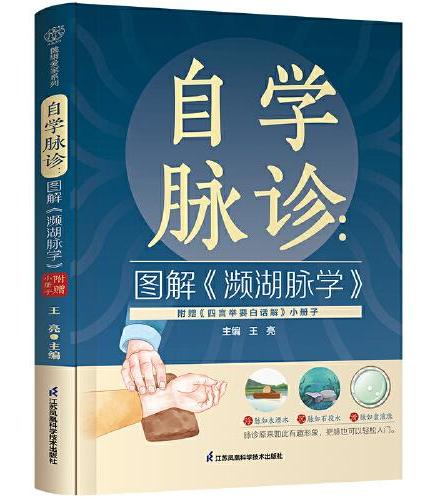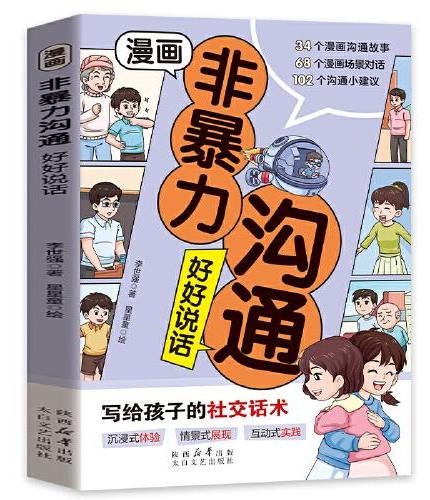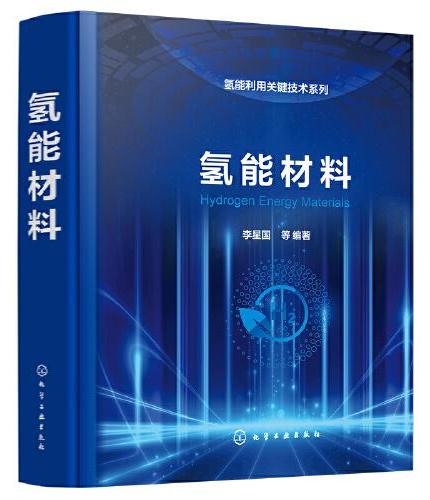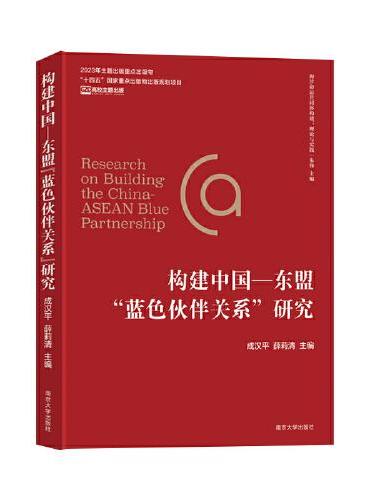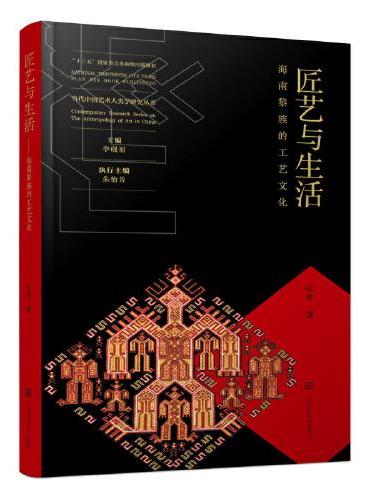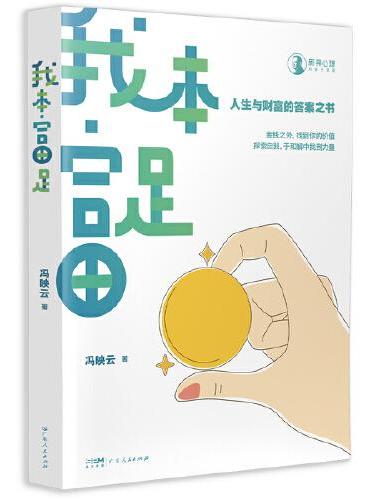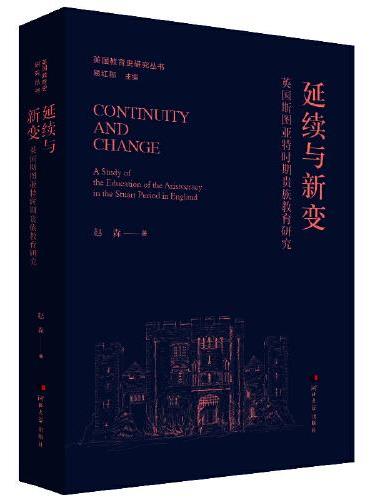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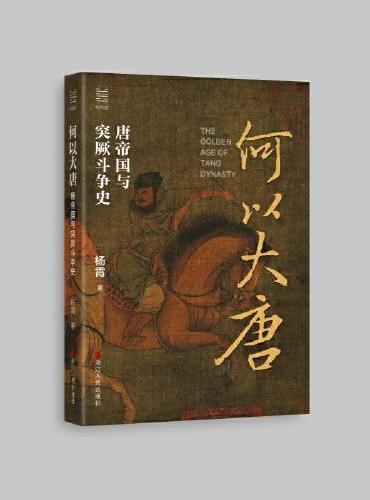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以大唐:唐帝国与突厥斗争史
》
售價:HK$
8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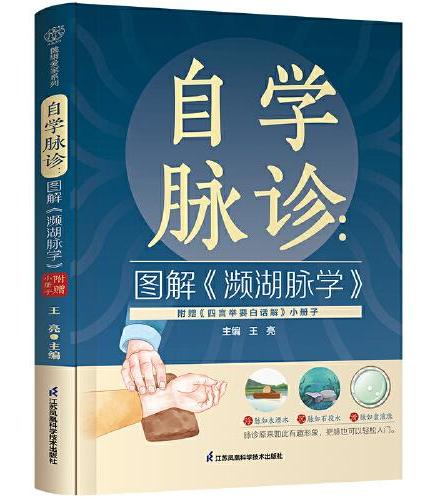
《
自学脉诊:图解《濒湖脉学》
》
售價:HK$
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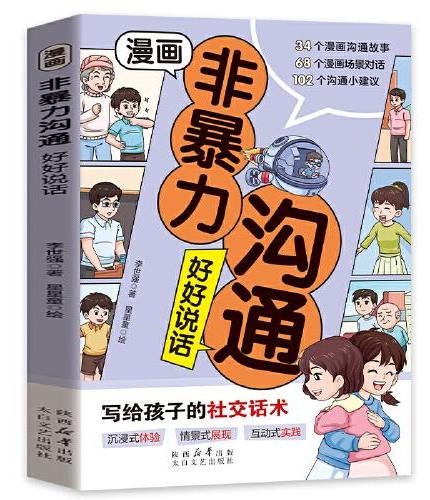
《
漫画非暴力沟通 好好说话写给孩子的社交话术让你的学习和生活会更加快乐正面管教的方式方法 教会父母如何正确教育叛逆期孩子 用引导性语言教育青少年男孩女孩 帮助孩子拥有健康心理的沟通方法
》
售價:HK$
5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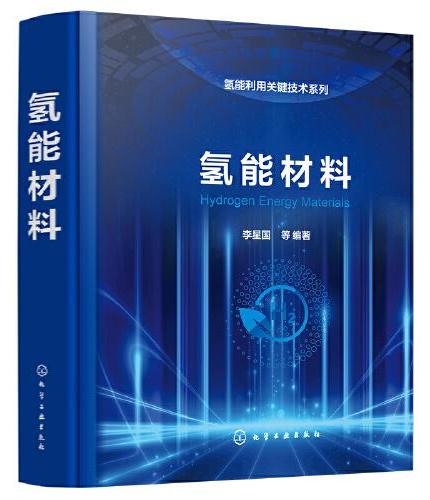
《
氢能利用关键技术系列--氢能材料
》
售價:HK$
3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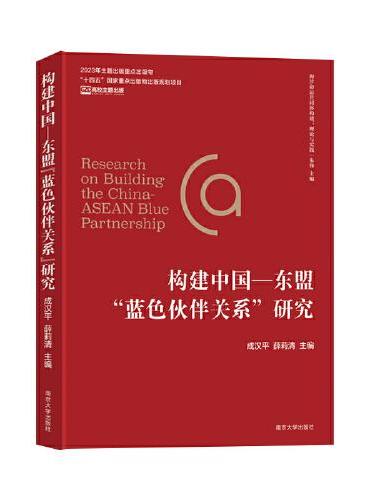
《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 理论与实践)构建中国——东盟“蓝色伙伴关系”研究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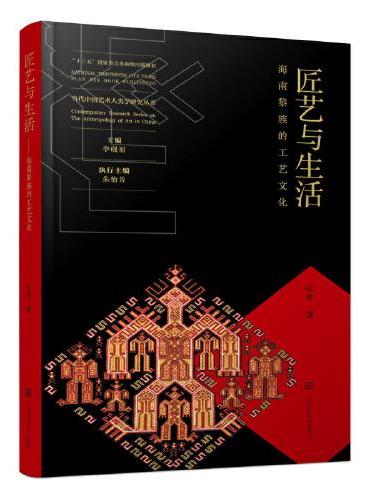
《
匠艺与生活:海南黎族的工艺文化
》
售價:HK$
10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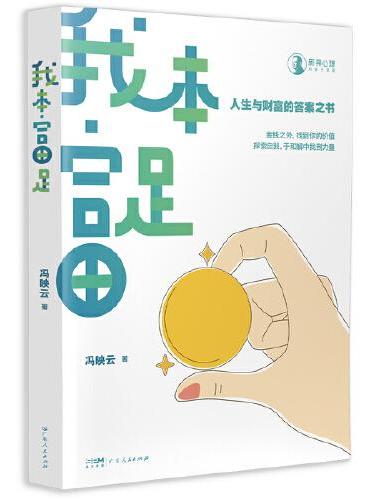
《
我本富足
》
售價:HK$
7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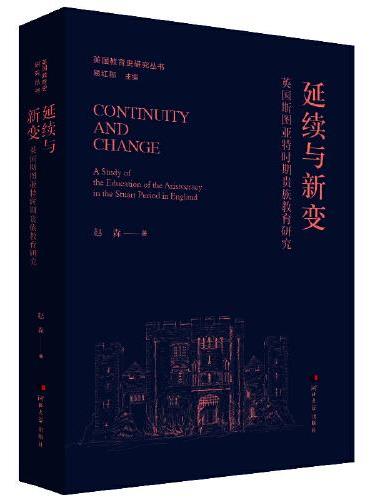
《
英国教育史研究丛书——延续与新变:英国斯图亚特时期贵族教育研究
》
售價:HK$
108.9
|
| 編輯推薦: |
|
◎2015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非虚构作品奖◎《西雅图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圣路易斯邮报》《卫报》年度图书◎医生开的处方,怎么会跟海洛因和死人扯上关系呢?接受了好的戒毒治疗怎么还戒不掉呢?止痛药依赖怎么会让海洛因趁机进入主流社会?死于药物过量的人多过死于车祸的人!《梦瘾》告诉你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
| 內容簡介: |
服用止痛药在现代社会是家常便饭。对于非致瘾性止痛药的研究,美国药物依赖问题委员会1928年一成立便视为己任。然而,有医生认为“患者很少成瘾”,此言1980年代初经权威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令医药界兴奋不已。
1996年,普渡制药推出新型止痛药奥施康定。公司开展大规模营销,不仅大做广告,还招募大量销售人员对医生采取盯人战术,、支付度假费用,还出资赞助医学研讨会。而1999年疼痛被医疗认证机构定为第五大生命体征,以及官方报告称疼痛没有得到充分治疗,更是推波助澜。于是,处方开具无度,造成患者的药物依赖。
奥施康定效果神奇且有不同剂型,价格却过高,一些成瘾者便利用医保以及各州的法律差异获取药物,以贩养服,或者干脆改用毒品。
同期,怀着发财梦的墨西哥年轻人带着廉价且后劲大的黑焦油海洛因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以加州等地的拉美人社区为基地,以白人富人为目标,建立起隐蔽而强大的零售网,使得买毒品可以像点外卖一样方便。
就这样,毒品经由止痛药开辟的途径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这一次,瘾君子几乎都是白人。2000年和2006年,美国缉毒署两次开展行动打击黑焦油海洛因,但死于药物过量的人数仍然居高不下,甚至超过了车祸的死亡人数。
本书作者山姆?昆诺斯曾是《洛杉矶时报》墨西哥缉毒战报道组的记者,他从“蓝领之城”朴茨茅斯追踪到墨西哥小镇,采访了年轻毒贩、制药业人士、缉毒署特工、痛失子女的父母以及沉迷药物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以令人心碎的故事揭示了止痛药及毒品对于当代美国社会及其核心价值观的腐蚀。
|
| 關於作者: |
山姆?昆诺斯,1958年出生,从事记者工作近30年,曾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墨西哥生活了10年,在那里他完成了两本著作。2004年,他回到美国为《洛杉矶时报》工作,进行移民、贩毒、帮派等方面的调查和报道。2014年辞职,重做自由职业者,为《国家地理杂志》《纽约时报》《洛杉矶杂志》等刊物工作。
2011年开始撰写并出版“真相系列”作品,《梦瘾》便是其中之一。
|
| 目錄:
|
本书中大事件时间表/001
前言 俄亥俄州朴茨茅斯/001
导言/001部分1
1. 恩里克/003
2. 吉克医生的信/005
3. 都是老乡/007
4. 阿巴拉契亚的李伯拉斯/015
5. 广告人/021
6. 恩里克发迹/026
7. 分子/031
8. 像送批萨一样送货/036
9. 恩里克只能靠自己/044
10. 罂粟/050
11. 比种甘蔗容易/055
12. 打个电话就来了/069
13. 漂泊的恩里克/074
14. 寻找圣杯/078
15. 疼痛难忍/083
16. 疼痛与职业摔跤手/090
17. 神秘人/093
18. 一场革命/097
19. 都是为了501型牛仔裤/107
20. 里程碑式的研究/116
21. 恩里克的救赎/122
22. 我们意识到这是公司/127
23. 普渡制药/137
24. 神秘人与纳亚里特州/142
25. 和奥施康定一起摇摆/146
26. 神秘人回家/155
27. 奥施康定是什么?/161
28. 偏僻之地的贩毒家族/165
29. 李伯拉斯开路/171
30. 神秘人在腹地/181
31. 尸体是案子的关键/191
32. 恩里克当老板/196
33. 海洛因就像汉堡/202
34. “焦油坑行动”/206
第二部分211
35. 两千年前的问题/213
36. 碰撞: 零地带/220
37. 煤矿里的金丝雀/225
38. 一个月50、100个病例/231
39. 梦之地的瘾君子王国/235
40. 刑事诉讼/251
41. “接管奥施康定地带”/253
42. 后的便利/257
43. 山雨欲来/265
44. 五旬节派的虔信,疯狂的抓痕/269
45. “我们带起了这波流行”/275
46. 药物过量致死比车祸更甚/282
47. 一位职业摔跤手的遗产/289
48. 成为海洛因贩子的大好时机/292
49. 刑事案件/301
第三部分309
50. “现在轮到你邻居的孩子了”/311
51. 就像烟草公司的高管/316
52. 没有疤面人,没有大头目/323
53. 父母的摧心之痛/327
第四部分345
54. 美国/347
55. 你就是你的药/355
56. 毒品界的互联网/362
57. 没人能凭一己之力做到/372
第五部分381
58. 瓦砾中成长/383
后记/399致谢/
|
| 內容試閱:
|
1929年,俄亥俄河边的蓝领小镇朴茨茅斯正处于30年的繁荣时期,一家私人游泳池对外开放,人们称之为“梦之地”(Dreamland)。
游泳池有橄榄球场那么大。几十年来,一代一代的小镇居民就是在这晶莹湛蓝的水边长大的。
夏天,孩子们都在“梦之地”度过。父母们每天都会把孩子们留在这里。小镇居民从“梦之地”厚厚的湿热中找到了喘息的机会,然后穿过街道去A&W快餐店买些热狗和根汁汽水。泳池卖的炸薯条是好的。早上,孩子乘公交车去游泳池,下午回家。他们来自赛欧托县的各个学校,在此相识并学游泳。当地一家名为WIOI的电台每半小时就会播放一句广告语——“该翻身了,免得晒伤”,电台的人很清楚,许多听众此时此刻就在“梦之地”边听收音机,边享受日光浴。
巨大的泳池中间有两个水泥平台,孩子们可以在那里晒晒太阳,然后再潜入水中。平台上还竖着几根杆子,顶上挂着泛光灯,为晚上游泳的人照明。泳池的一边有一片巨大的草坪,许多家庭会把浴巾铺在草地上;泳池的另一边则是更衣室和一家餐馆。
“梦之地”可以容纳几百人,然而神奇的是,它周围的空间还在不断扩大,总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多年来,这座游泳池的主人一直都是市财务长杰米·威廉斯。此外,他还和别人合开了一家鞋厂,鞋厂是朴茨茅斯工业实力的核心。他买下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多年以来,“梦之地”的发展似乎越来越好,还新增了一个大型野餐区和好几个儿童游乐场,以及垒球场、橄榄球场、篮球场和沙狐球场,外加一个电子游戏室。
有段时间,这里只接待白人,泳池变成了一个私人俱乐部,连名字都改成了“天台俱乐部”。可是,朴茨茅斯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杂居城镇,警察局长是黑人,学校里既有黑人孩子也有白人孩子。只有这家游泳池实行种族隔离。1961年夏天,一个名叫尤金·麦金利的黑人男孩因为不能进这家泳池而去了赛欧托河游泳,结果溺水身亡。朴茨茅斯的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介入此事,举行了“涉水示威”wadein,黑人为抗议种族歧视而在白人专用的海滩或游泳池举行的示威。——译者,而黑人也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泳池边。随着种族融合,泳池改回了原来的名字“梦之地”,尽管黑人再也没在这里感到完全地踏实。
不过,“梦之地”确实冲走了阶级差异。穿上泳衣,工人看上去与工厂经理或服装店老板并无区别。住在朴茨茅斯山顶上的富裕家庭向一个基金会捐款,用于支付该镇东端到铁道和俄亥俄河之间这一带家庭的夏季通票。这样,生活在东端的底层人士和生活在山顶的上层人士都能在“梦之地”相遇了。
加州有自己的海滩。美国腹地的人们夏天都在游泳池边度过,而在俄亥俄州南端的尽头,“梦之地”对朴茨茅斯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一张家庭季卡只要25美元,这是非常珍贵的礼物,通常是圣诞赠礼。家里买不起季卡的孩子们可以为邻居家割草,换得15美分,正好够买一张游泳池单日卡。
周五的游泳舞会在午夜开始。人们搬出了自动点唱机,孩子们在泳池边手舞足蹈。一对对情侣手拉手绕着“梦之地”散步,宣告新恋情的诞生。女孩们从舞会步行回去,家家都夜不闭户。“夜晚的酷热配上清凉的池水,简直棒极了,”一位女士回忆道,“那是我的整个世界。我别的什么都不做。等我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也要带他们去那里。”
事实上,“梦之地”见证了朴茨茅斯一轮又一轮的生命周期。蹒跚学步的女婴在父母,尤其是妈妈的注视下,在泳池的浅水区度过了自己人生的初几年,其间她妈妈通常会和其他年轻的妈妈一起铺块毛巾,坐在泳池边的水泥地上。她小学毕业后,活动范围渐渐转移到了泳池的中区,注视着她的父母也会退到草地上。进了高中,她就会去10英尺深的泳区附近的草地,在靠近跳台和救生队长椅子的地方活动,而她的父母则撤得更远了。当她结婚生子后,她会回到泳池的浅水区照看自己的孩子,整件事又重新来一遍。
“我的父亲是二战的海军老兵,他坚持让他的4个孩子不仅要学会游泳,还要学会不怕水,”一位男士写道,“我妹妹3岁时就可以从15英尺高的跳板跳水。当然,父亲、我还有哥哥都站在水里,以防万一。我妹妹会从水里探出头来,大叫……‘再来一次!’”
多年来,“梦之地”的经理查克·洛伦茨一直带着码尺在这里走来走去,这位朴茨茅斯的高中教练、纪律严明之人,要确保孩子们牢记他定下的“3英尺规定”,即彼此保持3英尺的距离。他的规定并没有起作用。似乎镇上一半的人都在泳池得到了某人的初吻,还有很多人在“梦之地”一望无际的草地上失去了童贞。
与此同时,洛伦茨的儿子还不会走路就学会了游泳,并在高中时当上了“梦之地”的救生员。“作为救生员,坐在这张椅子上,所有的活动、所有的昂首阔步、所有的打情骂俏你都尽收眼底。”约翰·洛伦茨说。现在,他是一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你就像坐在王座上的国王一样。”
这些年间,朴茨茅斯陆续开了两家保龄球馆、一间杰西潘尼百货公司、一间希尔斯百货、一间带自动扶梯的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商店,还有当地人开的马丁百货,店里有家照相馆,毕业生会来此拍证件照。奇利科西街总是熙熙攘攘。街道两旁成排地停靠着美国产的大轿车和旅行车。每个周六,人们会在Kresges兑现支票,摩根兄弟珠宝店、赫尔曼肉铺、康特面包房以及阿特拉斯时装店的老板们过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孩子们乘公共汽车去市中心看电影或去史密斯杂货店买樱桃可乐,在万圣节时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到很晚。周五、周六的晚上,十几岁的孩子们在奇利科西街上游荡,从斯戴克杂货店走到史密斯杂货店,然后转身再走一遍。
鞋厂全年都会从每个工人的工资中扣除圣诞储蓄的钱。圣诞节前,每个工人会拿到一张支票,然后在银行兑现。奇利科西街上那时到处喜气洋洋。当顾客摩肩接踵地站在商店橱窗前,看着里面画满的各种拐杖糖、圣诞树和雪人,欣赏着机械木偶的表演时,铃声就响了起来。马丁百货的二楼有一个圣诞老人。
因此,1979年和1980年,朴茨茅斯人觉得被评上全美城市是理所当然的。当时,这座城镇有超过42万居民,富人极少,美国劳工部将会把许多朴茨茅斯人划为穷人。“但我们没意识到这一点,也不在乎。”一位女士回忆道。这里的工业支撑了整个地区的发展。没有一家的后院有游泳池,但这里有公园、网球场、篮球场,可以欣赏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可以从堤坝往下滑着玩。家家户户冬天会去米尔布鲁克公园溜冰,夏天则去罗斯福湖边野餐,或者当孩子们在街上不亦乐乎地玩着踢罐子游戏时,大人们在一旁闲坐到夜深。
“我们家过去常常去俄亥俄河旁的小公园里野餐,父亲会把我的秋千推得高高的,让我以为我会落在肯塔基州。”另一位女士说。
所有的这种娱乐活动让工薪家庭感到非常富足。但是,这一切的中心就是那个闪闪发光的游泳池。当小镇渐渐衰落,浸透了氯气、水宝宝防晒霜和炸薯条味道的“梦之地”的记忆,却伴随着几乎每一个在朴茨茅斯长大的人。
如今有两个朴茨茅斯。一个是俄亥俄河边的那个随处可见废弃房屋的小镇,另一个则深藏在成千上万个背井离乡的朴茨茅斯人的记忆中,这些人在此长大,见证了辉煌,已经很少重返现实中的故地了。
你要是问他们,那时候的城镇是什么样的,他们会告诉你,是梦之地。
人物故事
1. “好孩子”麦特之死
2009年,麦特进入大学读大一,父母从未弄清楚麦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服用当时遍布俄亥俄州中部和田纳西州的那些药片的。但就在那一年,药片已经成为麦特生活的很大一部分。
那年年底,麦特回家和父母一起生活。回到家的麦特似乎不再像他在学校时那样漫无目的。他衣着整齐,并在好几家餐饮公司做过全职。但是,他的父母后来意识到,在他搬回家时,他已经成了一个功能性瘾君子,使用阿片类处方止痛药,尤其是扑热息痛。后来,他改用奥施康定,普渡制药生产的一种强效药。
2012年初,麦特的父母发现了问题。他们很担心,但麦特一直在滥用的药都是医生开的处方药,不是那种会要人命的街头毒品,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带麦特去看医生,医生要求他在家戒毒一周,用血压药和安眠药来缓解阿片类药物戒断所产生的症状。
不久,麦特就故态复萌。由于买不起市面上的奥施康定,麦特在某个时刻转而用起了黑焦油海洛因,一种由墨西哥年轻人从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一个名叫纳亚里特的小州带来,已经充斥哥伦布的毒品。
2012年4月,麦特涕泪交加地向父母坦白了自己海洛因成瘾的事。震惊之余,他们把他送进了一家治疗中心。
2012年5月10日,经过三个星期的戒毒治疗之后,麦特?斯库诺夫回了家,这让他的父母觉得噩梦结束了。第二天,他们给麦特买了一块新的汽车电池,一部新手机。麦特出门去参加戒毒互助会的一次聚会,然后和朋友们去打高尔夫。他本该在聚会结束后给父亲打个电话的。
然而,他的父母等了一整天也没等来电话。当晚,一位警官敲开了他们的门。
800多人参加了麦特的葬礼。他才21岁,死于黑焦油海洛因注射过量。
麦特去世后几个月里,保罗和艾伦被他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一切震惊了。首先是那些药片:那是医生开的处方,怎么会跟海洛因和死亡扯上关系呢?什么是黑焦油海洛因?住在天桥底下帐篷里的人才会吸食海洛因,而麦特在好的社区里长大,上的是私立基督教教会学校,参加的教会也是非常知名的。麦特承认自己有瘾、寻求帮助,也接受了哥伦布好的住院戒毒治疗。为什么这还不够呢?
经由药片,海洛因进入了主流社会。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是瘾君子队伍中的新成员;橄榄球运动几乎是通往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一扇大门。从阿富汗归来的受伤士兵因止痛药成瘾而死在了美国。孩子们在大学里染上了毒瘾,再也没能活着走出校门。他们中有牧师的女儿,警察、医生的儿子,承包商、教师、企业主和银行家的孩子。几乎每个瘾君子都是白人。
许多父母,他们的孩子还活着,但已经变得谎话连篇,为了一种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偷窃成性。这些父母每天晚上都害怕接到电话,说他们的孩子死在了麦当劳的卫生间里。他们耗尽家财为孩子支付戒毒的费用,到头来还是阻止不了孩子锒铛入狱。他们举家搬到没人知道他们家丑的地方。他们祈祷自己的孩子能重新做人。有些人想过自杀。对于阿片类药物滥用造成的突如其来的噩梦,以及由此对他们的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他们既震惊又措手不及。
2. 恩里克的美国梦
恩里克的母亲讨厌下雨。雨滴在他们纸板棚屋的瓦楞铁皮的屋顶上,几个星期都干不透。她得把平底锅、水桶放在小屋各处去接不断从屋顶漏下来的雨水。当恩里克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小孩时,他在雨天到处跑、踩地上的水坑,还追赶镇上的流浪狗。但对恩里克的母亲而言,冰冷无情的雨水映衬出了他们的贫穷,也让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
恩里克的父母生活在墨西哥纳亚里特州一个屯子的尽头,那里没有平整的街道,也没有电。父母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了,手里没有土地。他们靠卖木炭和木材勉强维持生计。恩里克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这家人和另外两家一起挤在一个四居室的房子里。几年以后,他们在一个名为蟾蜍村的街垒找到了一块地,就在村子尽头的沼泽附近。他们用纸板、油布以及可能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胶合板,建了个有两个房间的棚屋。他们又生了更多的孩子。恩里克对于那些年的记忆只有吼叫、父亲殴打母亲、母亲为不知从哪里弄到食物而发愁。
后来,奇迹发生了,恩里克的父亲继承了自己父母的土地,全部50英亩只留给了他而不分给其它子女。由此,恩里克的父亲变成了地主,种上了甘蔗,这在墨西哥民粹主义兴起的1970年代是享受新政府的价格支持的。有了积蓄之后,他买了一辆旧卡车运甘蔗。财产并没有让恩里克的父亲脾气变好,反而使他更自大了。他不仅夜里醉醺醺地回家,还对孩子大喊大叫,对妻子拳脚交加。
他听人们说他们很穷,但很快乐。可是,恩里克从没见过哪个穷人身上绝无半点凄惨的。一条不可逾越的河流似乎将蟾蜍村与世界隔离开了。在蟾蜍村,贫穷屡屡使村民们为了占点上风而与人恶战。恩里克帮另一个农夫家挤奶,报酬是每天2升牛奶和每周10比索,为此,他得忍受和他同样年纪的农夫儿子的拳脚和侮辱。有一次,恩里克病了,母亲带他去了特皮克的一家医院。他盯着那些香喷喷的女人、坐在新车里的男人以及穿着新衣服的孩子看。特皮克离他所在的屯子只有几英里远,但它就好像在河那边一个遥远的地方。
再长大些,恩里克上学去了。他讨厌学校的老师,就像他母亲讨厌下雨一样。老师对村里条件好的地方的孩子和颜悦色,对蟾蜍村来的衣衫褴褛没有午饭的孩子们却言语尖刻。对条件好的地方的孩子,老师奖励他们糖果、玩具,蟾蜍村来的孩子却连一次拿奖的机会也没有。有些老师不许蟾蜍村来的孩子上厕所,直到他们尿在了裤子上。有几个老师醉醺醺地就进了课堂;还有几个一连几星期都不见人影。恩里克的父亲嘲笑他连乘法表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老师,他怎能学会呢?
生活给了他一个惊喜: 他的舅舅们北上去了洛杉矶工作,这一层关系让其他的孩子对他家羡慕不已。村里的人把他的舅舅们说成是远方的探险家,并交换各自所知的消息。恩里克没有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父亲与舅舅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好。几年前,他们还打过一架,他父亲被刀伤了,舅舅那边家里死了2个人。他父亲跟这个家庭是姻亲,但他和他的小舅子们都不喜欢对方。
某天,有消息传来,说他的一个舅舅要从圣费尔南多谷回来了。亲戚们为即将收到的礼物激动不已。那天,妈妈们都给孩子梳洗干净,排着队,翘首企盼。这个舅舅依然记得与恩里克父亲之间的恩怨,给每个人都带了礼物,就是没有恩里克和他的姐妹们以及他的母亲的那份。孩子们带着不解流着泪回家了。
生活在慢慢地改善。他的母亲总算攒够了钱,买了一头牛,他们终于也算得上是牧场主了,因此他们更加卖力地工作。恩里克睡觉的时候,梦想着以后可以过受人尊敬的农民的生活。过段时间,他又想当警察。公路巡警看起来是个令人兴奋的工作,但他的父亲并没有政界的关系送他进警察学院。
恩里克看着和他父亲一样的农夫把自己的生命都浪费在那些田地里,却依然一样地无知、暴力、冷酷、深陷贫困,受人控制。逃离这种命运成了恩里克的头等大事。
遇到一个女孩后,他的这种想法就更加迫切了。她12岁,很漂亮,她父亲是镇上的屠夫,这使她属于屯子里的上层阶级,比恩里克这种酒鬼甘蔗农的儿子高贵得多。恩里克知道他无法给这个女孩以及她父亲所期望的生活。但当他要求她做他女朋友时,她答应了。
后来,他的母亲去了加州几个月,回来时带了礼物。几个北上的舅舅,曾经不满恩里克的父母结婚,现在已经平息了怒火,给恩里克寄去了他人生中批来自美国的衣服。村子里的人把他们看作英雄;有些人请求他的舅舅们帮助他们北上。恩里克想象中他的舅舅们都是那个叫卡诺加公园的地方的大人物。
初中毕业后,恩里克去了特皮克的高中。他在高中待了两个星期,每天中午都没有饭吃,在用完给他乘巴士的钱之后,他退学了。田间日头的生活现在似乎要变成可怕的现实了。在甘蔗田里劳作,他永远也不可能给得起那个女孩和她父亲想要的。在村子里,女孩们早早就嫁人了;虽然她只有13岁,可恩里克却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水管终于通进了村子。镇民们现在喝水不用从远处的井里打了,打开自来水龙头就有。马桶的到来让大家不用去山里解决了。但恩里克满脑子想的只有他在卡诺加公园的舅舅。于是他定了计划,藏在心里。他要先到蒂华纳,找个蛇头带他去卡诺加公园。他没有舅舅的地址,也没有电话,但他想着舅舅们肯定名声在外,很容易就能找到。
一天,他穿过村子,去跟朋友们打招呼,又跟女朋友待了一会儿,没和任何人告别。第二天,他带上出生证明,穿上舅舅们寄给他好的一件黑色夹克,还有白衬衫和蓝裤子,吻了吻他的母亲,说他那天会晚点回来。他去了特皮克,搭乘“三颗金星”的大巴,这条低成本的公交线多年来载过数十万打算穿越边境的墨西哥人北上。
他用从父母那里偷来的200比索买了一张车票。他把这笔钱看作贷款,这样他就不会为此而内疚了。他在靠窗的位置坐了28个小时,为了去一睹他以前从没看到过的一切。
那是1989年,他14岁。
3. 像病毒一样的“铪利斯科男孩”
查维斯总在街上看到毒贩、背包里装着海洛因的快递员、带着海洛因气球的司机,线人说,这些人看上去很随意、很分散,但其实不是。他们都是一伙的。他们都来自一个名叫铪利斯科的小镇。
线人告诉查维斯,所有在丹佛的大街小巷兜售黑焦油海洛因的人都来自这个名叫铪利斯科的小镇,或者其附近的小村庄。他们之所以成功,在于他们学会了建立一个系统,一个海洛因零售系统。这个系统很简单,真的,就是依靠廉价的墨西哥非法劳工,就像所有快餐外卖一样。
从那以后,查维斯就常和线人一起坐在离线人房子不远的酒吧或卡车里,听线人滔滔不绝地讲着铪利斯科来的这些人和他们的海洛因零售系统——这和线人之前在地下毒品世界所见到的完全不一样。
线人说,把它想象成一个快餐连锁店,比如提供批萨递送服务的一个地方。这里的每一个海洛因窝点或连锁店都有一个在纳亚里特州铪利斯科的店主,为这个窝点供应海洛因。店主不常来美国,他只和住在丹佛、帮他经营业务的窝点管理人联系。
线人说,窝点管理人手下有一个接线员。接线员整天待在公寓里接电话,都是瘾君子打来的,要订购毒品。接线员下面是几个司机,拿周薪,包吃包住。他们的工作就是开着车在城里转悠,嘴里塞满了未充气的装有黑焦油海洛因的小气球,一次塞上25到30个,看上去像只花栗鼠。他们会随身备一瓶水,遇到警察让他们停车,他们就大口大口地灌水,把气球吞下去,后气球会原封不动地随排泄物一起排出。除了司机嘴里的气球,车里的某个地方还藏了百余只气球。
接线员的电话号码在海洛因吸毒者之间流传,他们会打电话订购。线人说,接线员的工作就是告诉他们在哪里和司机见面:郊区某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或者麦当劳、温蒂汉堡、西维斯药店的停车场。随后,接线员会把信息转给司机。
司机在停车场附近转悠,瘾君子开车跟着,通常开到小巷子司机会停下来,瘾君子就跳进司机的车里。然后,一个人操着蹩脚的英语,一个说着蹩脚的西班牙语,一场跨文化的海洛因交易就这样完成了,司机吐出吸毒者所需的气球,拿上现金离开。
线人说,司机整天都做这件事。工作时间——通常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开始,一个窝点的司机可以很快就每天挣5000美金;一年内,这个窝点每天能有1.5万美元的进账。
这一系统是按照一定的原则运作的,线人说,纳亚里特州的毒贩不会违反这些原则。这些窝点之间相互竞争,但司机都是在老家就互相认识的,所以他们从来不会动用武力。他们也从不带枪,尽量和平共处。他们不在自己住的地方聚会。他们开的是用了好几年的轿车。这些司机没有一个吸毒。司机们在一个城市干了几个月之后,就会被老板送回家,或者送到另一个城市的窝点。窝点换车的频率跟换司机的差不多。新司机源源不断地送来,通常是铪利斯科县的农村男孩。窝点老板喜欢年轻的司机,因为后者不太可能偷他们东西;司机越有经验,就越有可能知道怎么偷老板的东西。线人猜测在纳亚里特州有成千上万的孩子渴望北上干司机这活,嘴里塞满海洛因气球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里转悠。
他说,在某种程度上,铪利斯科的窝点与其他任何毒品交易都不同,它的运作更像小企业。窝点老板付每位司机工资——当时丹佛的工资行情是每周1200美元。窝点老板对每个司机的花销都了如指掌,午饭花了多少钱、招妓花了多少钱都要有收据。为招揽生意,司机被鼓励给吸毒者提供特殊优惠:1个气球15美金,7个只要100美金。周一到周六天天都买了气球的瘾君子,周日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一次卖0.1克海洛因是这些司机的一份工作,全职,一周七天,圣诞节无休。因为吸食海洛因的人每天都离不了它。
窝点的利润靠零售业的传统做法——加成。他们的顾客都是精神恍惚、不顾一切的瘾君子,买不起半公斤的海洛因。任何一个想买大量海洛因的人十有八九是警察,目的是想办成一件案子,这会让毒贩坐好几年牢。线人说,你要求买大量的毒品,他们就会关机。然后你再也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这真的让线人吃惊。他从没听说过还有哪个墨西哥贩毒集团更愿意按小剂量卖毒品的。
此外,铪利斯科的贩毒窝点从来不和非洲裔美国人打交道。他们的毒品不会卖给黑人;也不会从黑人那里买,他们害怕被黑人抢劫,几乎只做白人的生意。
铪利斯科毒贩的创新实际上也是一种递送机制。从铪利斯科来的人发现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白人的孩子——想要的是服务和便捷。他们不想去贫民区或某些肮脏的毒品屋买毒品。现在他们不必去了。铪利斯科来的人会将毒品送到他们手里。
因此,这一系统快速扩张。到了1990年代,据查维斯的线人统计,美国西部十几个主要的大都市地区都有纳亚里特州的铪利斯科人运作的窝点。就当时而言,在丹佛,他就可以报出8到10个窝点,每个窝点都有3或4个司机,而且每天都开工。
听着查维斯的讲述,我感觉铪利斯科的人似乎是冲动之下才来的这里,事实上,很多墨西哥移民正是受这种冲动的驱使。大多数墨西哥移民在美国待了几年,并没有融入美国,而是想着终有一天会回家。这是他们的美国梦:衣锦还乡,向家乡的每个人炫耀。他们经常打电话回家,给家里寄钱,比起自己孩子就读的美国学校的事务,他们通常更关心老家屯子里打新井的事。他们回家参加村里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在烤肉宴、婚礼和成人礼上打肿脸充胖子地花钱。为了这些,他们一边在美国做着艰苦的工作,一边在屯子里坚持不懈地盖房,房子就像纪念碑一样承载着他们有一天要衣锦还乡的愿望。这些房子要花十年才完工。这些移民每次回家都会给房子添点什么。他们始终如一地往房子一楼顶上加钢筋。钢筋是一种承诺,一旦他拿到钱,就会加盖第二层。一根根钢筋醒目地矗立在那里,成了成千上万墨西哥移民村庄和屯子的天际线的一部分。
完工的房子通常有大铁门、现代管道和大理石地面。随着那些梦想建造自己的房子的人们的离开,这些镇子慢慢地改善着。多年来,这些城镇变成了梦想之地,空旷如电影里的场景,移民们在圣诞节或一年一度的宗教节日期间短暂地回来放松一下,想象着有一天他们能再次回来,过上富足的退休生活。讽刺的是,工作、抵押贷款和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让大多数移民永远无法回到墨西哥永久居住在他们用这种牺牲建起的房屋里。
然而,铪利斯科的海洛因毒贩却一直在这么做。他们的故事里有移民,有让一个贫苦的墨西哥人移民的动力,当然也有贩毒的故事。那些终没有坐牢的铪利斯科毒贩回到了家乡,住进了他们的房子里。他们没有在美国扎根;事实上,他们在这里几乎不怎么花钱。牙买加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甚至墨西哥其他毒贩都在美国买房置业,炫耀自己的财富。而铪利斯科来的毒贩是查维斯所知道的一群以回家为终目标并且没开过一枪的移民贩毒集团。
他们像病毒一样蔓延,悄无声息,许多执法人员都无法认出他们,常常把铪利斯科的团伙错认为是不成气候的小毒贩。
“我称他们为‘铪利斯科男孩’,”查维斯说,“他们遍布全国各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