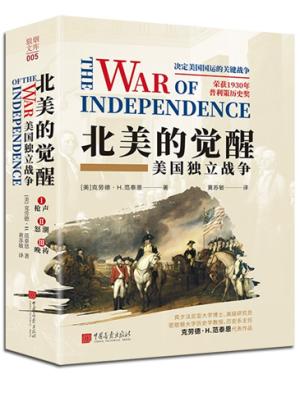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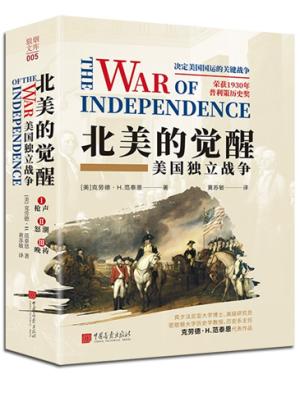
《
北美的觉醒:美国独立战争(全3册)
》
售價:HK$
173.8

《
遥远的不莱梅(直木奖获奖作家重松清超人气暖心疗愈系小说!)
》
售價:HK$
54.8

《
名士的反抗:从孔融到嵇康
》
售價:HK$
96.8

《
万千心理·图式疗法临床实践:模式工作模型应用指南(原著第二版)
》
售價:HK$
85.8

《
美国启蒙运动
》
售價:HK$
129.8

《
变局与定力
》
售價:HK$
86.9

《
岭南学报复刊第二十四辑:文本·观念·空间:中国文学的一个精神侧影
》
售價:HK$
107.8

《
星斗:古国时代的中国
》
售價:HK$
327.8
|
| 編輯推薦: |
(附赠短篇小说夹在图书中间)
★90后天才女作家萨莉·鲁尼继《聊天记录》《正常人》之后重磅新作
★聚焦后疫情时代下,经济、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年轻人的迷茫和挫败感
★上个世代的迷茫青春,有他们的塞林格,有他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有他们的《在路上》,这一代有自己的代言人——萨莉·鲁尼
★《纽约时报》小说排行榜名,“美国版豆瓣Goodreads2021年年度小说,英国、爱尔兰所有畅销书排行榜名,英国上市5天销售4万册,欧美青年爱的2021年读物
|
| 內容簡介: |
小说家艾丽丝独自搬到陌生滨海小镇,在交友软件结识蓝领工人费利克斯,邀请他陪自己去罗马宣传新书。在都柏林,她好的女友艾琳刚走出失恋的阴影,开始与从小就相识的西蒙约会。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艾丽丝,费利克斯,艾琳,西蒙,四个人都过了三十岁,他们仍然年轻,但生活正在渐渐追上他们。他们相互渴慕,相互隐瞒,分分合合。他们为爱与性,为友谊和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烦恼。他们是否站在天黑以前后一个有光的房间里,见证什么?他们能否相信,还存在一个美丽的世界?
|
| 關於作者: |
萨莉·鲁尼,世界知名的爱尔兰新生代小说家。1991年生于爱尔兰西部的梅奥郡,2013年毕业于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英文系。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聊天记录》成为全球畅销书,萨莉·鲁尼因此获得2017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青年作家奖,该书也被《巴黎评论》杂志评为年度小说。
2018年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正常人》入围布克奖、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英国女性文学奖、迪伦·托马斯奖,获得科斯塔年度小说奖、爱尔兰年度图书奖,被评为水石书店“年度图书”,英国图书奖年度图书。根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于2020年春季由BBC、Hulu推出,风靡全球。由该剧制作团队改编拍摄的《聊天记录》电视剧于2022年5月播出。
第三部小说《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于2021年9月在英美同步出版,迅速登上《纽约时报》小说排行榜榜首,并被Goodreads评为年度小说。
|
| 內容試閱:
|
一
一个女人坐在一家酒店的酒吧里,注视着门口。她穿着整洁,一件白衬衫,浅色头发别在耳后。她扫了眼手机屏幕,上面显示着一个聊天界面,然后重新看向门口。这是三月末的一天,酒吧里很安静,在她右侧窗外,大西洋之上,太阳刚刚开始下沉。现在是七点零四分,然后是七点零五,零六。她短暂地检查了一下手指甲,看上去不是很感兴趣。七点零八分,门口进来一个男人。
他身形瘦削,深色头发,窄脸。他环顾四周,目光扫过其他顾客的脸,然后拿出手机,查看屏幕。窗边的女人看见他了,但她只是注视着他,没有特意做什么引起他注意。他们看上去年纪相当,二十八九或三十出头。她任由他站在那里,直到他看到她,走了过来。
你是艾丽丝?他问。
没错,她答道。
好,我是费利克斯。抱歉我迟到了。
她用温和的语气答道:没关系。他问她想喝什么,然后去吧台点单。女服务生问他近如何,他答道:还行吧,你呢?他点了一杯伏特加汤力水、一品脱杯的拉格啤酒。他没等回到桌边,
就把那瓶汤力水倒进伏特加杯中,手腕动作利落熟练。女人坐在桌边等他,手指轻轻叩击啤酒垫。这个男人进来后,她的举止变得更警觉,也更生动了。她此刻看向窗外的夕阳,仿佛对它兴趣盎然,尽管此前她并未关注它。男人回到桌边,把酒放下,洒了一滴啤酒,她看着它从他的玻璃杯侧飞快地滚落下来。
你之前说你刚搬过来,是吗?他问。
她点点头,啜了一口酒,舔了舔上唇。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问。
什么意思?
我是说,没什么人会搬过来,一般来讲。大家都是从这儿搬走,这个更常见。你该不是为了工作搬过来的吧?
噢。不,不算是。
他们的目光短暂交接,可以确定,他在等她进一步解释。她神情闪烁,仿佛在下决心,后她微微一笑,有点随意,仿佛心照不宣的样子。
这个嘛,我刚好打算搬家,她说,然后听人说城外有栋房子——我有个朋友认识房东。他们好像一直想卖掉,后决定在找到买家前先把它租出去。总之,我觉得在海边住着挺好的。这个决定可能的确有点心血来潮。所以——但来龙去脉就是这样,没别的原因了。
他边喝酒边听她说话。讲到后,她似乎变得有点紧张,主要体现在说话有些气短,脸上露出自嘲的神情。他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的表演,然后放下酒杯。
好吧,他说,你之前住都柏林是吗?
各种地方都待过。我在纽约住过一阵。我是都柏林人,我应该跟你说过。但我去年刚从纽约回来。
那你如今在这儿准备干吗呢?找工作什么的?
她顿了顿。他微微一笑,向后靠在座位上,依然注视着她。
不好意思,我问题有点多,他说,我还是有些不明白。
没关系,我不介意。不过你也看得出来,我不太擅长回答问题。
那好,你是做什么的?这是我后一个问题了。
她对他回以微笑,笑容紧绷。我是个作家,她说,要不你说说你是做什么的?
唉,没有你的职业那么特别。我很好奇你写什么,不过我就不问了。我在城外一间仓库上班。
做什么?
嗯,做什么,他镇静地重复道,把包裹从货架上拿下来,放到手推车里,再推到前面去打包。没什么意思。
那你不喜欢这份工作咯?
老天,当然不了,他说,我他妈恨死那地方了。但没人会雇我去做我喜欢的事,不是吗?上班就是这么回事,它要是真那么好,免费你都愿意。
她微微一笑,说那倒没错。窗外天空暗了下来,房车停车场那头的灯亮了起来:户外灯散发着清冷的白光,橱窗里则是暖调的黄光。服务生从吧台后出来,用抹布擦拭空桌。这个叫艾丽丝的女人盯着她看了几秒,然后看向男人。
这里的人喜欢玩什么?她问道。
跟别的地方没啥两样。附近几家酒吧。巴利纳那边有家夜店,开车大概二十分钟。当然了,还有游乐园,不过主要是孩子玩的。我猜你在这儿暂时还没什么朋友吧?
你应该是我搬过来后个聊上天的人。
他扬起眉毛。你很害羞吗?他问。
你说呢。
他们看向彼此。她现在看上去不紧张了,但有些疏离,他的目光在她脸上移动,仿佛试图得出什么结论。一两秒过去,后他似乎认为自己没有成功。
我觉得你可能有点,他说。
她问他住哪儿,他说他和朋友合租一栋房子,就在附近。他看向窗外,说从他们坐的地方几乎能看到那个小区,就在房车停车场过去一点点。他俯身靠近桌子,指给她看,然后说外面现在毕竟太黑了。反正就在那头,他说。他凑近她时,他们四目相对。
她将视线落到腿上,他坐回原位,似乎忍住一丝笑意。她问他父母是不是也住在本地。他说他母亲去年去世了,至于他父亲在哪儿,只有“上帝知道”。
当然了,他可能就在戈尔韦什么的,他补充道,他又不可能跑到阿根廷之类的地方。不过我有好多年没见他了。
听说你母亲去世了我很难过,她说。
嗯,谢谢。
我其实也有一阵没见过我父亲了。他——他不是很靠谱。
费利克斯从酒杯上抬起眼来。哦?他酗酒吗?
嗯。而且他——你懂的,他爱编故事。
费利克斯点点头。我以为那是你的工作,他说。
她听后脸很明显地红了,他似乎吃了一惊,甚至有点警觉。
很好笑,她说,不提了。你要再来一杯吗?
他们喝完第二杯酒后,又各自要了一杯。他问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她说她有个弟弟。他说他也有个兄弟。第三杯快喝完时,艾丽丝的脸泛起粉色,双眼发亮,透出醉意。费利克斯看起来和刚进酒吧时一模一样,举止和语调没有任何变化。艾丽丝的视线逐渐在四下游走,对周遭表现出更涣散的兴趣,他对她却越来越警觉专注。她摇晃着空杯子里的冰块,自娱自乐。
你想来我家看看吗?她问道,我一直很想向谁炫耀,可是没有人可以邀请。当然,我会请我朋友过来。但他们都不在一处。
在纽约。
大部分在都柏林。
你家在哪儿?他问,走路能到吗?
当然可以。事实上我们只能走路。我不能开车,你行吗?
现在不行。而且我也不能冒这个险。不过我有驾照。
你有是吧,她喃喃道,真浪漫。你是想再来一杯,还是咱们现在就走?
他对着自己皱眉,或许因为她的问题,或许因为她提问的方式,或许是“浪漫”这个词。她正埋着头在手提包里翻找什么。
行,咱们走吧,没问题,他说。
她站起来,开始穿外套,是一件米色单排扣防水风衣。他看着她挽起袖口,使两边对称。站着他其实只比她高一点。
有多远?他问。
她冲他打趣地笑了笑。后悔了吗?她问,你要是累得不想走了,随时可以抛下我回去,我习惯了。我是说,那条路我走惯了。
不是说我习惯被人抛下。当然后者也有可能,不过我不会跟陌生人坦白这种事。
对此他没有作答,只是点点头,脸上略显阴沉,带着忍耐的神色,仿佛在和她聊了一两个小时后,他注意到她容易话多,还喜欢表现得很“风趣”,并决定对此视而不见。离开时他和女服务生道了晚安。艾丽丝露出诧异的神色,回过头仿佛想再看她一眼。等他们走上人行道后,她问他是不是认识那个女人。海浪在他们身后拍打堤岸,碎成悦耳的轻响,空气很凉。
在那儿上班的那个女孩儿?费利克斯说,对,我认识她。希妮德。怎么了?
她肯定好奇你为什么会在那儿跟我聊天。
费利克斯用不带任何情绪的语气答道:我敢说她心里有数。咱们往哪儿走?
艾丽丝双手揣进风衣口袋,朝山坡上走去。她似乎从他的语气中读出某种挑衅甚至否认,而它不仅没能让她退缩,反倒让她的决心更加坚定。
怎么,你经常在那里和女人见面吗?她问。
他需要加快步伐才能跟上她。他答道:这个问题问得很怪。
是吗?我想我的确是个怪人。
我在那里见人和你有关系吗?他问。
你的事都跟我无关,这是自然的。我只是好奇。
他似乎想了想她的话,然后以安静一些、不那么肯定的语气答道:对,但我不觉得这关你什么事。几秒后他补充道:是你提议去那家酒店的。你别忘了。我并不怎么去那里。所以,我不会经常在那里见人。行了吧?
行啊,没事儿。我之所以好奇,是因为你说吧台的那个女孩儿会对我们为什么在那里“心里有数”。
好吧,我是说她会以为我们在约会,他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艾丽丝没有转过来看他,她的脸上却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或者说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兴趣。你不介意认识的人看见你和陌生人约会吗?她问。
你是说因为这个有点尴尬之类的?不,我不介意。
他们顺着沿海公路朝着艾丽丝家走去,路上聊着费利克斯的社交生活,更准确地说,是艾丽丝对此提出很多问题,他斟酌后作答,为了盖过海的响声,两人的音量都比之前大很多。他没有对她的问题表示诧异,轻松地给出回答,但都不是特别长,也没有提供任何多余信息。他说他主要和上学及上班时结识的人往来。
这两个圈子有一定重合。他没问她任何问题,或许因为之前她回答问题时有所保留,也或许他对她已经失去了兴趣。
到了,她终于说道。
哪儿?
她拉开一扇小白门的门闩,说:这里。他停下脚步,看向房子,它就立在一个带坡的绿色花园之上。窗户没亮灯,看不清房子正面的细节,但他的表情说明他知道他们在哪儿。
你住在教区神父的房子里?他问。
哦,我不知道你认识这里。不然我在酒吧就跟你说了,我没有故弄玄虚的意思。
她开着门等他进来,他跟在她后面,视线依然停留在房子旁边的雕塑上,它凌驾于他们之上,面朝大海。身侧,暗绿的花园在风中窸窣有声。她步履轻盈地走到小径尽头,在手提包里找房门钥匙。能听见钥匙在包的某处作响,但她好像还没找到。他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她为耽误的时间道了歉,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功能,照亮包的内部,为房前的阶梯投下清冷的灰光。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找到了,她说。然后她开了门。
进屋后是一个很大的门厅,红黑相间的地砖。头顶悬着一盏大理石条纹的玻璃顶灯,靠墙立着一张细长的桌子,上面摆了一只水獭木雕。她把钥匙扔到桌上,迅速地扫了一眼墙上挂的昏暗斑驳的镜子。
你一个人租这里?他问。
我知道,它确实太大了,她说,而且光暖气就要花好多钱。但它很不错,不是吗?他们甚至都不收我租金。要不要去厨房?我这就去开暖气。
他跟着她沿着门厅来到一间大厨房,一边是整体橱柜,一边是餐桌。水槽上方开了一扇窗,面朝后花园。他站在门口,她在橱柜里找东西。她转过身看向他。
你如果想坐可以先坐,她说,但要是想站也完全可以。想喝杯红酒吗?酒的话,我这里只有红酒。不过我准备先喝杯水。
你是写什么的?如果你是作家的话。
她转过身,有点困惑。如果我是的话?她说,你该不会觉得我在撒谎吧。我要是撒谎的话会编一个更好的职业的。我是小说家。写书的。
你靠写书挣钱?
她似乎察觉到这个问题蕴含的全新意义,又扫了他一眼,然后继续倒水。没错,她说。他继续看着她,然后在桌边坐下。椅子上垫了细纹毛呢坐垫。一切看上去都很干净。他用食指尖揉了揉光滑的桌布。她在他面前放了一杯水,然后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你之前进来过吗?她问,既然你知道这栋房子。
没来过,我知道它是因为我从小在镇上长大。我一直不知道里面住的是谁。
我对他们知道得也很少。是一对年长夫妇。妻子是艺术家,
我记得。
他点点头,没说什么。
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带你转转,她补充道。
他还是没说话,这次甚至连头都没点。她看上去没有为此感到不安;仿佛它验证了她心中的某种想法,当她再次开口时,她的语气依然干巴巴的,几乎带着嘲弄的口气。
你肯定觉得我一个人住在这儿脑子有问题,她说。免费住?少开玩笑了,你要是不住才有病,他答道。他满不在乎地打了个哈欠,向窗外望去,确切地说是看向窗户,因为天已经黑了,玻璃上只映出房间内部。我有些好奇,你这儿一共有多少间房?他问。
四间。
你的在哪儿?
面对这个唐突的问题,她起初没有抬眼,而是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水杯,几秒后才抬头直视他。楼上,她说,都在楼上。
你想去看看吗?
好极了,他说。
他们从桌边起身。二楼楼梯平台上铺了一张缀着灰色流苏的土耳其地毯。艾丽丝推开她的卧室门,打开一盏小小的落地灯。
左手边是一张大双人床,裸露的木地板,靠墙的一边用青玉色的砖砌了一个壁炉。右手边,一扇推拉窗面朝大海,望向黑暗。费利克斯转到窗边,凑近玻璃,身影遮住了反射的灯光。
白天从这儿看出去肯定不错,他说。
艾丽丝依然站在门边。对,很美,她说,傍晚的时候其实更美。
他从窗边转过身来,审视的目光扫过房间的其他部分,艾丽丝注视着他。
很不错啊,他总结道,相当不错的房间。你准备在这儿写本书吗?
我尽量吧。
你的书是讲什么的?
哦,我不知道,她说,关于人吧。
有点模糊啊。你写什么样的人,你这样的?
她平静地看着他,仿佛在告诉他:她知道他在玩什么把戏,
或许她甚至会让他赢,只要他遵守游戏规则。
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她问。
她波澜不惊的样子似乎让他不安,他发出一声短促尖锐的笑声。好吧,好吧,他说,我才认识你几个小时,我还没想好。
希望你想好了跟我说。
可能吧。
她一动不动地在房间里站了几秒钟,他又转了转,假装四处打量。他们此时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尽管两人都说不出他们是怎么知道的。她公允地等他四下张望完,直到后,他或许再也没有气力拖延那不可避免的结局,于是向她道谢告辞。她陪他走下楼梯,没完全下去。她站在台阶上,看他走出门。这种事可能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他们事后都觉得很糟,但谁都不确定这一晚为什么以失败告终。她独自一人,在楼梯上停留了片刻,回头看向楼梯平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卧室门没关,透过扶手栏杆,能看到一块白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