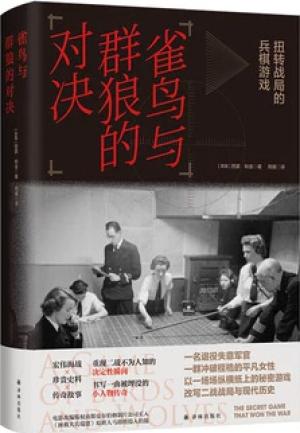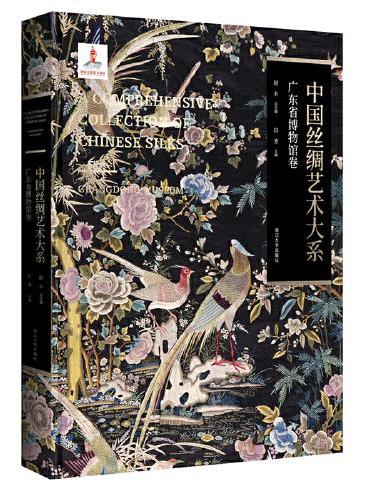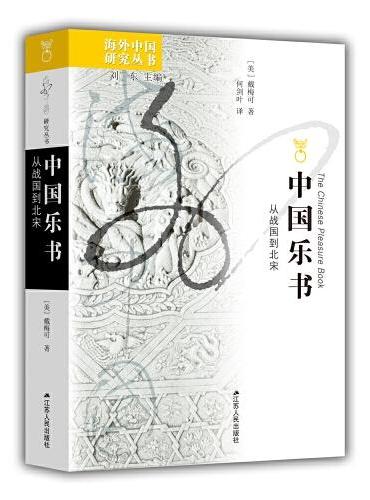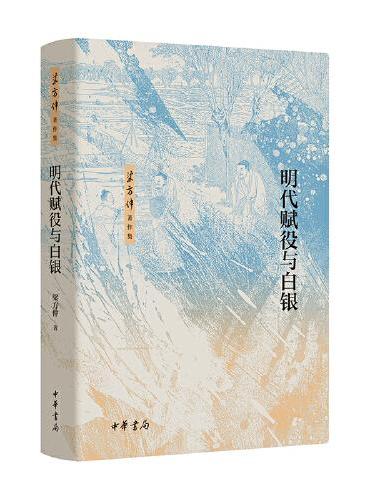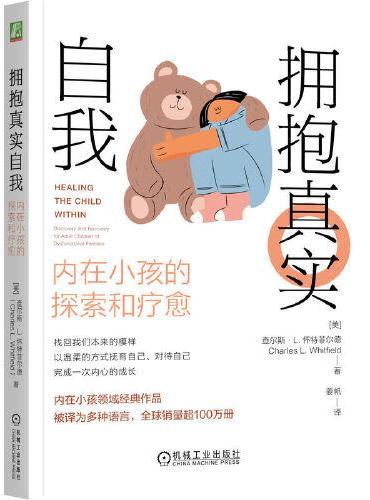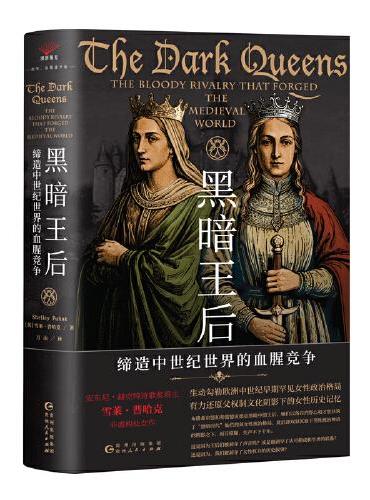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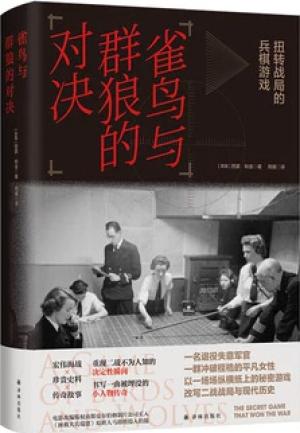
《
雀鸟与群狼的对决:扭转战局的兵棋游戏
》
售價:HK$
96.8

《
老年膳食与营养配餐 第2版
》
售價:HK$
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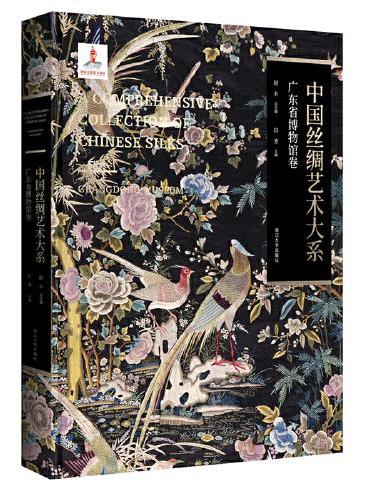
《
中国丝绸艺术大系·广东省博物馆卷
》
售價:HK$
10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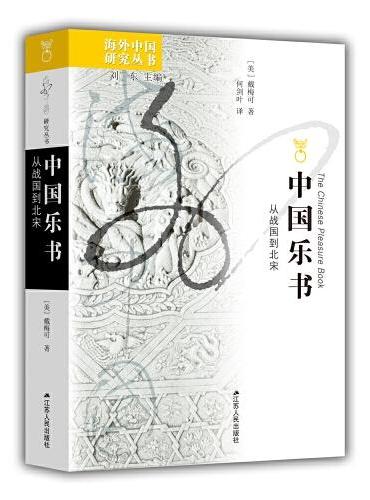
《
海外中国研究·中国乐书:从战国到北宋
》
售價:HK$
16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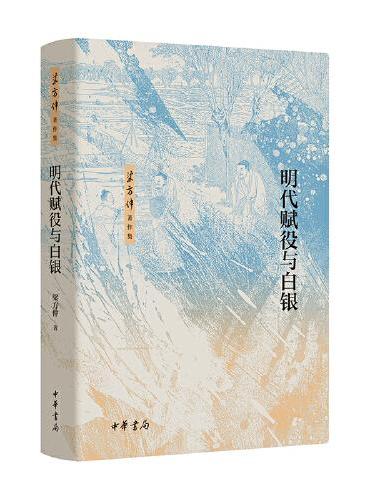
《
明代赋役与白银——梁方仲著作集
》
售價:HK$
79.2

《
量子纠缠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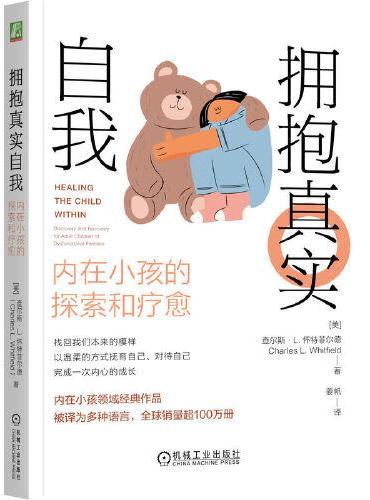
《
拥抱真实自我:内在小孩的探索和疗愈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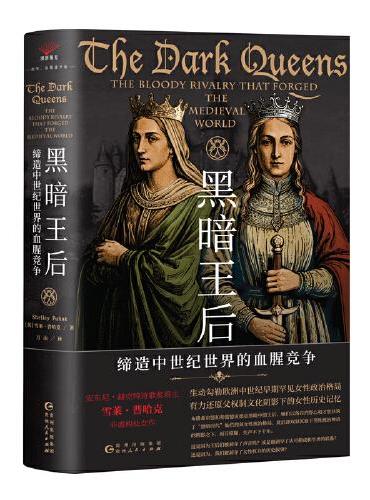
《
黑暗王后:缔造中世纪世界的血腥竞争
》
售價:HK$
129.8
|
| 編輯推薦: |
*俄罗斯传奇剧作家阿尔布卓夫六部经典剧作的权威中文译本
*轻描淡写地书写沉甸甸的时代,歌颂可爱又青春的人儿
*《老式喜剧》《我可怜的马拉特》几度被人民艺术剧院摆上舞台
最大概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断地接近你。(《老式喜剧》)
*不过你别怕,别怕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可怜的马拉特》)
*青春就过去了,可爱的、好笑的青春!(《塔尼娅》)
|
| 內容簡介: |
|
《阿尔布卓夫戏剧六种》选录俄国剧作家阿尔布卓夫六部代表剧作《老式喜剧》《我可怜的马拉特》《塔尼娅》《伊尔库茨克的故事》《阿尔巴特旧区的传奇》《漂泊的岁月》。阿尔布卓夫是苏联时期最受欢迎的剧作家,他善于将时代洪流同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使他的剧作在国内常演不衰。
|
| 關於作者: |
阿尔布卓夫(1908-1986)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阿尔布卓夫,苏联剧作家。出生于莫斯科贵族家庭,1917年因革命爆发成为流浪儿,由教养院收留。11岁在彼得堡大剧院观看席勒名剧《强盗》后痴迷戏剧。毕业于列宁格勒戏剧学校,代表剧作有《塔尼娅》《老式喜剧》等,1980年获苏联国家奖。
译者简介:
白嗣宏
1937年出生,笔名石公。1956年赴列宁格勒大学(现圣彼得堡大学)俄国戏剧文学专业学习,1961年回国。现居莫斯科。著名翻译家、戏剧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俄罗斯电影家协会会员。致力于中俄文化交流,创办莫斯科华人华侨联合会。
|
| 目錄:
|
老式喜剧 1
我可怜的马拉特 79
塔尼娅 177
伊尔库茨克的故事 281
漂泊的岁月 385
阿尔巴特旧区的传奇 489
附?录 571
译后记 591
|
| 內容試閱:
|
《老式喜剧》第一部
一 她的第六天
[这个故事记得是一九六八年七月底,在里加海滨开始的。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疗养院的总医师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的男子,跷着二郎腿,坐在藤椅上。在接待病人的时间里,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不大喜欢待在自己的办公室——他只是在阴雨天才这样做,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他喜欢望着蔚蓝色的苍穹,时而放下公务,细心地欣赏周围的花草树木。他叫人把一套简单的轻便家具布置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前,一棵高大的栗树下。这样,就把这一角变成办公室的夏季分部。
话说在那个值得怀念的早晨,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正在翻阅公文,莉吉娅·瓦西里耶夫娜第一次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女士,遗憾得很,我不能说她还年轻。然而,如果我们望着一位女子,猜到她年轻的时候是多么迷人,难道年龄还会那么重要吗?诚然,假如仔细观察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生活并不一直是吉星高照的,而现在要交好运则更非常事。尽管如此,当她出现在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面前的那个早晨,她的衣着不乏雅致……我重说一遍——不乏雅致,尽管有点花里胡哨。
她看到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后,仔细地端详了一番,然后用略带傲慢的口气同他谈话。
她 我好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您的大名是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
他 的确如此。
她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您肯定是本疗养院的总医师了。
他 这一点也不违背事实。
她 既然如此,那我就更无法理解,您为什么要笑嘻嘻的。
他 虽然令人奇怪,但我也不明白。
她 可是您仍然笑嘻嘻的。
他 (沉下脸来,一副严肃的样子)请注意,闲话到此为止。
她 我在办公室里没找到您。我遵照值班护士维尔塔·瓦吉卡的劝告,下楼到花园里来散散心。找到您我很高兴。
他 请原谅,我除了接待时间,一般喜欢待在办公室窗外的花园里。请坐。
她 谢谢。(坐下)不过,您原可以早一点想到请我坐的。
他 您说得对。但是我没有立即想到这一点。
她 为什么呢?
他 因为我一见到您,就感到非常惊讶。
她 (冷淡地)您惊讶什么呢?
他 我自己也不知道。虽然我确实十分惊讶。我甚至觉得,我们过去就认识。
她 (同样严厉地)难道就是这一点使您发笑吗?
他 大概是的。
[停顿。
她 您为什么不说话呀?
他 您认为我应当说话吗?
她 当然该您说。因为是您找我来谈话的。
他 请原谅……您在我们疗养院休养吗?
她 (骄傲地)我还以为您知道呢。
他 不过……我是想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她 热贝尔·莉吉娅·瓦西里耶夫娜。
他 (仔细地从头到脚看了她一遍)热贝尔?就是她?
她 (矜持地)就是她?如何理解这句话?您承认吧,这句话听起来是有点怪。(哼了一声)就是她!
他 请原谅,热贝尔同志。但是,我是请您早上十点钟来的。随您怎么说,现在可已经是下午一点多了。
她 这算不了什么!难道这有什么关系吗?我到底来了。
他 (小心翼翼地)当然,这使我很高兴。但是,十点钟您为什么没来?
她 时间不合适。十点钟的时候我要喂海鸥吃东西。(严厉地)我每天早餐之后就喂它们。
他 我还是认为,您迟喂它们一次也没什么关系。
她 (不容置辩地)不,这样就是违反作息制度。
他 有人给您规定这个制度吗?
她 当然不是。我一切都是由自己做主的。
[停顿。
这是棵什么树?
他 (惊奇地)栗树。
她 这些小树呢?
他 (更加惊奇地)这是金合欢。
她 我必须把这些树都记住。唉,这些年来我的生活远远离开了大自然。我常弄错花儿和鸟儿的名称。根本不记得它们的名称。现在我应当想起它们的名称。但是,您为什么老是不说话?我来了,同您一起坐在这儿,浪费时间——而您却不说话……好像躲着我似的。难道是我的心电图不太妙?验血的结果很糟?或者是别的烦恼事?您别瞒着我。
他 (急忙地)不是,不是……暂时没有任何值得担心的材料。问题完全不在这儿,热贝尔同志。您知道吗……我们的疗养院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个治疗机关……这里不是旅店,甚至也不是休养所。这里必须保持绝对的安静和秩序。而……
她 我对您的话很感兴趣,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
他 您的表现,使周围的人很有意见。您在我们这儿才待了六天,我们收到的批评意见却有一大堆……请相信,我们疗养院从来没有过这样不寻常的女病号。
她 首先,我要指出,我根本不喜欢“女病号”这个词儿。这个术语必然会使每个正常的、怀着一颗纯洁真诚的心到贵院来的人感到苦恼。
他 您知道……这个术语不是我规定的……不过制度如此。
她 (轻蔑地)“制度”!……制度通常是由那些无所事事的人规定的。
他 请原谅,我不这样看……
她 都指责我些什么呢?
他 首先说您妨碍周围的人睡觉。
她 (冷冰冰的口气)我倒是怎么妨碍周围的人睡觉呢?
他 您躺在床上,半夜里忽然大声朗诵起诗来,弄得您的邻床病人感到非常突然。
她 难以想象!您看,她们不喜欢我朗诵诗!难道她们以为打鼾要好一些吗?您知道的。我的邻床——我们就叫她X女公民吧——她的鼾声如雷,连我床头上的花儿都直打战——请您相信——全是她的鼾声震动的……同一时刻,我的另一位邻床——我们就叫她Y女公民吧——在梦中又是呻吟,又是哼哼,简直使人觉得她不久于人世了……但是,您看,我毫不灰心丧气,老老实实地忍受这些呻吟。
他 好吧,就算是这样……但是还有,天不亮您就突然唱起歌来,把周围的人都吵醒了。
她 难道您认为,在阳光明丽的夏天早展,能忍住不唱歌吗?请您注意,阴雨天我是不唱歌的,我也不打算唱歌。同时,我唱歌的声音很低,勉强听得见。(轻声唱道)
我漂泊在天涯海角……
旱獭随我到处奔跑……
您自己看吧,这样的歌声能吵醒人吗?
他 您唱得十分动听,但是您得注意,有人睡觉特别容易惊醒。难道我们有权为了满足个人的愿望而去剥夺他人清晨的美梦吗?
她 没什么,没什么——她们少睡一会儿没什么!再说,什么都不像酣睡那样会缩短我们的生命。这样会错过大量有趣的事。您总不会否认,一般来说,生活在世上是很有趣的。
他 当然,这一切都对,不过清晨的美梦……
她 (打断他)您再想想,我的邻床们尽管早就待在这儿,可是一次——您明白吗——一次都没欣赏过日出!而照我了解到的情况看,海上日出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印象。
他 我完全同意您的话。但是,照受害者的说法,您为什么要在深更半夜从窗户往花园里跳,而过一会儿,您又采用同样方法回到病房里?许多被惊醒的人耐心地等待您的归来,为的是等您进来后再睡一会儿。但是您有时候大约过一个半小时才回来,这样您就更把她们害苦了。
她 那是因为值班护士维尔塔·瓦吉卡夜里要锁上大楼的门。而我呢,有时渴望半夜到花园里去观赏月色;踱到海滨,单独同大自然待在一起……您要理解我,我是一个城里人,多年来一直没见到过大海,没有机会在树林里散步……这里周围的一切完全使我沉醉了……(她忽然为自己的倾诉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大概您对这一切都是无动于衷的。这不是已经有半个小时了,您一直从小盒里拿糖吃,吃得忘了神。您继续吃吧,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看来这是您唯一的特长。
他 (深受侮辱)对不起,不过……
她 我可以提出一个替自己开脱的理由——我跳窗户是极其小心的。十分谨慎。
他 遗憾的是,我掌握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昨天夜里,您从窗户跳下去的时候,打翻了三瓶酸牛奶。据目击者说,三瓶都打得粉碎。这样您不仅把您病房里的人吵醒了,而且吵醒了整整一层楼的人。
她 请相信我,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今后我一定万分小心地跳窗子。
他 真见鬼!同您谈话实在是够困难的。
她 (同情地)许多人都这样对我说过。但是我完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在和人交往的时候,一般是满怀善意的。
他 哎,得了吧!您具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奇才。
她 自然是这样:我总是拼命赶上时代的步伐。您对我还有什么意见,大夫?
他 您知道……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哎……病员……我们进行了一种试验,请病员们填写一张简表。直截了当地说吧,您填的内容弄得我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先说“年龄”这一栏吧。您画了一道杠。
她 (生硬地)我认为向妇女提这种问题是不妥当的。真的,您可以提别的问题。年龄——这纯粹是每个苏联公民的个人问题。并且我坚信,在这种问题上,国家替每个同胞都保密。而且一般来说……为什么要有这种不健康的好奇心?比如我就不问您贵庚多少。
他 (骄傲地)您本来可以问的。我同您这位妇女不一样。您不知出于什么莫名其妙的原因,要隐瞒自己的年龄。我可以坦率地回答您——我很快就满六十五岁了。
她 真的吗?
他 什么——真的吗?
她 我以为您还很年轻。
他 哼……您是这样想的吗?(又变得严厉起来)无论如何,确实如此。
她 那好吧,您的坦率很合我的心意。我也尽量以坦率相待——我还不到八十岁。我想,您满足了吧?
他 (生硬地)真的,我不明白,满足我哪一点?然而,我们谈下去吧。在“您的职业”这一栏里,您填得太笼统:“我在杂技团工作”。
她 我确实是在那里工作。在杂技团。
他 担任什么工作?您的职业是什么?
她 您认为这有助于治疗动脉硬化吗?您的医生们总算在我身上找到这个病了,但是,我的动脉根本就没有硬化。
他 哎,我真的要失去耐性了。(暴怒地)您的职业是什么?您在马戏团里干什么,热贝尔同志?翻筋斗?敲鼓?活吞青蛙?
她 您这种不健康的好奇心总有一天要毁了您。(突然哧哧地笑了)我表演魔术。像我这样年龄的女人还能干些什么呢?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摊开双手)我表演魔术。我想这个问题就谈到这里为止,行吗?
他 那好吧……就算是这样。还有,您为什么没有填“婚否”一栏?
[停顿。
您结婚了?
她 要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有时并不那么容易。
他 (不耐烦地)真见鬼……您到底结过婚没有?
她 (沉默片刻)您知道吗,这个问题使您这样激动,真有点可爱。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使我感动。那好吧,只好向您和盘托出,我根本没结过婚。根本没有。现在您满足了?您没别的什么新问题了吗?您问题提完了?罗吉昂·尼古拉耶维奇?那好吧,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您已经使我腻烦透了。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使我厌烦。您尽提些不知深浅的问题,拼命想知道我结过婚没有?谢天谢地,没有。而您自己竟然连白大褂都没穿。(严厉地)您应当穿着白大褂提问题,而不应该穿这件没熨平的西服,上面连扣子都不全!真可怕——您叫我来谈严肃的事,而您自己却一直在吃糖。这还算是苏维埃医生——可耻可悲!我不愿意再看见您。
他 (大为生气)原来如此——够了!……她不喜欢我吃糖……您知道吗,我一直在吃糖,是为了改掉吸烟的坏习惯。您简直是个好斗嘴的女人……已经半个小时了,您一直在狡猾地挖苦我。够了!要么您重填一份表,要么我请您马上出院!
她 (庄重地)您如果再不停止胡闹,我就叫警察来。(从他的小盒里摸出一块糖,放到嘴里,关上盒子,优哉悠哉地下)
他 (惊慌地望着她的背影)一个多么怪的女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