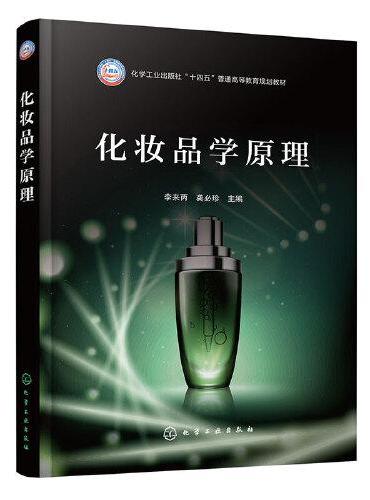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我们身边的小鸟朋友:手绘观鸟笔记
》
售價:HK$
80.3

《
拯救免疫失衡
》
售價:HK$
57.3

《
收尸人
》
售價:HK$
74.8

《
大模型应用开发:RAG入门与实战
》
售價:HK$
91.8

《
不挨饿快速瘦的减脂餐
》
售價:HK$
68.8

《
形而上学与存在论之间:费希特知识学研究(守望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
售價:HK$
113.6

《
卫宫家今天的饭9 附画集特装版(含漫画1本+画集1本+卫宫士郎购物清单2张+特制相卡1张)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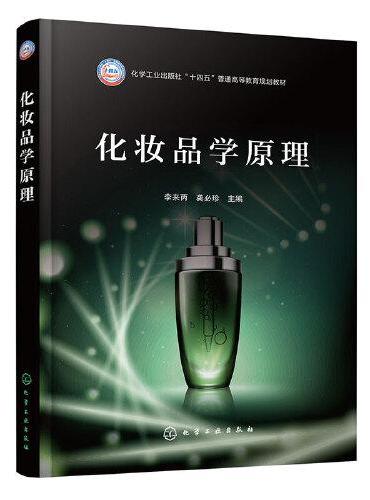
《
化妆品学原理
》
售價:HK$
57.3
|
| 編輯推薦: |
《现代法国的起源》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人类文明史上百大经典著作”之一;
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
“红楼梦”式的全景式描写,鞭辟入里的社会分析,深层次解读社会转型的艰难与曲折、从改革到革命的狂风暴雨式的突变;
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兰西帝国,为什么在一夜间迅速垮台?为什么繁荣与变革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青年学者黄艳红翻译,国内首次推出中文无删节平装普及全译本;
国外政商学界精英人士必读书
全书共5卷,预计年末全部出版完成。
|
| 內容簡介: |
|
《现代法国的起源》分为三部分,即旧制度、大革命、新秩序,本书即第一部分,讲述的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社会总体状况,并以“红楼梦”式的全景式手法,描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表现,其中包括高层、中层、下层、公共知识分子、军队等社会群体的活动状况,生动地再现了大革命爆发之前,即将喷发的火山潜伏在一潭死水下的沉闷肃杀的社会态势;或者说,本书描述是,一个曾经称雄欧洲大陆的强国,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走到了暴力革命的临界点。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姊妹篇,不同之处在于,《旧制度与大革命》采用的是理论分析的方法,更像社会分析报告;而本书采用的是实证主义方法,除了社会分析,还有大量真实而令人震惊的社会情境叙述,它不是自问自答式的告诉读者“为什么”,而是通过叙述让读者自己明白“为什么”。
|
| 關於作者: |
|
伊波利特 泰纳,19 世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主要作品有《英国文学史》 《现代法国的起源》等。在历史学领域,泰纳倡导历史学的科学化,是法国实证主义史学的重要代表;其代表作《现代法国的起源》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绚丽的修辞技艺著称,对后世历史学和法国政治思想史有重大影响。
|
| 目錄:
|
第一卷第一章:特权的起源
第二章:特权
第三章:特权者应负的地方职责
第四章:特权以普遍的服务为条件
第二卷第一章:旧制度风尚的本质特点
第二章:沙龙生活
第三章:沙龙生活的苦恼
第三卷第一章:革命思想的形成
第二章:第二个要素:经典精神
第三章:两种元素的结合
第四章:未来社会的构建
第四卷第一章:这种哲学在法国成功,在英国不成功
第二章:法国的公众
第三章:中产阶级
第五卷第一章:农民和农村
第二章:苦难的主要原因:税
第三章:不安定的下层
第四章:军队
第五章:小结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特权的起源
Ⅰ. 教士的服务和酬劳。Ⅱ 贵族的服务和酬劳。Ⅲ.国王的服务和酬劳。
1789年,三类人,教士、贵族和国王,占据国家的显赫位置,这种位置带给他们各种好处:权威、财产、荣誉,至少是特权、豁免、恩泽、赏赐、优待,等等。如果说他们很久以来就处在这一位置上,那是因为他们很长时间里配得上享受这些好处。实际上,他们以长期艰巨的努力,相继奠定了近代社会的三大基础。
Ⅰ
三个层层叠加的基础中, 最古老最深厚的是教士的作品: 在1200多年的时间里,教士一直为此劳作着,他既是建筑师又是泥瓦匠;一开始他独自劳动,随后几乎仍是在独自劳动。在最初的4个世纪里,他创造了宗教和教会:请掂量掂量这两个词的分量以感受其全部的影响力。一方面,在一个以征服为基础、坚硬冷漠有如青铜机器的世界上,人虽然注定会因为这个世界的结构而丧失行动勇气和生活意愿,但教士仍在宣扬“善的音信”,在许诺“神的王国”,在劝诫人们驯服地依从天国之父的指引,在召唤耐心、温和、谦卑、克己、仁爱,他为栖身于罗马地牢中的窒息之人打开了唯一尚能呼吸和瞥见日光的出口:这就是宗教。另一方面,在一个人口日渐稀少并逐步解体、注定要受尽蹂躏的国度,教士建立起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它受纪律和法规的指引,团结在同一个目标和同一个信念周围,它的基础在于首领的虔诚和信徒的服从,破败的罗马帝国曾致使蛮族从它的各个缺口蜂拥而入,如今唯有这个社会能历经这一洪流的洗礼而延续下来:这就是教会。在这两个最初的基础之上,教士继续着建设工作;从蛮族入侵开始之后,在500多年的时间里,他拯救了尚能拯救的人类文化。他迎合了蛮族人,或者说在蛮人到来之后就立刻争取了他们;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只需一个事实就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大不列颠像高卢一样拉丁化了,但它的征服者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都是异教徒,艺术、产业、社会、语言,统统被摧毁了;整个部族被屠杀或逃亡,剩下来的只有奴隶,即使他们留下了痕迹也要去猜测,他们堕入了牲畜般的状态,从历史中消失了。欧洲也会是这样的命运,如果不是教士迅速减轻欧洲到处盛行的粗野暴行的话。
在身披镀金斗篷的主教面前, 在“ 形销骨立、苍白孱弱” 、“比蜥蜴还要肮脏、麻点还要多”的修士面前,皈依基督的日耳曼人就像站在巫师面前一样害怕。在狩猎和酗酒之后的平静时刻,对神秘而崇高的彼岸的朦胧猜测,对未知的正义的模糊认知,在莱茵河那边的森林中就已然具有的粗浅意识,此刻都因为骤然的惕厉而苏醒了,那种惕厉带有恐吓性的半异象的特征。在侵犯圣殿的时候,他们会想自己是否会跌倒在门槛上,会不会天旋地转、脖子拧断。当他们深信自己会有麻烦时,就会收手,放过那个受教士庇护的地区、村庄和城市。原始的怒火和贪婪产生的兽性冲动曾驱使他们去杀人和抢劫,但是,在得到满足之后的厄运与病痛的日子里,他们会听从姘妇或妻子的劝告,会痛悔前非,会双倍、十倍、百倍地补救,会大施捐赠和豁免。因此,在所有地方,教士都在守护和扩大着失败者和被压迫者的避难所。另外,在身披裘皮的国王身边,头戴冠冕的主教、前额剃度过的僧侣与长发披肩的武士首脑一起出席会议,唯有他们通文墨、谙辩论。他们担任秘书、顾问、神学家,参与法令制定工作,因而能涉足政治,他们通过斡旋调停,而在混乱无序的汪洋大海中,建立起些微的秩序,让法律变得更为合理和人道,恢复并维持着信仰、正义、财产,特别是婚姻制度。这种断断续续的、很不完善的秩序,使得欧洲没有陷入蒙古式的大混乱中,而这种秩序肯定应归功于教士。直到12世纪末,如果说教士还对君主们有很大的影响,那主要是为了抑制君主及其下属的粗野脾性、血腥的叛乱以及无法遏制的野蛮行径的发作与反复:这类情形会导致社会的解体。然而,在教堂和修道院里,教士们保存着人类过去的成就,如拉丁语、基督教文学和神学,部分异教的文学和科学、建筑、雕刻、绘画、用于宗教崇拜的手工业技艺,以及更为珍贵的东西:这就是给人提供面包、衣着和住房的工艺,尤其是所有人类成就中最为宝贵、最能抗拒野蛮人的掠夺、懒惰和流浪天性的东西,即定居和劳动的习性。罗马的苛捐杂税、巴高达的叛乱、日耳曼人的入侵、盗匪的恣意横行,致使乡间人烟稀少,正是本笃会的僧侣们在荆棘和刺藤之中用树枝搭起了窝棚,而窝棚四周曾经畦垄整齐的土地,如今已是灌木丛生。僧侣与伙伴们一起披荆斩棘、营建修造,他们驯化了半野蛮的牲畜,建起了农庄、磨坊、冶炉、烤炉、制造鞋和衣服的作坊。根据教规,他们每天读书两小时,体力劳动七小时,只有在绝对必须之时方可饮水进食。这种劳动是合理的、自愿的、自觉的,并着眼未来,因而比俗人的劳动更有成效。因为那一套克制、统一、节俭的体制,他们比俗人消费得少。这就是为什么在俗人破败衰微的地方,他们却能维持下来甚至能兴旺发达。他们收容不幸者,养育这些人,给他们活儿干,让他们结婚;乞丐、流浪汉、逃亡的农民都会聚到避难所的周围。他们的营地逐步变成了村庄,接着成为小集镇:当收成有指望时,人们就会劳作,当他们觉得能够养育孩子时,他们就会成为一家之主。于是新的农业和工业中心形成了,它们也成为新的聚居中心。
除了身体所需的面包,还有灵魂的面包,它同样必不可少;因为在提供食物的同时,还应赋予人生活的意志,至少是赋予能让他忍受生活的逆来顺受的心境,以及能给他带去虚幻的幸福感的动人与诗意的梦想。直到13世纪中叶,教士几乎是唯一能提供这类东西的人。靠着无数的圣徒传记,靠着大教堂和大教堂的结构,靠着宗教雕塑和它们的表情,靠着祭礼和其中尚能明了的意思,教士将“神的王国”变得具体可感,并在现实世界的尽头树立起一个理想世界,就像糊满烂泥的围墙的尽头耸立着一座华丽的黄金楼阁。正是这个甜蜜而神圣的世界收留着那些渴望宽容和温情的悲伤灵魂。也正是在这里,迫害者在逞强时会受到无形的打击:野兽变成家畜,林中野鹿每天上午都会前来,自己挽上圣徒的犁具;这时原野为它们绽放了鲜花,仿如新的天堂,它们只在想死的时候才死去。这些生灵会给人以慰藉,它们唇齿之间有着无法言表的温情,流淌出善意、虔诚和宽恕;它们抬眼向天国望去,看见了神,并且毫不费力地升入光明之中,坐到神的右侧,这一切就像梦境一般。在一个暴力支配一切的世界中,这种天国传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如要忍受生活,就应该设想另一种生活,并使其在灵魂之眼中显得清晰可见,就像肉眼见到的第一种生活一样。在12个世纪多的时间里,教士就以这种设想出来的生活哺育人们,根据他所得到的回报的分量,我们就能判断出人们对他的感激之深。教宗在200年中曾是欧洲的独裁者。他发动了十字军行动,罢黜国王,处置列国。某地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成为拥有主权的君主,另一地他们又是王朝的庇护者和真正的奠基人。欧洲13的土地、12的收入、23的资本都掌握在教会手中。但不要认为人会盲目地感激,会在没有合理动机的情形下捐赠,因为人太自私,嫉妒心太强。任何机构,不管是教会的还是世俗的,任何教士,不管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与其相随40代的人们对它们的判断不会错;人们只会根据它们提供的服务来奉献自己的意愿和财产,无限的忠诚可能意味着无法估量的善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