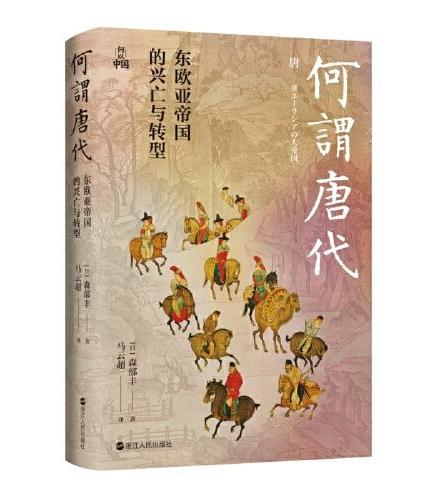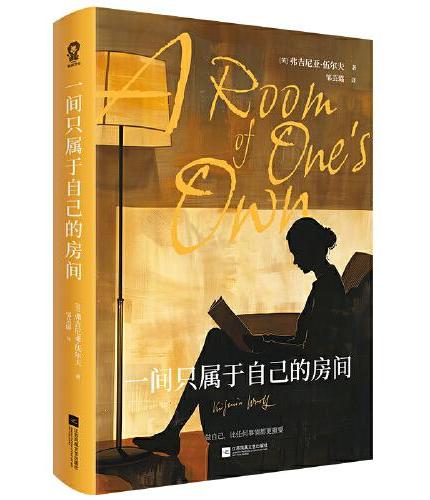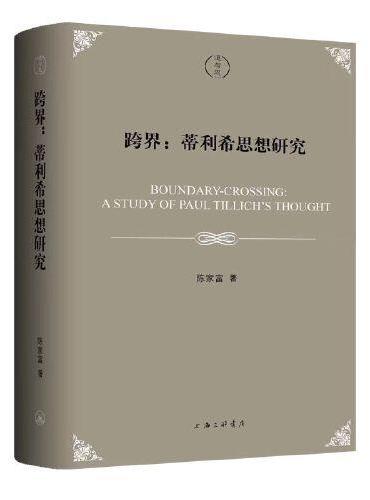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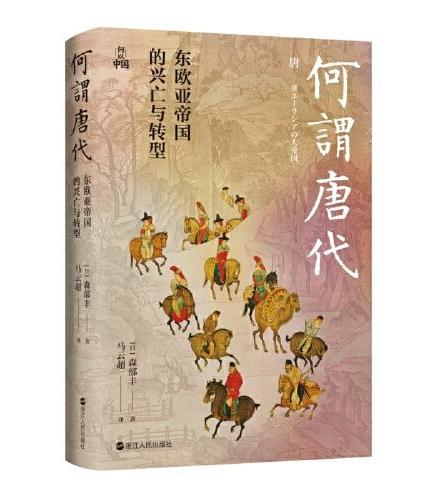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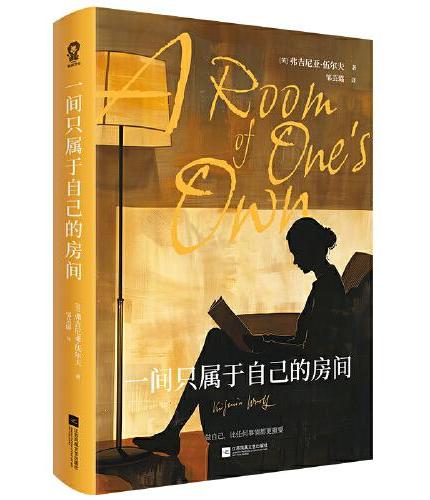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5.8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7.8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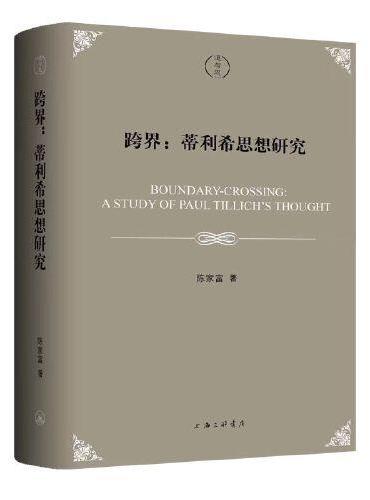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5.9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HK$
115.0
|
| 編輯推薦: |
|
《文坛逸话》一书记录的多为作者石湾先生亲身经历,披露的多为文坛已被遗忘或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真实生动,极具史料价值,可以让广大读者了解一些文坛著名作品及文人背后的故事:如《黄河大合唱》歌曲的创作由来,《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小说《青春之歌》、《李自成》的出版波折,莫言的**本书如何出版的,高晓声如何在“文革”后重返文坛,刘白羽在“文革”后的忏悔与反悔,杨苡与巴金先生几十年的相交情谊等。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开卷书坊第四辑”之一,“开卷书坊”为当今知名学者文人的散文小品系列丛书集。“开卷书坊”丛书以营造“书香中国”氛围、弘扬书香文韵为宗旨,第一辑八本、第二辑十二本、第三辑十本分别于2011年、2013年、2014年在上海书展亮相后,得到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并逐渐形成了应有的品牌效应。
《文坛逸话》一书收录的稿子为作者石湾先生自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岗位退休后十多年来已发表或出版过的文章,内容主要为回顾文学编辑生涯和缅怀作家、艺术家朋友,披露了有关周扬、郭沫若、田汉、光未然、刘白羽、梅娘、张庚、杨沫、萧也牧、白桦、杜高、陆文夫、高晓声、莫言、张炜、雷抒雁、遇罗锦、杨苡等诸多文化名人或已被遗忘或鲜为人知的逸闻轶事,这些篇什所记录的文坛往事大多皆为作者亲临亲历,真实生动,独具史料价值和阅读品位。
|
| 關於作者: |
|
作者石湾先生本名严儒铨,江苏武进人,出生于1941年,196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曾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文化部艺术局、北京京剧团从事戏剧等专业创作。先后曾在《新观察》、《中国作家》杂志担任编辑、记者,1985年任作家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1992年创办《作家文摘》,1997年至2004年任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昆曲《春江琴魂》(与人合作),歌剧《甜嫂》,诗集《鲜红的领巾》,报告文学集《春光属于你》、《无花果》、《丽人行》、《中国出了个童话大王》,散文随笔集《维纳斯的诞生》、《人说我像赵忠祥》、《〈作家文摘〉里的春雨秋风》、《梦里情怀》、《生为男人》、《母亲的爱》、《人生如歌》、《昨夜群星灿烂》、《真情永远年轻》、《记忆常新》、《向世界微笑》及传记《红火与悲凉——萧也牧和他的同事们》等十余部作品,所编《祖国之恋》获全国首届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
|
| 目錄:
|
偶见梅娘
何来“驴在叫”
也说京城名编
“这个女人很刁”
从俞珊说到田汉与江青的恩仇
远飞的不死鸟
《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
《青春之歌》的出版波折
周扬晚年出版的两本书
张炜的愚公精神
刘白羽的忏悔与反悔
一个名叫齐琪的德国读者
九十不留书
陆文夫受茅盾先生赞赏前后
想起陈恭禄先生
莫言的第一本书
高晓声与丁保林
雁过声犹在
“利令智昏”
《青年爱情诗抄》编选前后
光未然与冼星海
失眠及应对下联
《反思郭沫若》的意外遭遇
杨苡:爱做梦的青青者
还你一个真实的杜高
不该写错的挽联
张祖道:中国纪实摄影的先行者
|
| 內容試閱:
|
何来“驴在叫”?
读今日《文汇报》,见笔会副刊上有篇题为《“马在叫”与“驴在叫”》的文章,甚是醒目。此文转引了陈为人《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的一段文字:“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唐达成,曾听张光年回忆过这句歌词修改的情节,依稀记得是著名诗人贺敬之看了他写的初稿之后,认为‘驴的形象稍逊雅观’,建议将‘驴在叫’改为‘马在叫’。”作者在议论了一番将“驴在叫”改为“马在叫”如何“很好听很美感”、“确实是再恰当不过”之后,还着意问了一句:“不知张光年当年是否感谢过这位‘一字师’?”
贺敬之果真是张光年写《黄河大合唱》时的“一字师”吗?稍了解一点这两位大诗人历史的人,恐怕都不敢信以为真。经历了五十年文坛风雨的唐达成,无论对张光年还是贺敬之,应该是了解都很深的,决不可能“依稀记得”这样无中生有的“情节”。
光年同志在世时,为编辑出版他的《光未然诗存》,我曾多次拜访他,每次谈诗论词,也都要说到《黄河大合唱》。当时,他夫人黄叶绿正在编选《〈黄河大合唱〉纵横谈》一书,也曾征询过我的意见。因此,我对《黄河大合唱》诞生的全过程至今仍“依稀记得”。恰好我手头亦有《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便翻出黄叶绿赠我的《〈黄河大合唱〉纵横谈》(新华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对照着看,事实究竟如何,就一清二楚了。
先让我们来看光未然写成《黄河大合唱》初稿的时间。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一文中记述:“一九三八年秋冬,我和抗敌演剧队第三队同志们一起,经常在大西北的黄河两岸行军。在敌后游击根据地活动。中国雄奇的山川,游击健儿们英勇的身姿,时刻强烈地感动着我,我在心头酝酿着一个篇幅较大的朗诵诗《黄河吟》。稍后在延安治病写诗的时候,接受星海和演剧三队同志们的建议,改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黄河吟》确实是“吟”出来而不是“写”出来的,即他躺在病床上口授,是由演剧队员胡志涛笔录下来的。因为光未然说的“治病”,实际是疗伤。当年与光未然在黄河上“同舟共济”的邬析零,曾在《〈黄河大合唱〉的孕育、诞生及首演》一文中回忆:“光未然同志在山西汾西县勍香镇的一次归途中,不慎坠马,左臂骨折,再次渡过黄河,行程七百里,他被直接送往边区和平医院治疗,他躺在担架上,不断构思创作”。而《“马在叫”与“驴在叫”》一文却想当然地说:“由于战火纷飞,当地的马都入伍打仗去了,只有驴在山道上奔波,为前线和后方立下‘汗驴功劳’。驴的嘶叫与狂风的怒吼和黄河的咆哮混合在一起,组成惊天动地的‘交响曲’,张光年因此信笔写下‘风在吼,驴在叫,黄河在咆哮’……”仿佛是亲眼得见,说得如此“逼真”。殊不知光未然当年是骑着马在黄河两岸行军!怎么会“只有驴在山道上奔波”呢?更何况,懂艺术的人都会明白,这歌词里“马在叫”的“马”已是典型形象,代表着中华大地上的所有牲灵在向日寇发出愤怒的叫声。
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一文中接着写道:“一九三九年二月的一个晚上,延安交际处一个宽大窑洞里,抗战演剧第三队三十位同志共度愉快的农历除夕,我应邀从二十里铺的医院赶来参加这个晚会。星海同志也应邀参加了。在明亮的煤油灯下,我站起来作了几句说明,然后很带感情地一气朗诵了全部四百多行的《黄河》歌词。同志们以期待的眼光聚精会神地谛听着。掌声刚落,星海同志霍地站起来,把歌词抓在手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冼星海在《我怎样写〈黄河〉》一文中则说:“《黄河》的歌词虽带文雅一点,但不会伤害它的作风。它有伟大的气魄,有技巧,有热情和真实,尤其是有光明的前途。而且它直接配合现阶段的环境,指出‘保卫黄河’的重要意义。它还充满美,充满写实、愤恨、悲壮的情绪,使一般没有渡过黄河的人和到过黄河的人都有一种同感。在歌词本身已尽量描写出数千年来的伟大黄河的历史了。”于是,他从3月26日开始谱曲,到31日就完成了,仅用了短短6天时间!
再让我们来看《黄河大合唱》公演的时间。据《星海日记》,那是四月十三日“下午七时在陕公(大礼堂)开延安第一次音乐大会”,压轴的节目就是《黄河大合唱》,由邬析零指挥,光未然亲自担任朗诵。关于首演效果,《星海日记》写道:“《黄河》因‘第三队’女声独唱走了音,给观众不好印象。整个曲子,他们觉得很雄伟。”第二次演出,是五月十一日,在“鲁艺”周年纪念的音乐晚会上,合唱团有一百多人,伴乐队,冼星海亲任指挥。《星海日记》的记载是:“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王明,康生都跳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其演出盛况,贾漫在《诗人贺敬之》(大众文艺出版社二000年一月第一版)一书里也有描写:“当延安礼堂舞台上唱起《保卫黄河》的第一段合唱以后的轮唱时,台下所有的听众一同唱起来:‘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有意味的是,贾漫在形容这一“中国新音乐有史以来空前的壮观”时,接着写道:“当唱到‘风在吼,马在叫’,台下的人都激动得站了起来,确确实实是黄河在咆哮,珠江在咆哮,黑龙江在咆哮……因为台上台下哪里的人都有,别说是东北人,广东人,还印尼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等等许多国家的华侨。”请注意,文中是“马在叫”,而不是“驴在叫”;也请注意,尽管当时“台上台下哪里的人都有”,但并没有来自山东枣庄的贺敬之。
……
行文至此,为慎重起见,我给黄叶绿同志打了个电话,征询她的意见。她一听我念完《“马在叫”与“驴在叫”》的首段文字,就惊讶地说:“哪来的‘驴在叫’呀?没那会事儿!光年的初稿就是‘风在吼,马在叫’!”
是呀,人们常说历史不是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怎么好些当事人还健在,像《黄河大合唱》这样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不朽的经典作品,其诞生的真实情节就被莫名其妙传来的一声“驴叫”篡改了呢?
二00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