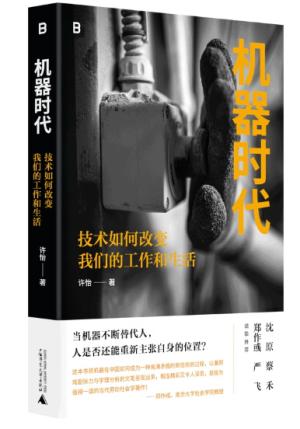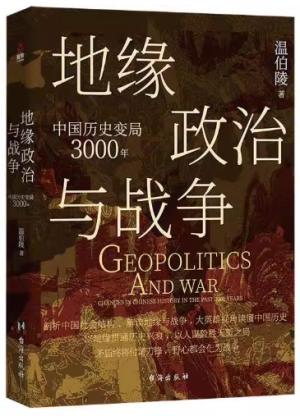新書推薦:

《
5秒法则:重拾改变生活的勇气
》
售價:HK$
63.8

《
睡虎地秦简普及本
》
售價:HK$
327.8

《
资本的全球化:近代上海外商证券市场兴衰史(1843-1941)
》
售價:HK$
107.8

《
纯粹理性批判 德国哲学家康德代表作 西方哲学史的里程碑著作 著名翻译家蓝公武经典译本
》
售價:HK$
138.6

《
惨痛的胜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的战略和作战行动
》
售價:HK$
18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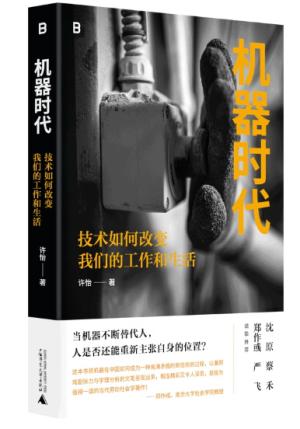
《
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
》
售價:HK$
6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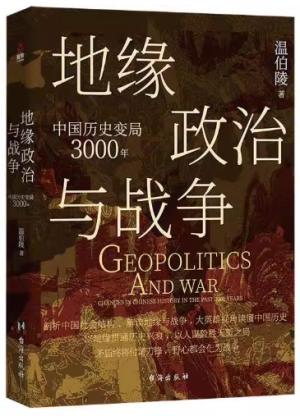
《
地缘政治与战争:中国历史变局3000年
》
售價:HK$
85.8

《
追踪进化论 在游戏中读懂科学史 《龙与地下城》玩家打造 沉浸式体验进化论 附赠精美计分器
》
售價:HK$
86.9
|
| 編輯推薦: |
|
这是一部以基层部队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乡村青年布小朋,几经周折终于当上兵。后被分配到偏远的A基地,康又汉是A基地老司令,一身正气,他逐渐喜欢上耿直、憨厚的布小朋,多次出手相助,使他在部队站稳脚跟。孟广俊和布小朋同年入伍,他善于投机钻营,为人圆滑世故。二人既有深厚的友谊,更有惊心动魄的争斗。随着职务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布小朋于诱惑面前坚决不伸手;孟广俊却雄心勃勃,不达目的不罢休。时光匆匆,孟广俊却面临着牢狱之灾;而一身浩然正气的布小朋,虽坎坷不断,最终成长为A基地司令员。
|
| 內容簡介: |
访谈《一座营盘》: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陶纯:这座营盘容不得蛀虫
这是多年以来为数不多的“剑”指军内腐败的长篇力作。
“我觉得写这部作品的时机成熟了。”上周,总装备部创作室专业作家陶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想说的话,在心里酝酿很久很久了,不写出来实在不痛快。但是多年来,‘军队反腐’这个话题一直很敏感。”
陶纯已有十多年没有写小说了。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就发表和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阳光下的故乡》《芳香弥漫》《像纸片一样飞》,在《人民文学》《十月》《青年作家》《上海文学》《解放军文艺》《小说界》等刊物发表了中篇小说二十多部。他参与创作的长篇小说《雄关漫道》和长篇纪实文学《国家命运》分别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还多次获得军内各项文艺大奖。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作品和奖项,陶纯仍觉得有“胸中块垒”难以表达、无法表达之痛。
“党内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更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2012年的冬天,当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班子向党内军内的腐败宣战时,他的心热了。
他对自己说:“现在可以写了。”
有读者在这部长篇里读到了徐才厚、谷俊山等军中“大老虎”的影子,但陶纯却坚持说:“我不认为它仅仅是一部‘反腐小说’。”
而先期读过这部作品的一些评论家、读者则认为:“《一座营盘》,是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又一扇大门即将被打开的先声,它为军事文学创作闯出了一条新路。”
《一座营盘》,写的不仅仅是一座营盘
《一座营盘》,以我军某个军级建制的基地为背景,展示了三十多年来我军老中青三代官兵走过的历程。“说是‘一座营盘’,其实我内心是将它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有营盘的缩影来写的。”陶纯说。
故事从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底的一场征兵展开,主人公布小朋因“家庭成分”不好,脾气又倔,靠姐姐布花委身于接兵连副连长康文定,才当上兵。康文定之父康又汉是A基地老司令,一身正气,康家人逐渐喜欢上耿直、憨厚的布小朋,多次出手相助,终于使这个出生于社会最底层的孩子在部队站稳脚跟。和布小朋同年入伍又分在一个连队的孟广俊,善于投机钻营,为人圆滑世故。早就瞄准“哪里油水足,就去哪里”的他,先是在部队经商的大潮中成了“能人”,后来又当上了基地营房处长;而老是心疼“军费”的布小朋偏偏当上了管钱的财务处长。尽管布小朋清正廉洁,但在“吃喝风”、“送礼风”等潜规则盛行的当时,他常为不得不违反制度和良知而痛悔不已。
布小朋和孟广俊二人既有一个连队成长起来的友情,更有立场鲜明的对垒。两人曾畅谈理想,布小朋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能在部队当个上校就很满足了;孟广俊笑他志向太低,孟广俊的人生理想是当个“中将”。“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句拿破仑的格言如今已传遍“营盘”,但是“只想当将军”的士兵,就是好士兵吗?孟广俊费尽心机攀附上了总部的一位大首长孔家瑞,花钱买到了“中将”军衔,终于成功实现了“人生理想”。但好景不长,十八大后,中央开始动真格“打虎”,孟广俊从人生最高处跌入囹圄。而布小朋虽然坎坷不断,最终成长为A基地司令员,成为中国军队新一代中坚力量的代表人物。
这还不是“军队反腐”小说吗?陶纯认为,不是,至少不仅仅是。如果是“纯反腐”小说,一定要花大量笔墨用在对一件件腐败案件抽丝剥茧式的侦查上,花在贪腐官员对纪检人员和组织的反扑、暗算上,但在《一座营盘》里,这些都被淡化了。陶纯把更多的笔墨花在了因军中贪腐和“小圈子”对部队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上,以及在被扭曲的政治生态下,一批忠诚而正直的军人所遇到的严峻考验。
正是从贪腐和“小圈子”对一个单位、一个行业乃至一个系统的政治生态的恶性破坏上,《一座营盘》的意义远大于一座座营盘。军队如是,地方如是,逆淘汰曾经到处都有。
“有读者说,孟广俊的原型就是谷俊山。应该说,孟广俊和谷俊山有相似之处,但在孟广俊的身上,不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说还有其他‘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职位虽不起眼但称得上‘虎蝇’的影子。”陶纯说。
“谷俊山这样的人,即使不能说哪里都有,但至少在生活中并不少见。否则,当下就不会有数十名将军被中纪委、军纪委调查。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这既是军队的耻辱,更是军队和国家在不幸之后的幸事。”陶纯说。
有读者质疑:现在还有布小朋这样一身正气的军人吗?陶纯肯定地说:“绝对有,这样忠诚和正直的军人,是国家的脊梁,是我们的军魂,每个单位都有。”
布小朋和孟广俊,这两个渐行渐远终成对手的军人,也可被视为一个军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朝左走,是布小朋;朝右走,是孟广俊。布小朋,走得很累,磕磕绊绊,有时甚至山穷水尽真无路;而孟广俊,越走越滋润,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你不得不掩卷而思:究竟是孟广俊在顺应、利用和固化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还是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在利用和“培育”乃至“浇灌”了孟广俊呢?
陶纯在书中还塑造了一个颇有分量的军人形象——夏忧。在常人眼里,他就是“瞎忧”,整天为国家战略“瞎操心”,而本人的仕途和家庭生活却一团糟。全书中,夏忧总共出场了二十一次,几乎涵盖了军队经商、台海危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灭等重大事件,每逢大事,他都有独到的见解,常有着惊人之语还偏管不住自己的嘴。在党忧党,在国忧国,在军忧军,夏忧其实是个难能可贵的军人,是另一个布小朋,他的军事理念和科技素养也绝不逊于布小朋,可惜的是,他没有布小朋这么坚韧,或者说他没有能永远坚强下去,没有真的成为同事调侃的“夏坚强”,他把生命终结在了十八大以前。
战争时期,军人要坚强;和平时期,军人须坚韧。如果你不想被不正常的政治生态所扭曲和吞噬,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尽可能地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必须足够坚韧,这也是一个合格军人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质。
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
陶纯和书中的主人公布小朋为同代人,而且都是农民的儿子。
陶纯出生于山东省东阿县姜楼镇陈店村,那里是鲁西平原地带,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黄河出河南后,经过他的家乡向东奔向大海。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和杀西门庆的阳谷县狮子楼,离他的老家只有几十里地,当地民风纯朴,嫉恶如仇。
陶纯发育长身体的年头,正是家乡农民最贫穷的时候。吃不饱饭,是他童年深刻的记忆。“你吃过榆钱吗?”他问,记者只能摇摇头,“那时,每到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榆树开花了,我们就爬到树上采榆钱。一串串的榆钱白白的,用手一捋就行,那样子真的像铜钱一样,中间有个眼。拿回家,我母亲就将它和玉米面合在一起,贴饼子吃。新鲜的榆钱又甜又有些苦涩,就算是农村孩子的美食了。”
家里兄妹五人,他是老大,下面四个全是妹妹。母亲干一天活,只能挣生产队七个工分。一个男劳力可以挣十个工分,折算一下,大概也就是一角来钱。陶纯十一岁就下地干活,一天只能挣四个工分;到十三岁了,可以挣五个工分。父亲没有读过书,母亲读到小学三年级,能识会写简单的常用字,算是家里唯一的文化人。家里穷,读完了小学,老古董式的祖父让他别读书了,理由是“读书白糟蹋钱,有了文化不会干农活,只能坑爹”。幸亏这遭到了他母亲的坚决反对:“不让孩子读书,让孩子没文化就是‘坑儿’。到头来,不是更‘坑爹’吗?”正是在母亲的顽强坚持下,陶纯读完初中读高中,参加了1980年的高考。
陶纯的考分本来可以上地方上的名牌学校,他却选择了位于长春的一所空军机务学校,学的是地勤专业。“农村孩子,还是认为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当兵不仅很光荣,而且上军校期间,不用家里花一分钱,学校全管,每月还有津贴费。”
陶纯至今记得他离家去军校报到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情景。当地有“上马饺子下马面”的习俗,母亲一宿未睡,为他包了韭菜鸡蛋馅的饺子,然后凌晨四点多钟叫醒了他。平时他忒爱吃母亲包的饺子,临出门却吃不下了。六点之前,母亲等人把他送到八里外的镇上等长途汽车。天气已经有了凉意,穿着夹袄的他感到心里更凉,车开的一瞬间,望着母亲的身影,他止不住留下了眼泪。这个十六岁的大男孩之前只去过几次县城,从没离开过父母,而军校远在东北,还规定一年半不能回家探亲。
一个乡村少年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和对家乡的依恋,都写在了《一座营盘》里。临行前的晚上,“(姐姐)布花特意烧了两大锅开水,倒进木桶里,让他洗得干干净净,把二十年岁月留在身上的脏污都洗掉,再换上新衣裳。泡在温热的水桶里,听到隔壁姐姐烧柴火引起的咳嗽声,他忍不住又哭了。”
留在布小朋心底的,不仅是饥饿,还有当兵第一天副指导员王新亮的话:“我们军人,花的每一分钱,我们吃的、穿的、用的,都是军费,军费是从国库里拨给的,其实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它包括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劳动成果,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
“军费”这个词,在全文中,反反复复出现了三十次。正是贫困的记忆,让陶纯和布小朋这两个农民的儿子更加懂得和珍惜“军费”的来之不易,“军费”就是军人和老百姓的关系。这就是布小朋的人生“底色”:为什么他不同于孟广俊,他能做到“能贪不贪”,全在这“底色”里。而对陶纯来说,对军费的珍惜也是他写这部小说的源动力:贪污腐败、买官卖官、惊人的浪费、形式主义,甚至侵蚀到营盘的封建迷信:“你这样瞎折腾,得糟蹋多少钱呀?这可都是军费,是纳税人的血汗钱!”
军旅作家要有情怀,更要有血性
陶纯的文学启蒙是在军校完成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王蒙、刘心武、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蒋子龙、鲁彦周,以及军旅作家徐怀中、李存葆……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站立在时代的潮头,直面人生、直面苦难,敢于打破一个个禁区,反映人民真实的呼声。陶纯读了他们的作品,有痛快淋漓的酣畅之感。正是这个时代潮,打开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军校生的视野和胸怀,让陶纯爱上了文学。
军校毕业后,陶纯来到驻扎在山东潍坊的空军部队。基层连队,生活条件很艰苦,要求严格,什么都要统一行动,每天晚上九点半,部队统一熄灯休息。陶纯就找到连指导员,请求人家把俱乐部的门打开,让他进去看书写作。指导员很爱才,关照说:“别太晚,十二点回去睡觉。”
就这样,陶纯开始了艰难的创作之路,当退稿装满了床头柜的抽屉时,四川成都的《青年作家》杂志终于给他寄来了用稿通知。那是1986年,他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从此他的文学创作激情一发而不可收。
在他1991年走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之前,《人民文学》和《解放军文艺》已经多次发表过他的作品。1993年从军艺毕业之后,二十九岁的他成为空军所属部队的专业作家。
但是自从2003年以后,陶纯十多年来基本没再写小说,改为创作电影和电视剧本。他认为,军旅文学遇到了一个瓶颈:从《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之后,军事文学走的大多是歌颂奉献精神的革命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这当然非常需要,但写了那么多年的军旅文学,不能不问一下:“今天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敌人?”这十多年来,我军的新型装备大量研发列装,虽然和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但是和过去相比,中国军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战斗力大大加强,已经足以令老对头们发怵。“今天,能够打败我们人民军队的,只能是腐败,”陶纯说,“腐败是军队最大的敌人。正如过去常说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但是军队的腐败现象,文艺作品能碰吗?多少年来,这是不成文的禁区。“毁我长城”的大帽子,曾经是不少军旅作家头上的“紧箍咒”。类似题材,军内的文艺刊物不敢发,地方的文学杂志、出版社似乎更是不敢碰,谁也不想找麻烦。
“军队的敌人,不就是军旅作家的敌人吗?”陶纯血性未泯。
陶纯认为,这些年来文学的凋敝,有目共睹。与其说是读者抛弃了文学,不如说是作家先远离了时代,不接地气了。文坛上“小时代”走红,少有作品真正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这是社会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它反过来又弱化了文学的力量,成为文学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物极必反。党的十八大以来,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一个个“大老虎”落入法网。
期盼已久的陶纯,从2013年5月起,全情投入《一座营盘》的写作。整整八个月,最多的一天他写了八千字。
去年冬天,《一座营盘》写作的最后关头,有一个影视公司老板找到他,请他一个月内帮助改定一个剧本,允诺给150万元稿费。
陶纯谢绝了,他不能停下笔走出这《一座营盘》。
军队需要这部作品。
记者问陶纯:你觉得写这部作品,什么是最难的?
“分寸感。我和作品中的布小朋一样,都是穷人家的孩子,没有军队的培养,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今天,因此我太爱军队了。我写到的买官卖官、任人唯亲、欺下瞒上、形式主义,部队的同志都知道我没有编造;但地方的人士看了会不会大吃一惊,会不会对今天部队还能打胜仗失去信心?这曾是我最担心的。现在看来,《一座营盘》这个分寸感还是把握住了。”
军事文学评论家汪守德对《一座营盘》的评价是:“它能直面丑恶,但写得不脏,分寸感好,充满了浩然正气。是伟大的时代召唤了作家,作家用自己的艺术良知回报了时代。”
陶纯,一个有血性的军旅作家,写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
|
| 關於作者: |
陶纯,一九六四年生。一九八〇年入伍,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长篇小说《阳光下的故乡》《芳香弥漫》《像纸片一样飞》,中短篇小说集《恋爱季节》《子弹穿过头颅》《雨中玫瑰》《坐到天亮》等。另外参与编剧了八部电影和电视剧。
文学作品曾多次获得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军文艺新作品奖一等奖”、“中国图书奖”,以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刊物的优秀作品奖。
|
| 內容試閱:
|
傍晚时分,空中飘起了雪花。天气冷寒,路上几乎没有行人,道路坑坑洼洼,布花骑一辆破自行车,艰难地向前行进。她脖子上围一条红围巾,如果不是因为天色已晚,她应该是很醒目的。途中,不知谁家的一只狗,追着她跑了一阵,狂吠了几声,然后无趣地掉头跑进了荒野。
到达县城西边的粮食局招待所门口时,雪花已经把布花的头发染白了。布花下车,拍打干净头上和身上的积雪,找个地方把自行车放好,落了锁。这时已是晚上八点钟左右。突然天边传来一声隆隆的炸雷,把布花吓了一跳。年底的天气,下雪是再寻常不过,但是天上打雷,却是很多年没有的事了。
粮食局招待所的服务员告诉布花,接兵的干部都不在,到街对面的三元酒家喝酒吃饭去了。布花不好意思在招待所前厅等人,就踱出来,先是到三元酒家窗户外面转了转,确实听到有操普通话的人在里面喝酒。然后,她回到招待所门口不远处的一棵柿树下,耐心地等。街上的一个大喇叭里正播放国际国内的新闻,国内的新闻,主要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党工作重心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然后又说国际新闻,主要是说越南背信弃义,忘恩负义,武装军警镇压和驱赶华侨等等,声音慷慨激昂。等到新闻播完,布花的脚快要冻僵时,三元酒家门上的布帘挑开了,出来五六个穿军装的人,说话带着明显的酒意,咋咋呼呼往这边走来。
布花的心扑通狂跳起来,几乎蹦到了嗓子眼。她背过身去,借着柿树的掩护,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镜子,飞快地照照脸庞,理了理额边散乱的头发。这当儿,那五六个人过来了,迈着矫健的步子进了招待所大门。但是这时候,布花才发现,她来时积攒的勇气消失得差不多了,她已经没有了跟进去的勇气。
布花犹豫一阵,决定回去。就在她往停放自行车的地方走去时,一个身材修长挺拔的军官摇晃着,朝她走了过来。她一下子认出来了,这人是接兵连的副连长,姓康,人们叫他康副连长。一个月前,在县医院她陪弟弟布小朋体检时,见过这个人。康副连长可能因为酒后小解,从三元酒家出来晚了。
康副连长打量了一眼布花。布花脖子上的红围巾是那么的耀眼。
仿佛地上有磁铁,布花的脚步也被吸住了:“康……康副连长……”
康副连长问:“你找谁?”
布花不知该怎样回答,一咬牙说:“就找你。”
康副连长四下看看,悄声说:“2楼201。你晚一会儿上去。”
说罢,康副连长晃荡着挺拔的身躯,旋风一般进了招待所大门。
布花犹豫片刻,没再犹豫,两分钟后,她进了门。她担心值班的服务员会盘问她,她想,如果服务员问她什么,她也许会掉头走掉。但是服务员头都没抬,什么也没说,一切仿佛都是命中注定。
布花上到二楼,楼道里光线昏暗,长长的走廊里只有三只灯泡亮着,其他的灯泡都像是睡着了。201房间的门虚掩着,没等布花敲门,康副连长就把门打开了一条缝,示意布花快进来。屋里明显地温暖,窗帘已经拉上,大灯没开,床头的小台灯开着。康副连长问布花渴吗,喝水吗?布花说不渴。只有一把椅子,椅子上搭着康副连长的军大衣,没有地方可坐,布花只好怯怯地坐到了床边。康副连长真像是喝多了,说话舌头直打弯,他先是到脸盆架那儿洗了几把脸,又拿起杯子漱了漱口。他说他很少喝酒,今天高兴,征兵任务即将完成,架不住几个战友劝酒,喝了有小半斤,出洋相了。
“你叫什么?”他问。
“我姓布,叫布花。”
“你是哪个村的?”
布花的装束不像城里人,他一下子就看透了。布花捏着袄角,说:“我家是大王公社胡家庄的。”
“胡家庄的……我没记错的话,是你弟弟想当兵,对吧?”
“是。”布花好生感动。喝醉了酒的康副连长居然能记得她弟弟。她赶紧补充说,“体检过了,政审也过了。”
“我知道。”康副连长说,“屋里热,你把围巾、棉袄都脱掉吧。”
布花愣了愣,想想人家说得对,就把围巾摘下来,把棉袄也脱掉了。昏黄灯光下的布花头发有些蓬乱,气息是迷人的。等她抬起头来时,看到康副连长正痴痴地望着她,离她那样近,眼里似乎有小火苗蹿出来。布花吓了一跳。然而没等她有什么反应,康副连长一把抱住了她,一种她从来没闻到过的浓烈的男人气息,瞬间击倒了她……她迷迷糊糊地说:“我兄弟叫布小朋。”
她又说:“胡支书的儿子胡一宫也想当兵。可村里就一个名额。”
她又说:“我兄弟身体条件比胡一宫好,可武装部不让我兄弟走。”
康副连长的嘴巴堵住了她的嘴。她一时透不过气来,挣扎了几下,呼噜着继续说:“胡一宫满脸疙瘩不说,脚底板还是个平的……”
后来她又说:“我兄弟上过高中,胡一宫初中都没毕业,我兄弟文化比他高……”
她还说了一些话,后来连她都记不得到底说了些什么。再后来就是一阵尖锐的疼痛,她喊叫了一声,眼泪淌下来了。他在上面说着酒话、疯话、难听的话,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来,居然头一歪就睡着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