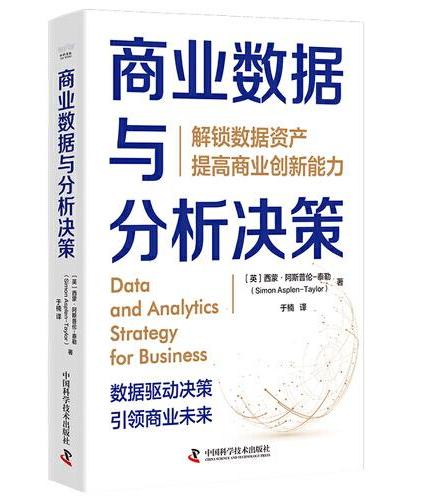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数据库原理与应用(MySQL版)
》
售價:HK$
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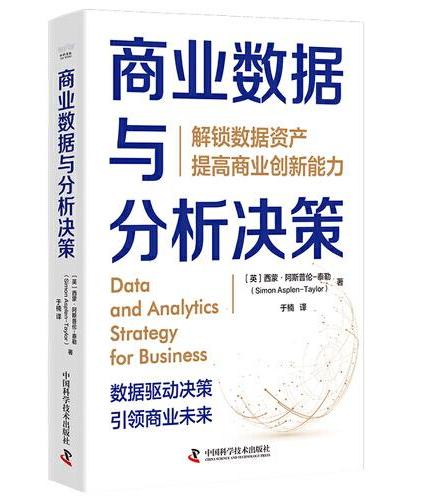
《
商业数据与分析决策:解锁数据资产,提高商业创新能力
》
售價:HK$
79.2

《
倾盖如故:人物研究视角下的近世东亚海域史
》
售價:HK$
77.0

《
史学视角下的跨文化研究(一): 追踪谱系、轨迹与多样性
》
售價:HK$
104.5

《
历史文本的文化间交织:中国上古历史及其欧洲书写(论衡系列)
》
售價:HK$
118.8

《
1688:第一次现代革命(革命不是新制度推翻旧制度,而是两条现代化道路的殊死斗争!屡获大奖,了解光荣革命可以只看这一本)
》
售價:HK$
217.8

《
东方小熊日本幼儿园思维训练 听力专注力(4册)
》
售價:HK$
88.0

《
粤港澳大湾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
》
售價:HK$
107.8
|
| 編輯推薦: |
★ 语文新课标必读名著,被誉为“人性向善的精神史诗”。
★ 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文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不朽之作。
★ 一部能代表雨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皇皇巨著。
一部气势恢宏的“人类苦难的百科全书”,世界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
| 內容簡介: |
《名家名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之一。是雨果的代表作之一。
冉·阿让因饥饿偷取了一块面包而入狱,出狱后又偷盗主教的银器,因受到主教的感化而从善,改名马德兰,兴办工业,救济穷人。后被选举为市长,却被新任警长沙威认出。为解救被误认为冉·阿让的无辜者,主动自首而再度被捕。出狱后收养了死去女工芳汀的女儿珂赛特。珂赛特长大后与贵族青年马里尤斯相恋,马里尤斯赴巴黎参加起义,冉·阿让为成全二人,亲赴战场寻找马里尤斯,却恰好碰见起义军将要处决被俘的沙威。冉阿让以德报怨,放走沙威。沙威受到感化,投水自尽。后起义失败,冉·阿让冒险救出受伤的马里尤斯,在成全他与珂赛特的婚事后死去。
|
| 關於作者: |
|
维克多·雨果(1802—1885),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贯穿他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其文学创作有诗歌、小说、戏剧、政论、散文随笔以及文学评论,卷帙浩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悲惨世界》及《九三年》等。
|
| 目錄:
|
第一部 芳汀 001
第一卷 沉沦 002
第二卷 一八一七年 050
第三卷 寄放,有时便是断送 062
第四卷 下坡路 072
第五卷 沙威 100
第六卷 尚马秋案件 105
第七卷 祸及 114
第二部 珂赛特 123
第一卷 奥里翁战舰 124
第二卷 履行对死者的诺言 129
第三卷 戈尔博老屋 140
第四卷 夜猎狗群寂无声 146
第五卷 墓地来者不拒 169
第三部 马吕斯 199
第一卷 大绅士 200
第二卷 外祖和外孙 203
第三卷 苦难的妙处 217
第四卷 双星会 223
第五卷 坏穷人 238
第四部 普吕梅街牧歌和圣德尼待史诗 271
第一卷 爱波妮 272
第二卷 普吕梅街的宅院 278
第三卷 结局不像开端 287
第四卷 销魂与忧伤 296
第五卷 他们去哪里 306
第六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310
第七卷 马吕斯走进黑暗 322
第八卷 绝望的壮举 326
第九卷 武人街 338
第五部 冉·阿让 347
第一卷 四堵墙中的战争 348
第二卷 出污泥而不染 381
第三卷 沙威出了轨 413
第四卷 祖孙俩 419
第五卷 不眠之夜 427
第六卷 最后一口苦酒 430
第七卷 人生苦短暮晚时 440
第八卷 最终的黑暗,最终的曙光 448
|
| 內容試閱:
|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沉沦
[一] 一天行程的傍晚
一八一五年十月初,约莫日落的前一小时,有位旅客走进小小小的迪涅城。在这种时分,只有寥寥无几的居民还站在窗口或门口,他们望见这个旅客,心中隐隐感到不安。很难遇见比他衣衫更褴褛的行人了。此人中等个头儿,身体粗壮,正当壮年,看样子有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头戴一顶皮檐鸭舌帽,遮去流汗的、风吹日晒黑了的半张脸。身穿黄色粗布衫,领口搭了一个小银锚扣,露出毛茸茸的胸膛,领带皱巴巴的像根绳子;蓝色棉布裤已经很旧,一个膝头磨白,另一个膝头磨出窟窿;外罩灰色外套十分破旧,一个袖肘上用粗线补了一块绿呢布;背上有一个崭新的军用袋,装得满满的,袋口紧紧扎住;他手里拿一根多节的粗棍,脚下没有袜子,直接穿一双打了铁掌的鞋;他的头发短短的,胡须长得很长。
他浑身破烂不堪,再加上汗水、热气、风尘仆仆,给他增添一种说不出来的肮脏。
他推成平头,但是头发又开始长了,都竖起来,仿佛有一段时间没理了。
谁也不认识他,显然只是一个过路人。他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南边来的。可能是从海边来的。因为,他进迪涅城所走的街道,正是七个月前拿破仑皇帝从戛纳前往巴黎的路线。这个人肯定走了一整天,样子十分疲惫。城南老镇的一些妇女,看见他停在加桑迪大街的树下,并在林荫道尽头的水泉喝水。他一定渴极了,因为在后边跟随的那些孩子,看见他走了二百步远,到了集市广场又停下,对着水泉喝水。
他走到普瓦什维街口,便朝左手拐去,径直走向市政厅,进去之后,过了一刻钟又出来。一名宪警坐在门旁的石凳上——三月四日,德鲁奥将军正是站在那个石凳上,向惊慌失措的迪涅居民宣读瑞安海湾宣言。那汉子摘下帽子,冲那宪警恭恭敬敬施了一礼。
那宪警没有回礼,只是定睛注视他,目送了一程,便走进市政厅。
且说那汉子走向当地最好的“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进入临街的厨房,只见所有炉灶都生了火,壁炉里的火很旺。老板同时也是掌勺的厨师,他正在炉灶和炒锅之间忙碌,给车老板准备丰盛的晚餐,隔壁就传来那些车老板谈笑的喧哗声。凡是旅行过的人都知道,谁也没有车老板吃得好。一根长铁钎上插着几只白竹鸡和雄山雉,中间插着一只肥肥的土拨鼠,正在火上转动烧烤;炉子上则炖着两条洛泽湖的大鲤鱼和一条阿洛兹湖的鳟鱼。
店主听到门打开,走进一位新客,没有从炉灶抬起眼睛就问道:
“先生要什么?”
“吃饭睡觉。”那人答道。
“再容易不过了。”店主又说道。这时,他回过头来,从头到脚打量一下旅客,便补充一句,“……交现钱。”
那人从外套兜里掏出一个大皮钱包,答道:
“我有钱。”
“那好,这就伺候您。”
那人把钱包放回兜里,卸下行囊,撂在靠门的地上,手里还拿着棍子,走到炉火旁,坐到一张矮凳上。迪涅城位于山区,十月的夜晚很冷。
这工夫,店主来回走动,总是打量旅客。
“很快就能吃上吗?”那人问道。
“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这时,新来的客人转过背去烤火,可敬的店主雅甘·拉巴尔则从兜里掏出一支铅笔,又从靠窗放的小桌上的旧报纸上撕下一角,在白边上写了一两行字,再折起来,但是没有封上,交给一个看样子是给他又当厨役又当小厮的孩子,还对着耳朵吩咐了一句,于是,那孩子便朝市政厅的方向跑去。
那旅客一点也没有看见这场面。
他又问了一声:
“很快就能吃上吗?”
“稍等一会儿。”店主答道。
那孩子回来,又带回那张字条。店主急忙打开,就好像等候回音似的。他仿佛仔细看了一遍,接着摇了摇头,沉吟了片刻。那旅客心神不宁,似乎在想事儿。店主终于跨上前一步,说道:“先生,我不能接待您。”
那人在座位上猛然一挺身子。
“怎么!您怕我不付钱吗?您要我先付钱吗?跟您说,我有钱。”
“不是这个缘故。”
“那是为什么?”
“您有钱……”
“不错。”那人答道。
“可是我,”店主却说,“我没有客房了。”
那人平静地又说道:“那就把我安顿在马棚里吧。”
“不行。”
“为什么?”
“地方全让马匹占了。”
“好吧,”那人又说,“阁楼有个角落也行,放上一捆草。这事儿吃了饭再说吧。”
“我也不能供给您饭吃。”
这种表示,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语气很坚定,那旅客感到事情严重了,立刻站起身。
“哼,算啦!我可饿得要死。太阳一出来我就赶路,走了十二法里。我付钱嘛。我要吃饭。”
“什么吃的也没有。”店主说道。
那人放声大笑,身子转向壁炉和炉灶。
“什么也没有!这些食物呢?”
“这些全是定做的。”
“谁定的?”
“那些车老板先生。”
“他们有多少人?”
“十二人。”
“这里的食物够二十人吃的。”
“他们全定下了,预先付了钱。”
那人重又坐下,还以原来的声调说:“我来到旅店,肚子饿了,我不走。”
这时,店主俯下身,对着他耳朵,用一种令他惊抖的口吻说:“走开。”
那旅客正弯下腰,用他棍子的包铁头往火里拨弄几块炭,他听见这话,猛地转过身,正要开口反驳,而店主却盯着看他,又低声说道:
“喂,别废话了。要我说出您的姓名吗?您叫冉·阿让。现在,要我说您是什么人吗?我看见您进来,就觉得有点不对头,于是派人去市政厅问一问,这就是给我的回答。您识字吗?”
店主说着,就把打开的字条递给旅客。那张字条刚从旅馆传到市政厅,又从市政厅传回旅馆了。那人朝字条上瞥了一眼。
店主沉默片刻,接着又说道:“我一向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走开。”
那人低下头,拾起撂在地上的行囊,便离去了。
他上了大街,漫无目的地走去,而且溜着墙根儿,如同一个丢了面子而伤心的人。他一次也没有回头。他若是回头,就会看见“柯耳巴十字架”旅馆老板站在门口,被他所有旅客和街上行人围着,正用手指着他高声谈话,而且,从那众人惊疑的眼神里,他就能猜出他刚一到达,就闹得满城风雨了。
整个场面,他一点也没有瞧见。失魂落魄的人不朝身后看,他们十分清楚,追随他们的是厄运。
他就这样走了一阵,一直信步朝前走,穿过一条条他不认识的街道,忘记了疲劳,正像人在伤心时常有的那样。突然,他感到饥肠辘辘。天快黑了。他四下张望,看看能否发现一处可以过夜的地方。
那家华丽的旅馆拒不接待他,那么,他就找一家大众酒馆,找一家下等酒吧。
正巧街那端点亮一盏灯,悬挂在直角形铁架上的一根松枝,映现在暮晚的白色天空上。于是,他朝那里走去。
那的确是一家酒馆。在沙佛街开的一家酒馆。
那旅客停了一会儿,隔着玻璃窗朝里望望,只见顶棚低矮的餐厅,由桌上一盏小灯和壁炉里的旺火照明。有几个人正在喝酒,老板在烤火。一口挂在吊钩上的铁锅在火上烧得哗哗作响。
这家酒馆也兼客店,有两个门出入。一扇通街,另一扇门对着满是粪土的小院。
那旅客不敢从临街的前门进去,溜到院子里,又停了一会儿,这才小心翼翼地拉起门闩,将门推开。
“谁在那儿?”老板问道。
“一个要吃饭和过夜的人。”
“好哇。这里可以吃饭过夜。”
于是,他走进来。喝酒的人全都扭头看,他一侧有灯光,另一侧有火光照着。在他卸行囊的工夫,大家打量他好一会儿。
老板对他说:“这儿有火。锅里煮着晚饭。过来烤烤火吧,伙计。”
他走过去,坐到炉灶旁边,将走远路磨破的双脚伸到火前,闻到锅里飘出的香味儿。他的帽子仍然压得低低的,露出半张脸;从脸上能隐约看出一种舒适的表情,但是掺杂着饱受苦难所具有的凄然神态。
不过,他的侧影显得坚强有力,也显得忧伤。他这相貌的组合非常奇特:乍看上去低下谦卑,最后又呈现出一副凛然正色。眼睛在眉毛下炯炯发亮,犹如荆丛里的火堆。
且说围着餐桌喝酒的人中间,有一个马贩子,他先去将马拴到拉巴尔的马棚里,然后才进沙佛街这家酒馆。也是碰巧,当天早晨,从布拉-达斯村到……(地名我忘了,想必是埃库布龙)的路上,他遇见这个一副狼狈相的旅客。路上遇见时,这人看样子已经疲惫不堪,还求过让他坐到马后臀捎一段路。马贩子的回答,就是催马加快脚步。半小时之前,这个马贩子也在围着雅甘·拉巴尔的那堆人中间,他还对“柯耳巴十字架”旅馆的那帮顾客,亲口叙述了他早上那次不愉快的相遇。现在,他从座位上偷偷向店主使了个眼色。店主走过去,二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刚来的旅客重又陷入沉思。
老板回到壁炉前,一只手突然按在那人肩上,对他说道:
“你给我从这儿走开。”
那旅客转过身来,口气温和地回答:
“唔!您知道啦?”
“是的。”
“另一家旅馆把我赶出来了。”
“也同样把你从这里赶走。”
“您要我去哪儿呢?”
“别的地方去。”
那人拾起他的棍子和行囊,便离去了。
几个孩童从“柯耳巴十字架”跟来,好像守在这儿等着他,见他出了酒馆,就朝他扔石块。他气愤地回身走几步,举起棍子威胁,吓得孩子像群小鸟一样逃散了。
他从监狱门前经过,看见门上垂着一条铁链,便上前拉响门铃。
一个小窗口打开了。
“看守先生,”他恭恭敬敬摘下帽子,说道,“您能打开门,留我住一夜吗?”
一个声音回答:
“监狱不是客店。您设法让人抓起来,这门才能给您打开。”
小窗口又关上了。
他走上一条小街,只见两侧有许多花园,其中几座只用篱笆围着,给街道增添欢快的气氛,只见花园和篱笆之间有一所小平房,窗口有灯光,他像到那家酒馆那样,先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房间很大,墙壁刷了白灰,一张床上铺着印花布床单,角落里放着摇篮,屋里还摆了几张木椅子,墙上挂着一支双响猎枪。房间正中的桌子上摆了饭食,一盏铜碗灯照见粗麻布白色台布,上面盛满酒的锡壶像银器一样闪亮,棕褐色汤盆热气腾腾。餐桌旁边坐着一位四十来岁的男子,他喜笑颜开,在膝盖上站着一个小孩。他身边坐着一位很年轻的女子,正给另一个孩子喂奶。父亲欢笑,孩子欢笑,母亲微笑。
面对这温馨宁静的家庭场景,那个外乡人出了一会儿神。他心中想些什么呢?只有他本人才可能说清楚。也许他想到,这个愉快的家庭很可能好客,他看见洋溢幸福的地方,也许能找到一点怜悯之心。
他极轻地敲了一下窗玻璃。
里边人没有听见。
他又敲第二下。
他听见女人说:“当家的,好像有人敲门。”
“没有。”丈夫答道。
他再敲第三下。
这回,丈夫站起来,端上油灯,走过去开门。
这人身材高大,半务农半工匠。他扎了一条肥大的皮围裙,一直搭到左肩上,腹部鼓起来,皮裙里边装着一把锤子、一块红手帕、一个火药壶,以及各种各样的物件,像装在口袋里一样,由一条腰带兜住。他朝后仰着头,衬衣大敞着口,露出赛似公牛的白净脖颈。他长着两道浓眉、一脸很重的黑髯须、一对金鱼眼睛,下颏儿尖尖的,整个相貌上,还有一种难以描绘的在自家家中的神态。
“先生,”那旅客说道,“打扰了。我付钱,您能给我喝点菜汤,让我在园中那个棚子角落里睡一夜吗?请告诉我,可以吗?我付钱行吗?”
“您是什么人?”房舍主人问道。
那人答道:“我从皮一穆瓦松村来,走了一整天,走了十二法里。您能接待吗?我付钱行吗?”
“我不会拒绝一个正经人花钱投宿的,不过,为什么您不去旅馆呢?”
“旅馆没地方了。”
“唉!不可能。又不是庙会赶集的日子。拉巴尔那儿您去过了吗?”
“去过了。”
“怎么样?”
那旅客有点尴尬地回答:“我不清楚,他没有接待我。”
“沙佛街那家叫什么来着,您去过了吗?”
那外乡人更加尴尬了,结结巴巴地回答:
“他也没有接待我。”
农夫的脸上换了怀疑的表情,他又从头到脚打量不速之客,突然提高嗓门,声音有些战抖地说:
“莫非您就是那个人?……”
他又瞥了外乡人一眼,倒退三步,将油灯撂在桌上,从墙上摘下猎枪。
就在农夫说“莫非您就是那个人?……”的工夫,那女人已经站起身,将两个孩子抱在怀里,慌忙躲到丈夫的身后,还敞着胸口,瞪大眼睛,惊恐地望着那外乡人,嘴里咕哝着:
“错马罗德。”
所发生的这一切,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房主就像观察毒蛇一样,打量一阵那人之后,又来到门口,说了一声:
“滚!”
“行行好吧,”那人又说,“给碗水喝。”
“给你一枪!”农夫答道。
他啪的一声又把门关上,求宿人听见插了两道门闩的声响。过了一会儿,又传来上窗板和别铁杠的声音。
天色越来越黑了。阿尔卑斯山区的冷风飕飕刮起来。那外乡人借着苍茫暮色,望见临街一个园子里有一草棚,仿佛是用草皮垒起来的。他把心一横,跨过一道木栅栏,溜进园子里,走近草棚,看到它的门就是又窄又矮的洞口:这类草棚,很像养路工在路边搭的窝棚。他一定认为这确是一名养路工的窝棚,而且他饥寒交迫,饥饿只好忍了,但这至少是个避寒的场所。一般来说,这类窝棚夜晚没人住,于是他趴下来,匍匐着爬进去。里面相当暖和,地上还铺了厚厚一层麦秸。他实在太累了,一动不动,就这样躺了一会儿。继而,他觉得背上压着行囊不舒服,卸下来就是现成的枕头,于是他动手解皮背带。正在这时,旁边响起吓人的吼声。他抬头一看,只见黑暗中草棚洞口映现出一条大狗的脑袋。
原来这是个狗窝。
他本人身强力壮,样子又凶猛,还有棍子当家伙,拿行囊当盾牌,挣扎着退出狗窝,只是破衣烂衫的口子又撕大了。
同样,他挥舞棍子,且战且退,不得不用剑术师所说的“玫瑰护身剑法”,逼使恶犬不敢近前,终于退出园子。
他费了好大劲才重又跨过栅栏,回到大街上,孤苦伶仃,无家可归,连个躲风避寒的地方都找不到,甚至钻进破烂狗窝里,躺在铺地的麦秸上也被赶出来。他看见一块石头,不是坐下,而是一屁股跌落在上面,一个过路人仿佛听见他恨恨说道:“我连一条狗都不如!”
过了一会儿,他又站起来往前走,出了城,希望在田野上找到树木或者草堆,也好避避风寒。
他始终低着头,走了一段时间,直到觉得远离了所有住户人家,他才举目四望。他来到一片田地中间,前面有一个矮丘,覆盖着收割后的麦茬儿,就像剃光了的脑袋。
天边已经完全黑了,那不仅仅是夜色,还是低沉沉的鸟云,乌云仿佛压着山丘,又渐渐升起,要布满整个天空。然而,月亮要升起来了,苍穹还飘浮着暮色的余光,而云彩在高空形成淡白色的圆顶,上面的微光落到大地上。
因此,大地比天空还要亮一些,这就显得格外阴森可怕。荒凉的矮丘光秃秃的,由黑黝黝的天边衬出灰色模糊的轮廓。整个形象又丑又陋又卑琐,又凄惨又狭小。无论田野还是矮丘上,都空荡荡的,只有一棵歪七扭八的树,在离这旅客几步远的地方瑟瑟发抖。
显而易见,在智慧和精神方面,这个人远远没有养成细腻敏锐的习惯,对事物的神秘现象麻木不仁。然而,在这天空中,在这座丘冈上,在这片平野里,在这棵树木枝叶中,有一种无限凄惶的意味,他呆立在那里出了一会儿神之后,就猛然沿原路折回去了。有些时刻,大自然也显出敌意。
他原路返回。迪涅城门已经关闭。在宗教战争中,迪涅城屡遭围困,直到一八一五年,老城墙两侧还有不少方形堡垒,后来才拆毁。他从城墙豁子回到城里。
约莫已经晚上八点钟了。他不熟悉街道,又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
走着走着,又来到市政厅,继而又到神学院,经过大教堂广场时,他朝天主教堂挥起拳头。
广场一角有一家印刷所。在厄尔巴岛由拿破仑口授的皇帝诏书,以及羽林军告全军书,带回大陆时,头一版就是这家印刷所印制的。
他精疲力竭,再也不抱任何希望,就躺在印刷所门前的石椅上。
恰好这时,一位老妇人从教堂里出来,她发现黑暗中躺着一个人,便问道:“您在那儿干什么呢,朋友?”
他粗暴而气愤地回答:
“您瞧见了,老太婆,我在睡觉。”
老太婆,就是R侯爵夫人,她的确当得起这种称呼。
“睡在这石椅上?”她又问道。
“我拿木板当褥子,已经睡了十九年, ”那人答道, “今天,我又拿石头当褥子。”
“您当过兵吧?”
“不错,老太婆,当过兵。”
“为什么您不去住旅店呢?”
“因为我没钱。”
“唉!”R侯爵夫人说,“我的钱袋里只有四个苏了。”
“给我就是了。”
那人接过四个苏铜钱。R夫人继续说道:
“您拿这点钱不够住旅店。您就没有去试一试吗?您这样过夜怎么行呢。您一定又冷又饿。总有人发善心,留您住一夜。”
“每扇门我都敲过了。”
“怎么样呢?”
“到处都赶我走。”
“老太婆”捅了捅那汉子的胳臂,指了指广场对面挨着主教府的一所矮小的房子。
“每扇门您都敲过了吗?”她重复说道。
“不错。”
“那扇门敲过了吗?”
“没有。”
“去敲敲那扇门吧。”
|
|